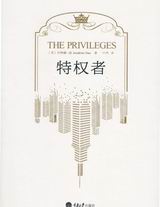1944年7月,远征军强渡怒江,收复了滇西的大片失地,开始了著名的松山大反攻。日军困兽犹斗,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坚固的明岗暗堡,发誓拼个鱼死网破。十多天过去,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只见一队队伤员抬下来,又见一支支部队拉上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7月27日凌晨,坚守待命的116师36团2营1连接到紧急命令,要求这个连尽快抓紧时间吃饭,饭后迅速奔赴火线,投入最后的生死决战。随着命令送来的,还有一批慰劳食品:猪肉、粉条、蘑菇、竹笋、高粱面这个连队是随大部队从东北一路后撤,一直退到大西南来的,官兵清一色都是东北人。这些具有东北风味的食品,无疑让人一下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勾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这下炊事班可忙开了。当第一甑高粱窝窝头刚刚出笼,一个小个子兵冒着被蒸气烫伤的危险,抢先抓起一个窝窝头,放在鼻尖前闻个不停,深情地吮吸来自黑土地的气息突然,“啪——...
初中毕业后,我就不再上学,于是我正式开始了我的流浪生涯,先是学着拜 大哥,紧接着就是无休止的打架,酗酒。不断的惹是生非,还经常去偷别人的自 行车,总之所有小混混干的坏事我几乎都干过,就这样混了四五年,派出所所有 警察的生辰八字,我都了如指掌,那一年我还不到二十岁。 每天晚上我都去金三角夜总会打发时间,把总各种渠道上挣来的钱肆意花掉,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简直没有一点人性,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喝的价格昂贵的 酒中,也许浸透了别人的血和泪,因为那时的我整天就和跟我一样坏甚至比我更 坏的人混在一起,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又在金三角喝的头晕目眩,正打算回 去睡觉,但我总觉得这一次酒吧里有些不和谐,与平日相比,我感到有一点刺眼...
:**钱学森传王寿云 等钱学森(一)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名家治,后以号行)是浙江杭州一没落丝商第二子,少小就学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曾到日本学教育和地理、历史。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女儿。钱学森的外祖父欣赏钱均夫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民国成立后,钱均夫就职北京当时的教育部。钱学森在3岁时随父到了北京,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师大附小和师大附中。...
【真事儿一】 往水箱里放砖头的富太太 闹闹是我朋友的女儿,前年去德国留学,租住在巴泽太太家。见面那天,老太太非常热情,带着闹闹熟悉一番环境,最后指着抽水马桶的开关说:"这是个老式马桶,正常用非常费水,我在水箱里放了一块小砖头,摁开关时要用不同的力量,砖头就会控制里面的球阀,让水流变小。小便后要这么摁,大便后要这么摁。"她边说边手把手地教闹闹,直到闹闹可以自己操作才罢手。 闹闹在国内时是个典型的物质女孩儿,别说节水意识,就是宿舍洗手房里长流水,她都会视而不见。没想到,留德的第一堂课,竟是一个抠门儿老太太给上的。闹闹在不以为然的同时,私下直翻巴泽太太的白眼。 没过几天,闹闹主动要求洗碗。刚打开水龙头,巴泽太太就惊叫着跑过来,嘴里嚷嚷着"太费水,太费水!"她给闹闹做起示范,先接一盆水,里面放点儿洗碗液,再把脏碗碟放里面擦洗一遍。冲洗的水流非常讲究,水龙头拧到这个位...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也可以不注意,宁愿不注意。希特勒军队人侵苏联时,苏联的犹太人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如果他们一开始抓紧时间向后方逃亡,是可以逃脱纳粹的魔掌的。要命的是犹太人对德国军队抱有好感。根据历史的经验,十月革命后那些“入侵俄国的外国干涉军中,德军的军纪算是好的”。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还记得当年白军头目彼得留拉在乌克兰屠犹,哀鸿遍野,血流成河;幸亏德国军队进驻,才制止了彼得留拉的屠犹。如今德国人会怎样对待犹太人呢?难道还会坏过彼得留拉?尽管苏联政府于战争爆发后不断宣传纳粹残暴,犹太人主动随苏军后撤的却不多。这造成了惨痛的后果,1941年至1944年,德国党卫军屠杀了90万苏联犹太人。 再说犹太人。波兰与丹麦是两个居住有犹太人的国家,两国的国情差别很大。波兰人是苦难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列强欺凌,国家四次被瓜分,卡廷森林惨案是世界史上重大悲剧之一。丹麦人是幸运民...
序言: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社会环境中朋友是最重要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你的朋友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于丹教授告诉我们《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谓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也就是说,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这三种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会给我们的生活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而那三种坏朋友又是什么样的呢?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又如何来分辨好朋友和好朋友呢?先说三种好朋友,所谓益者三友就是友直、友谅、友多闻。也就是第一这个朋友为人要正值、要坦荡、要刚正不阿,一个人不能有谄媚之色,要有一种朗朗人格,在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这是一种好朋友。因为他的人格可以映校你的人格,他可以在你怯懦的时候给你勇气;他可以在你犹豫不前的时候给你一种果断,这是一种好朋友;第二种是友谅,也就是宽容的朋友。其实宽容有的时候是一种美德,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美...
小时候上幼儿园,老师必须把我的坐位单独排在窗口。因为如果不能一直凝视着窗外,我就会哭闹不休,搞得别的小孩无法上课。于是从四岁到六岁,我是对着窗外度过我人生最早的学校生涯的。 世界,就在窗户的外面。 幼小的我不会这么想,却执拗地只愿意面对窗外那个有人走过,有云和树叶飘过的光影变幻的世界,而不愿意回头接受窗子里这种被规定,被限制的小小人生。令人头痛的是,长大之后的我竟然也是这样。 我没办法接受人生里许多小小的规矩。进小学,我读不会课本,做不了功课,念中学,我被好几所学校踢来踢去,上大学,我是自己关着门读了几个月书奇迹般考上的,等退伍有一份好工作后,我却跑去做当时还没有人认同的专职漫画家。就像小时候一样,别人上班,上课,我却只想一直看着,或接触窗户外面那个流动的世界。...
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是基于法律的,更是基于道德良知的.但中国的现实是,几乎很少有人把道歉作为一种道德要求,也几乎不会有人因为良心的声音而站出来承担责任. 道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没有人这样说过。当你做下一件不利于他人的事情时,你应当对受到影响的人说声“对不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受过的教育。只是,社会有时具有一种抹消教育成果的效应,当一个人渐渐不再年少,“对不起”会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 人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道歉的频率逐渐降低来量度。总体来看,在我们这个时代,“道歉”是一种与“主见”和“行为能力”相排斥的东西,人的“主见”越大,“行为能力”越强,就越是拥有不道歉的本领,都具有降低“道歉”水平的效用。当一个人完全不脸红、完全不向人道歉的时候,恭喜,你有福了,你已经不是一般的“大人”,而上升为别人眼中的“大人物”,犯下一个错,不仅不必道歉,而...
**第一章 奇怪的车祸(1)省委大楼。 运行到一楼的电梯里走出两位领导干部:一位是秀川市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温运和,一位是省委书记福庶国,他们刚刚研究完重要的人事工作。福庶国一贯亲贤礼下,凡比较重要的客人临别时,他都要亲自送到大楼门厅外。他们边走边交谈着,看来两人的兴致都很高。 大楼门厅外的台阶下,站着两位迎候他们的高个子男人,其中较年轻的是温运和的秘书林达,较老的是秀川市长亭县县委书记包仁杰。 福庶国站在台阶上微笑着说:“不送了,再见!”他和三个人一一握手道别。 别过省委书记,他们转身走向停车坪上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轿车,这是县委书记包仁杰的座车。市委的奥迪车把温书记和林秘书送到省委后返回去了,是温书记叫司机开回去的,他说:“我在省委汇报工作后要飞到上海、深圳去,为了改变个别集团公司在秀川的垄断局面去落实招商事宜,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来接我,听电话通知。没想到省...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锈得黑里透红,缠着盘旋转折的纹路,经常发出苍然悠远的声音,穿过庙外的千株槐,拂着林外的万亩麦,熏陶赤足露背的农夫,劝他们成为香客。 钟声何时响,大殿神像的眼睛何时会亮起来,炯炯的射出去;钟声响到那里,光就射到那里,使鬼魅隐形,精灵遁走。半夜子时,和尚起来敲钟,保护原野间辛苦奔波的夜行人不受邪崇 庙改成小学,神像都不见了,钟依然在,巍然如一尊神。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大家围着钟,睁着发亮的眼睛,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的大明年号上,尝震颤的滋味。 手挨着手,人人快活得随着钟声飘起来,无论多少只小手压上去,钟声悠悠然,没有丝毫改变。 校工还在认真的撞钟,后面有人挤得我的手碰着她尖尖的手指了,挤得我的脸碰着她扎的红头绳儿了。挤得我好窘好窘!好快乐好快乐!...
**第一章 动物的性生活:生物学的依据女人吗?这也太简单了!热衷于搞简单公式的人说:她就是子宫,就是卵巢。她是个雌性(female)——用这个词给她下定义就足够了。“雌性”这个词出于男人之口时,有种侮辱性的含意,可是,他并不为自己的动物性感到羞耻。相反,要是有人谈到他时说:“他真是个雄性(male)!”他会感到自豪。“雌性”这个词之所以是贬义的,并不是因为它突出了女人的动物性,而是因为它把她束缚在她的性别中。如果男人认为雌性这个性别即使在无害的哑巴动物那里,也是卑鄙的、有害的,这显然是由于女人引起了他的不安与敌意。不过他还是希望,能在生物学中找到为这一观点辩解的根据。“雌性”这个词,在他脑海里像跳萨拉班德舞似的引起了他一连串的联想:一个硕大的圆形...
=================书名:特权者作者:[美]乔纳森·迪,译者:叶肖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12ISBN:9787562476498编辑推荐内容推荐作者简介=================一隔了这许多年,总算有对新人要结婚了。新郎和新娘都刚过二十二岁,这年头算年轻的了。大多数亲友昨天就已经飞过来了。匹兹堡不算大,不过区区五十万人,可亲友们还是一副摸不着东西南北的样子。或许有点儿势利,可没坏心眼儿。一方面,他们来自纽约和芝加哥;另一方面,此时此地,他们最喜欢这种调调,幻想着自己身陷乌有之乡,新鲜、躁动,外加点儿神秘。不用说,孩提时代、少年时代,他们都参加过这个叔叔、那个阿姨的婚礼,有几位甚至还参加了自己父母的婚礼,都清楚婚礼上有什么,没什么。可这次不同以往。这次,他们是新人的朋友兼同龄人,这还是头一遭,感觉有点儿怪,有点儿乱,还有点儿怕,怕自己就此被扯进了事事讲究责任的成人世界,怕自己一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