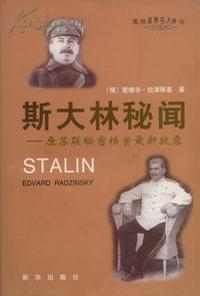:**《红袖》浮石引 子柳絮是上午九点钟左右被带走的。那天上午十点钟有场拍卖会,否则,柳絮还不会那么早去公司。她把宝马车泊好,刚走进写字楼的大堂,就有两个女人斜地里朝她靠了过来。她们一点也不起眼,如果不是她们的速度有点超常规,柳絮压根儿就不会意识到她们的存在。那两个人年龄相仿,大概都是四十来岁,高矮也都差不多,只是一个胖一个瘦一点儿。很多年以后,柳絮还会记得那个瘦一点的女人留给她的第一印象——看人的眼光冷冰冰的,嘴角却似有似无地向上翘着,绽出一朵菊花似的微笑,居然极其自然。她们一上来便像见到了亲姐妹似地一左一右地挽住了柳絮,问:“你是柳总吧,一诚拍卖公司的柳絮总经理,对吧?”柳絮多少有点发怔,她想把脚步停下来,却没有能够做到。她一边被两个女人挟持着朝外面走,一边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柳絮不想就这样被带走,终于有点费劲地站住了,一左一右地朝那两个人看了一下,问:“你们是...
╭╮╭╮ ╭╮╭╮⌒ ∨(﹏).. (﹏)╰╯停车暂借问作者:钟晓阳第一部 妾住长城外"奴是那二八满州姑娘,三月里春日雪正溶,迎春花儿花开时……亲爱的郎君你等吧!……"满州国奉天城里有一条福康街,福康街上有一座四合大院。这宅院门前是两棵大槐树,槐叶密密轻轻庇荫着两扇狮头铜环红漆大门。门内两旁是耳房。从大门起,一条碎石子径穿过天井迤逦到正厅。天井花木扶疏,隐隐一带回廊透出兴趣无限,东西两侧分别是左右厢房。而歌声是从左厢房里袅袅传出,十分闺阁秀气,委委弱弱的一丝儿,像绣花针曳着绒线在园中刺绣,却又随时要断。房门"呀"一声开了,赵宁静一手卷玩着发辫梢,一手拨开珠帘跨出来,恰见乳母江妈在打扫偏厅,手里一把鸡毛掸子孜孜拂着桌椅,虽不见得有什么尘,可还是让人觉得尘埃纷飞。...
《二把手》作者:唐达天【实体书精校版】二把手就像古时大家庭的二房,上要小心大房的淫威,下要提防众小妾的中伤。编辑推荐囊括了官场的全部智慧与权谋,放大后就是整个官场的图景。二把手就像古时大家庭中的二房,上要小心面对大房的淫威,下要提防众小妾的中伤。二把手是一个很尴尬的位子,你不能太张扬,也不能太无能。太张扬,会对一把手的权威造成威胁;太无能,一把手觉得有你无用,三四把手就会趁机篡权夺位。怎么把握,关键在于心智。二把手的理想是取代一把手,一把手的理想是当上更高层次的二把手。世上没有永远的一把手,也没有永远的二把手,只有永远的权力和欲望。二把手的生存之道,囊括了官场的全部智慧与谋略,放大后是整个官场的图景。内容简介...
《说好一言为定》作者:西门【完结】出版社: 百家出版社出版年: 20078页数: 278定价: 25.00元ISBN: 9787807037040文案:小说描述了美院毕业生西门离奇神秘的感情遭遇,已拍成电视剧(剧名《一言为定》),由佟大为、左小青领衔主演那些日子我无缘无故将头发披散下来,以便我的眼睛可以在额发后面毫无顾忌地测量我和女人之间的距离,希望从她们擦身而过时的脸上找到一些痕迹,找到可以直达那个怪梦的路径。然而,从未发现哪个女人或是女孩跟那个梦有一丝一缕的联系《说好一言为定》1九月微凉的空气像水。困在它的中央,我仿佛是一个蹩脚的泳者。我无法摆脱来自神经末梢的痉挛,就像无法摆脱呼吸。在此之前,我从未告诉过别人我有一种幻觉,总害怕那些潮湿的空气有一天会突然坚硬得凝固,所以在睡觉的时候也不敢尽情地做梦。有些时候,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冒险凫渡白日或者黑夜里那些梦的深潭,并且企图在它们无序而诡异的纹路之中...
《二刻拍案惊奇》作者:凌濛初序序尝记《博物志》云:“汉刘褒画《云汉图》,见者觉热;又画《北风图》,见者觉寒。”窃疑画本非真,何缘至是?然犹曰人之见为之也。甚而僧繇点睛,雷电破壁;吴道玄画殿内五龙,大雨辄生烟雾。是将执画为真,则既不可,若云赝也,不已胜于真者乎?然则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则已矣。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夫刘越石清啸吹笳,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今举物态人情,恣其点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此其奇与非奇,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则为之解曰:“文自《南华》、《冲虚》,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凭虚公子,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不知此以文胜,非以事胜也。至演义一家,幻易...
- 手机访问 m.---¤╭⌒╮ ╭⌒╮欢迎光临╱◥██◣ ╭╭ ⌒︱田︱田田| ╰--╬╬╬╬╬╬╬╬╬╬╬╬╬╬╬版 权 归 原 作 者【风月宝贱】整理附:【】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台湾文献丛刊·第 287 种】《使琉球录三种》 (明)陈侃、萧崇业、夏子阳 撰《使琉球录》 (明)陈侃等 撰 [沉思曲] 61K 09-05 12:36 24《使琉球录》 (明)萧崇业等 撰 [沉思曲] 121K 09-05 12:32 17《使琉球录》 (明)夏子阳等 撰台湾文献丛刊 【第 287 种】 使琉球录三种 .作者:陈侃、萧崇业、夏子阳 .原书页数: 0290 页 ●书籍简介 第二八七种「使琉球录三种」...
- 手机访问 m.--¤╭⌒╮ ╭⌒╮欢迎光临╱◥██◣ ╭╭ ⌒︱田︱田田| ╰--╬╬╬╬╬╬╬╬╬╬╬╬╬╬╬版 权 归 原 作 者【annie23】整理附:【】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风之王国 KAZENO OHKOKU 毛利志生子 SHIUKO MORI 插画/增田惠 时值西元七世纪。虽然是唐朝皇帝李世民的侄女,却以商人之女的身分被扶养长大的翠兰,有一天突然被皇帝召见,并向她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愿意成为朕的女儿,并嫁到吐蕃国去吗?」。必须前往边陲之地吐蕃(现今的西藏)接受政略婚姻的翠兰,只身跨上马背迈向旅程。然而在前方等待着她的,竟是意想不到的事件、令人心动而不安的邂逅以及……穿梭历史中的女主角翠兰,即将展开一场史诗般的冒险故事!...
陳獨秀全傳(上)唐寶林 著《陳獨秀全傳》唐寶林 著?香港中文大學 2011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461–0(平裝) 978–962–996–473–3(精裝)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852 2603 7355The plete Biography of Chen Duxiu(in Chinese)By Tang Baol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ISBN: 978–962–996–461–0(paperback) 978–962–996–473–3(hardcover)...
施耐庵绝代奇才 作者:孙昌宇一 钱塘县青衫灭门 淮泗道翠羽喋血二 觅豪客书生闯乌桥 斩红妆教主排貔貅三 刘福通弹铗述痛史 施耐庵洒泪祭亡灵四 娓娓道来国仇家恨 依依离去茜裙寒月五 获秘笈全凭扁舟一叶 说兴亡笑谈笔剑双绝六 荇水荷风柔情万种 嫉心诡谋恶浪千叠七 侠书生星夜走长堤 莽总管月黑奋短兵八 界首镇恶道索秘笈 汪家营神偷戏魔头九 析警诀书生踏北斗 觅神工旗首走东台十 白虎堂上铸大错 红灯影下宵小灭十一 宋碧云城厢施绝手 金克木荒郊逢魔劫十二 老雕工单斗金钟罩 髫龄女双殉红巾义十三 荒村野店侠影如烟 鬓乱钗横杯酒似血十四 龙港河惊逢屠龙手 武家庄忽遁江湖客十五 乡场新聚群雄惊异变 梁山旧事孤女誓苍天...
书名:幽灵列车与金平糖作者:瑞智士记在七月如火的骄阳暴晒下,“骗人!糟透了——”上初二的有贺海幸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她准备跳进当地的地方铁轨自杀,可那条铁轨已然废弃……海幸策划的完美“骗保”计划也被迫更改。这时,一名自称莉伽雅的女高中生出现在了她的眼前。莉伽雅在他加禄语中是“幸福”的意思。有着幸福之名的少女邀请海幸前往废弃铁路前方。那里孤零零地停着一辆废弃的列车。“咱来把这条废弃铁路复活成为‘幽灵铁路’给你看!”莉伽雅如此宣言道,海幸那前途未卜,不可思议的夏天也随之开始……水灵,伤感,捉摸不透的少女们在这个夏天上演了一出青春的空想故事。☆、序章寂静的无人车站的月台。金平糖。向日葵田。还有,那辆废弃的电车。...
《斯大林的秘闻》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译者李惠生等文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每天都念着他的大名醒来。他的大名整天挂在广 播员的嘴上,鸣响在歌曲中,出现在所有的报纸里。他的大名被授予工厂、农庄、街道和城市,作为最高奖赏。在那场最修烈的战争中,战士们喊着他 的名字投入殊死的搏斗。在战时,斯大林格勒流尽了鲜血,损失了全体居民, 大地变成了布满弹片的废墟,但是,以他命名的城市,没有向敌人投降。在 他安排的政治审判中,受害者临死时高呼斯大林万岁。在集中营里,根据他 的旨意驱赶来的千百万人,让江河倒流,在极圈内建起城市,数以十万计的 人死亡,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画像下完成的。在这个辽阔无垠的国家,到处 都是他的雕像和塑像。斯大林的巨像曾耸立在伏尔加一顿河运河旁,那是他的囚犯们开凿的又一条运河。发生在这座铜像上的一个故事,简直是对那个时代的嘲讽。 有一天,铜像看守人吓坏了,因为他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