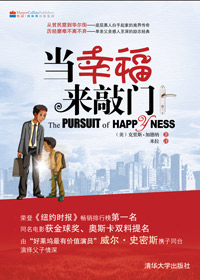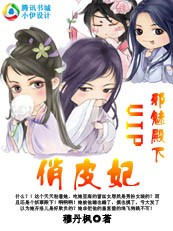当幸福来敲门-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后我只好“曲线救国”,换了一套行动方案。我知道她夜里睡觉时,会把假眼放在一个盛着液体的小罐子里,保持假眼湿润。我计划在早上她没醒的时候,就把假眼拿走,然后中午时,再偷偷送回来,通常她要在中午过后才会起床。
那天早上一切进展顺利,我到了学校,几乎等不及一个个轮到自己再做展示了。之前,谁都没有把假眼带到学校过的。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几乎抑制不住自己脸上漾起的得意微笑,马上就要到我大放异彩的时候了。
突然间,走廊里传来一阵阵尖声叫骂,开始还听不太真切,但很快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是在喊我的名字,“克里斯!还我的眼睛,看我不打烂你的屁股。把眼睛给我还回来!”
班里的人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在我身上,都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
又一轮叫骂开始了,比刚才更凶狠,“混蛋东西,把眼睛拿回来。给我眼睛。看我怎么收拾你,小贼娃子!”
接着,希斯姑妈一把推开教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门口,头发披散着,脚上只穿着拖鞋,随意披着家常外罩,气得浑身都在哆嗦,她用那只好眼扫视着大家,另一只眼框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把眼睛还我,混蛋东西!”她大声咆哮着,老师和同学们都惊呆了,大张着嘴巴,不明白这人是谁,为什么找自己的眼睛。教室里彻底乱作一团。
我尴尬万分,步履沉重地走上前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口袋里掏出了她的假眼。她用那只好眼瞅了瞅我手心的玻璃假眼,一把拿走,当着全班人的面,把假眼塞进了眼眶,转身走了,一路上还骂声不停。
我估计老师要晕过去了,有个小女生当时就吐了,显然谁都没见过这种阵势,也没见过有人这么当场装假眼。
家里的反应倒是没出我所料。弗莱迪当然又要大发雷霆,“克里斯,你要再敢动希斯姑妈的眼睛,看我怎么收拾你,我非打得你一个星期坐不下去。”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来让我受皮肉之苦,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还是回到学校让我更难以忍受。很长时间之后,我都是学校里的笑柄,关于希斯姑妈和她的假眼的事孩子们谈论了足足有几个星期不止。但我还是撑过来了。除了捅了这么个漏子之外,我在学校里过得还不错,那里有我喜欢的东西,也有我需要应对的挑战。而且,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经常泡在图书馆,看那些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经典小说,我甚至对历史也萌生了兴趣,而且觉得数学也是趣味盎然,我喜欢解决那些是非对错的问题。
而我家里那些事情,很难讲清究竟孰是孰非。
* * *
在过去几年间,妈妈出狱后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总想理解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她是否不再像从前,还是从未改变,她真实的想法究竟是什么。老家伙弗莱迪是我们所有人的噩梦,他是镣铐,是锁链,让我们喘息不得,同时他还挥之不去,欲罢不能,因为无论母亲怎样逃离这个家,怎样把他关在门外,发誓不再让他回来,他还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我甚至想,妈妈究竟怕不怕弗莱迪,是不是只要她存在,就可以向弗莱迪证明,就是他夺走了妈妈所有的梦想,妈妈也打不垮,即便他让妈妈两次锒铛入狱,他也打不倒贝蒂·让·加德纳。而且,即便妈妈曾经心灰意冷,曾经难以维系,她也从未表示过。
而且,在对我的态度上,无论我多么过分,她都很少丧失耐心和信心,但她少有的几次发火让我记忆犹新,她不会动粗,但是她言语中所透露的威严和力量绝对胜过皮肉之苦。
一次,她给我带回了一条八美元的裤子,一看就是从金倍尔百货这种地方淘回来的。我瞥见8美元的价签,非但没有感激她为自己如此破费,反而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天,整整8块钱哟,要是我,足够从打折柜台买上鞋子、裤子、衬衫,再加上去看场电影了。”
妈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让我不寒而栗,她拿起裤子,说了一句:“这条8块钱的裤子,你实在不配穿。”
一切为时已晚,我惊惶失措,知道自己和这条裤子从此无缘。在那之后,我对自己的言行倍加小心。我不是为自己开脱什么,只是觉得弗莱迪用词刻薄恶毒、说话不假思索,这种恶习我已经有所沾染。实际上,我们兄妹几个都有这种倾向,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出言不逊,口无遮拦。时至今日,我还要对自己的言行多加小心,慎言慎行,即便如此,有时还会出言不逊。
妈妈用她自己的方式告诉我,语言和沉默都可以充满力量。小时候那次偷爆米花,她用电话线对我一顿狠抽,可在这之后,我又想有小动作的时候,她投来的失望眼神就足以让我心有余悸。
13岁时,青春期萌动,我长得又高又壮,也想摆酷,决定去打折店顺一条裤子,显摆一下自己,同时觉得自己身手敏捷,应该不成问题。这种掩耳盗铃的想法绝对愚蠢,我一心想着怎么样才能得手,把赃物藏在裤子里面溜走,就没有想过自己这种打扮的学生娃怎么会不引起店家的注意。
我刚迈出店门,店长就一把钳住了我的肩膀。我被抓了个正着,还夹着课本,人赃俱获。店长对我一顿数落,不仅如此,车上下来两个白人警察,把我直接带到警局。我如坐针毡,准备和家人通电话,接下来是妈妈焦虑不安地赶来接人,还有那个醉醺醺的继父一同赶到。可是当值班警员拨通电话,听到的是弗莱迪的声音,可这次好像情况有所不同。警察和弗莱迪说明情况,我被警局扣押,需要家人来接我回去,突然警察放声大笑,挂上电话,就把我关进了号子。
他说,弗莱迪拒绝来接我,原话是这么说的:“什么?让这杂种就烂死在局子里吧,狗娘养的。”
我嘟囔了几句,从书包里拿出本书来,认真读了起来,希望梅尔维尔的《大白鲸》和自己的全神贯注,能让我平静下来。
结果这又成了这些白人警察的笑柄。一个人问:“你小子还读这个,是不是觉得自己聪明绝顶啊,都这样了,还琢磨什么呢?”
另一个警察学着弗莱迪的腔调说:“让这杂种就烂死在局子里吧,狗娘养的。”
当妈妈和弗莱迪真的来接我的时候,大家一句话都没说,因为我的悔改之意已经昭然若揭,这种关押的经历和如此的反省于我都是从未有过。余光中,我看到弗莱迪脸上的一丝得意让我怒火中烧,险些忘了自己的处境。可是妈妈的失望瞬间让我回归了理智。
当然,我最想做的事情莫过于让妈妈脸上有光,因此这种让妈妈伤心的事情,也会让我一辈子心怀愧疚。
我希望自己演奏小号能让妈妈引以为豪,于是刻苦训练,在青年音乐会上我有所表现,在罗斯福中学乐队里也积极表演。一天晚上,看到我在练习小号,妈妈本来想让我去买东西,结果转念自己动身去了,而只是让我帮着照看一眼锅里的豆子就好。
我满心欢喜,不用出去跑腿,只需要待在家里练习我的表演曲目--席佛的《父亲颂歌》。我那专心致志的特长此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彻底把锅里的豆子忘得一干二净。突然,一股刺鼻的焦煳味道弥漫在房间之中,我忙跑到厨房,豆子已经烧糊,不可救药。
我觉得还是继续练习,等回来之后,报告出现了问题,好像自己一直都在照看豆子,这可能让她消消气。听到她回来,我说:“妈妈,你看看吧,我觉得豆子可能烧煳了。”
只听锅盖咣当一声落在地上,走廊里都是回声,我心头一紧。妈妈每天挖空心思,给我们弄出这点食物实属不易,我却听任豆子烧糊都无动于衷。当时她一定想把我生吞活剥,但还是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缓缓走到客厅,站到我的屋门前,平静地说道:“克里斯,我和弗莱迪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因你而起,我要护着你,可你却连一锅豆子都看不好。”
她话语不多,却字字珠玑,每个字都生生敲在我的脑海之中。我知道自己是自私的,一心只想着自己,自己的演奏,这毋庸置疑。再有就是,她为了我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为了我,不惜激起弗莱迪的一腔怒火和怨气。难道我是他们争吵的主要原因?若真是如此,简直太不可思议。但这个念头立刻又激发了我对他的仇恨,那仇恨的火苗足以将这些豆子烧成焦炭。
妈妈说完这些,就转身离去。回到厨房,打开一罐番茄酱,加了些调味料,那锅烧焦的豆子又神奇地变成一顿美味的晚餐,端上了饭桌。
就我对妈妈的了解而言,她还是一团谜。仅仅有过几次,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有所表露,但转瞬即逝。一天夜里,弗莱迪出门了,我做完作业,电视上正在播放贝蒂·戴维丝的片子,妈妈喜欢贝蒂,我都怀疑这可能是与这个演员和妈妈同名有关。妈妈可不这么想,她觉得自己是喜欢贝蒂的伤感和哲理,情感真挚和强烈。妈妈说:“她演得很入戏,没法不为她动容。”
还有什么能让妈妈开心的呢?估计就是能从事她心仪已久的教师职业。对她而言,就是教好我们兄妹几个,她就是我们的教授,我们的苏格拉底。看到我们终于能领悟她的意思,明白无法识文断字就只能做牛做马,一事无成。当我来到第七大道北街的公共图书馆,本想查一本书或是找个问题的答案,结果却在索引目录中流连忘返,一本接着一本,如饥似渴,在图书馆里泡上一天,没有比这更让妈妈开心的了。她也喜欢阅读,喜欢《读者文摘》,而且让我也欲罢不能。我们俩通常是一字不落地看完一本,并且一起讨论问题。一次,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读者文摘》的旧刊,把其中一首诗抄下来,读给她听,我从未见过她那么开心。以前,我对诗歌的感觉一般,但那首诗是出自英国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笔下,其字里行间的乐感和真情让我动容。妈妈静静地听着,听到头几行的时候,她突然变得一动不动,她可以做到一动不动:让我怎样爱你?我来尽数告诉你。我可以爱你爱到地老天荒,爱到灵魂的深处……
我念到最后一句,“让我究竟怎样爱你”,我看到她眼中涌动着泪花。她告诉我喜欢这首诗,我的发现给她带来了快乐。
* * *
1968年对我而言异乎寻常,仿佛我的宇宙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让我的原子能得以爆炸式地释放开来,我身边更是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这段时期对我意味着生命开始重现色彩,随着我的发现,我的世界不再只有黑与白。5年前,大人们对肯尼迪遇刺所做的反应,或多或少预示着作为少数族裔,当竞争失利将意味着什么。但当一年之后,我和几个同学乘车来到密尔沃基东区的一所白人学校时,我终于亲眼目睹了妈妈年轻时离家工作时的情景,除了门房是黑人,除了零星的几个黑人孩子,到处都是白人,这与贫民区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只有个别店主和警察是白人,而余下尽数都是黑人。仿佛我的肤色就注定了我的身份,注定要被鄙视、低人一等,甚至让人视而不见。更令人发指的是有四个小女孩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被炸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