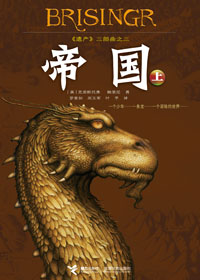柒零人三部曲-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我生命中的另一半,也是另一位主创人,李薇。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慎重考虑,终于启动了网站的开发工作。
一开始,网站的发展比较顺利,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很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的大力支持,很快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得到了同龄人的认可。在欣慰于工作得到承认的同时,飞速增加的访问量也对网站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虚拟主机已经无法负荷正常的运转,自己架设服务器呢,都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我们,又确实拿不出需要的经费。就在我们进退两难的时候,朋友们伸出了无私的援手,那是在网站发展过程中,无数次令我感动落泪的第一次。
几个版主自发发起了捐款,网友们纷纷解囊相助,其中居然收到了四五份1000元的大额捐款,要知道,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如此。聚会的时候,也常常会有朋友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红包,也许伴着一句鼓励的话,也许只是一个理解的眼神,一个温暖的笑容。就这样,“柒零派”像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终于坚强地成长起来了。
在网站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曾经面临两次重要的抉择。一次是我们一直坚持相对“苛刻”的论坛规则,不欢迎不健康的帖子,不欢迎没有内容的帖子,不欢迎与主题无关的帖子,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这种坚持势必会严重影响网站的人气;更有甚者,由于我们删除了一些不符合标准的帖子,有人竟然要把我们告上法庭。还好,经过反复的权衡,在人气与品位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保持了最初的风格,而且,实践证明,正是因为这种坚持,我们赢得了更多朋友的支持,网站的人气仍旧保持了相当可观的增长速度。而那位曾经要告我们的网友,可谓“不打不相识”,也成了我们的朋友。
。。
柒零派,我的精神家园(2)
另一次是网站逐渐创出了知名度以后,可观的访问量和影响力引起了很多企业的注意,希望投资者或是合作者络绎不绝,在是否转型进行更加商业化的行为问题上,我们同样考虑了很多,很久。最终,不愿意我们心爱的精神家园受到太多骚扰,我们还是拒绝了大多数的诱惑,把广告收入始终限制在网站运营成本的五分之一内,宁愿自己贴补,也要保持网站始终追求的方向。当时我提出了一个口号:“再把理想坚持70年!”只要能力允许,我会不断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回首网站风风雨雨走过的七年,付出了很多,但收获更是无法估量的。最大的收获,是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善良、最光辉的一面,看到了无私奉献的一面。曾经有人问我,网友与普通的朋友有什么不同,我的回答是,网友都愿意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更能体现出人心向善,更容易发现人的闪光点。这不是冠冕堂皇的敷衍,而是很多实际发生的事件体现出来的。记得有位网友得了白血病,当时为他回帖的有几百页,后来他来北京治疗,我们把这些回帖全部打印下来,并凑钱买花一起送去,他非常非常地感动。
当然,并不是非要伤感的事情才能触动人,才有价值,我们网站的宗旨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快快乐乐地生活。2006年春节,我们策划了一次拜年活动,所有版主向我家打电话,用数字录音下来,通过后期剪辑,配上不同的背景音乐,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向所有网友们拜年,效果非常的好。今年,我们准备进一步来个视频的拜年活动,让大家开心。
另一个有趣的收获是,我们网站被戏称为“红娘网站”,至今已经撮合了将近二十对七十年代人的百年之好(当然也包括我们两个)。平日生活中的相亲等方式,比较注重第一面外表的感觉,而在网上交流,更多注重内心的东西,注重对性格、生活方式和态度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的感情应该更加稳固,走得更远。
网站本身也是我们的收获之一。做到后来,网站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有了生命,她跟随我们一起在成长,是很多很多的人共同的生命力赋予了她活力,做好网站,跟养育好一个孩子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从对网络的态度,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每一个年代人的区别。六十年代人有相当一部分人使用网络不是很熟练,就算是使用者也往往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工具;八十年代人呢,是很依赖于网络了,但是他们更注重网络的娱乐功能;而七十年代人更注重论坛等交流方式,通过网络来思考、感悟,实现更深层次的要求。
对于我本人,无论工作还是业余时间都和网络摸爬滚打在一起,网络如今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工具了。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上网未必比别的方法更好,比如了解新闻,上网的方便程度未必胜于看一张报纸,但是我还是会选择使用网络。说起来,今年我与夫人去马尔代夫度蜜月,那一个星期的时间与网络完全隔绝,真的是感到非常别扭,呵呵。
一说起网站,总是感觉说不完的话题,其实无论多少笔墨,也很难描述全部的感受呢。毕竟,网上的东西,还是要靠网上来体验,多到“柒零派”去坐坐吧,相信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那里,永远是我们七十年代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生于70年代(1)
这些天来,心情很是怀旧,无论是听的歌,还是看的书、写的东西,都逃不开回忆。恍惚中,仿佛看到一种泛黄的色调正像雾气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弥漫了我的生活。突然发现,我竟然将前段时间充满春意的桌面换成了一群迁徙的大雁掠过夕阳。“我是不是老了?”这样问恐怕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但是,不这样问又能怎样呢?
曾经非常迷恋“代”这种说法,习惯称自己为70年代人,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自我定位始于一帮年轻学者所著的《第四代人的精神》,到了李皖的《这么早就回忆了》一文,这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达到极至,最终被一本《六十年代气质》的书彻底点燃。
非常认同李皖对“代”的定义,他在《这么早就回忆了》中讲到:“代,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代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命运。从一开始它表现为一种共同的经历;随后它表现为对这经历的无可奈何,以后的人生都被这经历所左右。”向前看,是60年代人已经不太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向后看,是80年代人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作为70年代人,我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吗?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吗?我们是否也在对其无可奈何呢?
回忆一下吧。
在文革前后出生,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几乎为零,稍大一点的还会在记忆中残留一丝伟人去世的片断,稍小一点的则将更多的敬意留给了为我们打开国门的小平同志,所以,降生于革命激情过后的萧条时期的我们,恰好错过了最有可能成为英雄的年代。我们的父母在生下我们的同时,已经开始怀疑和思考生活本来的意义,这种迷茫一直伴随我们的童年和少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生理的成熟期与父辈心理上的成熟期出现了惊人的重合。命中注定,一开始,我们就错过了最真诚的信仰。
童年的欢乐是每个人最最清晰的记忆,70年代人尤其突出。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成长,每一位同学都曾写过这样的文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似乎不这样开头就写不下去。总是觉得21世纪我们都共产主义了,到那时什么机器人、宇宙飞船还不随处可见,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绘声绘色地描写过这样的场景:2000年回到母校,聆听机器人为我们介绍学校的现况,其实这都是上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当。做科学家是最普遍的理想,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最不济也要做一名战斗英雄,这样的理想说出去才会有人赞许,不过我们确实也是那样憧憬的,当然这种憧憬在进入初中后就彻底破灭了。
那时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我们会聚集在一起看动画片,因为那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我们会放学以后不回家,不过是去田野、工厂捉迷藏,而不是去网吧。我们能够准确地分清小麦和稻谷,不只一次在夏天的晚上看到过流星和萤火虫。我们至少有十几种可供消遣的游戏,当然乐器、书法、芭蕾之类的不在其中。我们学习舍身扑火的赖宁和身残志坚的张海迪,男生传阅金庸和古龙,女生崇拜三毛、琼瑶,还有汪国真、席慕容、北岛、海子,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名人,却又无一例外都不是娱乐明星。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对现在的小孩来说新奇无比的故事,也就不一一道来了。因为生活相对稳定,只要父母是正式职工,什么都是国家统包,既无下岗失业的担心,更无医疗费无处报销的窘迫,这样一种稳定的生活让我们远离了贫困,暂时也还没有追求小康的欲望。因此,70年代人的童年有着太多的童趣。不过,读书的压力还是存在,在印象中,我老有做不完的作业,特别是小学,老师很变态,常常叫我们把词典里从第×页到第×页的词抄两遍,当时我们恨不得把词典裁掉一半。“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像我一样当工人。”每次不听话都会招来父母的这番教育,现在想想,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当个工人没有什么丢脸。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生于70年代(2)
60年代生人其实是父辈的延续,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代。他们的启蒙教育浸透了革命权威,他们的成才教育弥漫着革命激情,虽然他们也怀疑,也迷茫,但是和父辈一样,他们具有最纯洁的思想、最真诚的心灵、最狂热的情感,他们真诚地相信,在主义的指引下,他们能左右历史的发展,达到理想的彼岸。但是,父辈具有的革命浪漫主义他们却没能学会,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真诚的代价。因此,嘲弄践踏曾经奉为真理的理想,便成为60年代生人最最可悲的变化,也成为60年代生人与父辈在遭受了相同命运之后出现的最大的不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充满挫折的心理背景下长大的。虽然我们没有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但是,大概是智力开发较早,我们毫无障碍地领悟和接受了父兄的情绪。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妄图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改变世界是可笑的尝试。我们无师自通地选择了实用主义,同时也得到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对这种倾向的下意识鼓励,因为这也是父母在改革大潮中摸爬滚打琢磨出来的心得。我们深深明白,物质比精神更实在,所以,80年代后期形成主流的商业文化被我们迅速认同。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已经习惯从效率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我们嘴上不说,但却从心里赞同:奉献与牺牲在一个高效率的社会中是根本不需要的,如果每个人都较好地照顾了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协调这样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生来善于走捷径而较少有道德上的障碍。至此,中国五千年的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划上了句号。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至少不是效率最高的选择,在这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需要的是智慧、活力、创造力,是高效率、高智商、高素质的精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