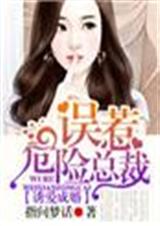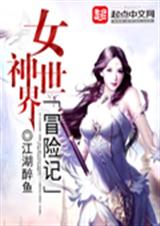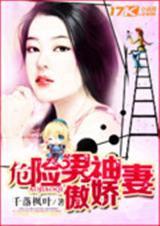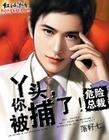思想的历险-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世纪50至60年代也许是它的最低谷。那今天的《泰晤士报》呢? 现在这个时代要好一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不会为资源发愁—即使你没有时间写作,不能做到四处旅行,见很多的人。作为一个编辑,这个时代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我们要做好一份报纸是不缺资源的。在英国媒体业和英国社会中,我们的道路很明确。我们的信心和依靠商业生存的能力,都能够让我们做出一份伟大的报纸。 被任命为《泰晤士报》总编,是你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吗? 。。
访谈(4)
这算什么问题,这当然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不过我想我这一生有很多转折点。我现在41岁,接受这一职位并非我走下坡路的开端,我很高兴获得这一任命。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媒体,这个职位远不如这个地方有价值,吸引我的是这个组织,而不是职位本身。但就个人而言,我很自知,扬名并不是我的驱动力,我自问扬名并非我所好。因此,它之所以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是因为这里能够提供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就新闻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感觉美妙的经历。 那对你来说,第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成为一名copy boy吗? 呃,我的第一个转折点应该是我出生吧(笑)。我想,远赴中国,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在那里还遇见了你的妻子。 对,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职业生涯来说,这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当时是1985年,正如你们所知,中国当时非常令人吃惊,到处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真的就在你眼前发生着变化,每个月都会不一样,你能感受到这些。我刚到中国时,大街两旁的扬声器里还播放着音乐,马路上时有马车来往,中国人还穿着中山服。现在去中国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原来是什么样子。我想我当时真的很幸运。回顾之下,我发现自己那个时候就在中国非常幸运,虽然问题还很多,但是人们—邓小平等领导—正在去尝试,不管是在艺术上、文化上还是经济上,甚至包括政治上,一切都在前进着。 这些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了解了中国,还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人民,我还了解了人们心中的愿望。人们想发展自己,想尽可能地挖掘自身的潜力,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有舒适的物质条件,但他们也想要个人的机会。当时我才刚满23岁,我最幸运的就是能够在当时去到北京并呆了一段时间。 随后你又去了东京、美国,在亚洲和在美国的不同经历分别怎样影响了你? 日本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给我的影响还要大一些。我很喜欢日本,我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的泡沫时期,也很令人惊奇。这是两个真正不同的文化。很大一个问题是,我在中国时,让人们办事非常困难,而日本就是什么都很正常。这两个国家给了我很不同的经历。总的来说,在亚洲的经历感觉很矛盾,人的外表很相似,社会却截然不同。 在美国的经历也是如此。人们在美国外面看美国,观点就远异于有过美国经历的人。尤其是欧洲人,左翼比较多,反美倾向较强。我不知道人们对美国了解多少,我很喜欢这个国家,我的两个儿子就是在纽约出生的,我对那里怀有感情。两地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住在伦敦,但在伦敦之外,我更愿意去北京和纽约。 从你17岁到41岁,过去的24年来你认为新闻业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技术。技术创造了信息,技术也影响了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你需要改变报纸,就是因为互联网等新技术造成的冲击。25年前的报纸不再与今天的报纸相同。你需要知道观众都知道什么,你不去了解,就不会有人买你的报纸。 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改变了吗?你知道,以前他们的形象包括反政府、反商业,但同时他们受教育程度又不是特别高。但今天,一切都改变了。你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的受教育程度还是那么低(笑)。我想有的新闻工作者仍是这样,但是我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被高估了。新闻业惟一没变的,是新闻工作者要做到有批判的眼光,不能偏听偏信,你需要对其做出评估,在做评估时你得做到公平,并且要强硬,以前的政治新闻编辑记者就是这么干的。但和旨在提供分析和新闻的新闻业相比,两者间有很大的不同。我很希望我的编辑手###变得更客观一点,能够最快地找到和挖掘事实,向事实发起挑战,而不仅仅是刻意地将自己变得不同。 最令你沮丧的经历是什么? 沮丧?最大的沮丧,是当我发现自己不能够对自己满意。我很少会为别人感到沮丧,我一般会对自己感到沮丧, 你常常对自己要求很苛刻吗? 是的,你不得不这样做。你常常会在别人不明白你想要做什么时感到沮丧。我认为问题肯定出在我的影响力不够以及自我表达的方式上。我认为真正的沮丧比较微妙,比较个人化。但我觉得沮丧也会变成动力,它会让你向自己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你常感焦虑吗? 是的,不过我不是一个神经质的人。 我们俩都认为你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是这样吗? 呃,是的。你要是不再提出问题,你就不再能获得答案了。 那你是个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 我?相当乐观。这既是天生的(by nature),也和家庭环境有关(by nurture)。 不管是偏左还是偏右,很多总编辑对政治、商业、文化都有很强烈的观点。你对世界的观点是什么? 我相信自由市场,相信个人自由。我觉得很多人的观点是殊途同归的,尽管有人说自己是右翼,有人自称是左翼,或者是社会主义自由派。人们倾向于将自己进行分类,你的观点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什么。在英国,情况似乎是这样,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那你就是左派,你就该买《卫报》,如果你看《泰晤士报》,那你就是右派。我不管这些。
访谈(5)
那就是说,你认为今天的政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认为,人们所意味的政治已经变成了党派政治。我考虑政治更多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个人之间的关系组成了社会,政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觉得政治就是支持某个足球俱乐部。我尽量避免犯这种幼稚的错误。我总是认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很微妙、很复杂的。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理查德·桑布鲁克
理查德·桑布鲁克(Richard Sambrook,1956-),BBC新闻台台长。 BBC新闻台有2000名记者,除英国总部外,在全球驻有56个分站。BBC新闻台提供电视、广播和网站新闻服务。 1980年,从伦敦大学波别克学院毕业的政治学硕士桑布鲁克,从一份地区报纸记者应聘为BBC新闻广播节目组的助理编辑;之后他开始负责国内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和编辑;数年后升为高级制作人和晚九点新闻的副主编,赴远东、中东、欧洲、俄罗斯和美国等地制作节目,并参与了英国三次大选的专题报道制作。桑布鲁克还于1989年制作了BBC关于柏林墙倒塌的新闻报道。 1992年,桑布鲁克成为BBC新闻中心的新闻主编,1996年升任新闻中心主任。在其任下,BBC海外新闻报道能力得到了大幅拓展,全球重点地区都设立了BBC的分社。桑布鲁克自1999年12月起担任BBC新闻台副台长,2001年初升任为台长。2000年4月至10月间BBC总台长格雷戈·戴克对全公司进行大调整时,桑布鲁克曾任BBC体育台代台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处于十字路口的新闻业(1)
“广播电视新闻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理查德·桑布鲁克在2001年11月4日的伦敦皇家电视协会会议上催促他的英国同行重新思考新闻业的发展方向。4个月后,他在华盛顿的记者俱乐部伤感与兴奋交叠地回忆起少年时对美国新闻的印象,那是肯尼迪遇刺、越南战争、登月行动与水门事件的年代。 作为BBC新闻台台长(Director of BBC News),桑布鲁克掩饰不住他对于伟大历史事件的偏爱,尽管不长的职业生涯已允许他见证其中的两次。当柏林墙拆毁时,时年34岁的桑布鲁克连夜飞往柏林,领导了BBC对该事件的报道。“而‘9·11’事件将再一次改变新闻业的面貌”,一年后,桑布鲁克仍坚持他最初的看法,“这是过去10年中最激动人心的变化,它将重新激起观众对于国际新闻报道的兴趣。” 从2001年初开始,桑布鲁克负责指挥BBC遍布全球的57个分支的2000多名记者。这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电视新闻网,它已经有70年的传统了,全世界每周有亿人在收听BBC的广播,有2亿人在收看BBC世界新闻台,数以千万计的人访问它的网站。而46岁的桑布鲁克无疑以此跻身于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新闻领袖的行列,尽管他总是过分谦逊地说,“我从不谈论与思考自己。” 在BBC新闻大楼6层的办公室里,桑布鲁克张开双臂迎接我们,笑容灿烂而真诚。他那蓝色衬衫与红条纹领带的穿着与办公室的陈列一样简单,而他讲话时的认真与谦虚态度则让我怀疑眼前这个人是否就是那位热衷于“伟大时刻”的记者。他表情严肃地倾听着问题,甚至记录要点,以使回答更为切中要害。我得承认,桑布鲁克先生不像我最初想像的那样激动人心,他的回答清晰、准确,却过分谨慎。但是一切谦逊都掩盖不住他对新闻业本身的信念以及试图领导BBC新闻台重新定义新闻概念的热忱。 “今天参与电视节目偶像评选的35岁以下的英国青年,比参与英国大选投票的人数还多。”桑布鲁克感慨在“历史已经终结”的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闻界沉醉于对戴安娜之死、莱文斯基这样的绯闻与琐碎新闻的追逐之中。令人吃惊的是,桑布鲁克并未指责观众趣味的庸俗化,他相信我们身处信息革命的中间地带,观众拥有前所未有的内容选择。“这是一个新闻业面临的新环境”,他解释道,“而严肃新闻节目的关键问题是,它们未能将这个更为复杂的世界向观众解释清楚,所以人们转向那些更容易理解的区域与琐碎的问题。” 在英国(甚至全世界)的新闻界中,很少有人比理查德·桑布鲁克更热心地相信“9·11”将再次改变我们的新闻价值取向。恐怖事件再次勾起人们对于国际新闻、陌生的阿拉伯世界的兴趣。或许新闻人都会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将重建新闻业的公共责任,但私下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相信,这可能仅仅是一次重大的灾难而已,人们的兴趣将很快回归最初的水平。在英国的新闻界,或许只有《镜报》的皮尔斯·摩根堪与桑布鲁克对“9·11”的热忱匹敌。这家英国第二著名的小报(仅次于《太阳报》)的传奇性主编语惊四座地宣称,要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严肃的新闻报道上,更多地探讨国际事务,而不是像对手《太阳报》那样目光短浅地仅仅刊登“三版女郎”。 “我们谁也无法预言,恐怖浪潮会持续多久,但我们必须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更全面与公正的新闻报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