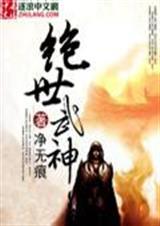芙蓉-2003年第3期-第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说法——加上几句英文,大家别介意,因为这是人家的事;咱们中国的事,全用中文——就是说“ident”是指同一性、同一律,这个东西碰巧就是自己那个样子。但是,当我们提到所谓的文化认同时,这个“ident”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我们谈到某一种文化身份的时候,往往不是在说“我自己是谁”,不是这个问题,不是“是与不是”,而是在说“你想当什么”,“你想成为什么”,“你要什么”,“你希望你自己变成什么”,事先为自己预定了一个身份。就好像现在的你不是你自己了,跟你自己一点都不像,但是你绝不是这模样,所以你想将自己预定东西套到自己身上,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点像我们要实现伟大的理想,长大了要当什么的意思,都是一些自己想象和幻想。除非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其绝大多数是一种自我表扬,是一种资格认证。就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为自己定位的时候,全都是好听的话,每个民族都说是世界上最勤劳勇敢、最智慧的民族。所以,当你说什么是你的“ident”的时候,我就是不太清楚,你是在说“我是谁”,还是在说“我想是谁”?这两个态度是不一样的,我是没有听明白。
杨 炼:我觉得更多的潜台词常常是“我不想是谁”、“我怕是谁”。我现在是穷光蛋,我想成为百万富翁,这还是一个比较容易实现的选择;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所要真正思考的,是你要清楚你想要走的路,想要成为哪个模式,这是很难的一件事,你要有相当深的认识才行。而更多的人是出于恐惧,出于实用,不想当穷人、不想当失败者、不想当中国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意思。
刘索拉: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是必须做贡献。比如我们音乐学院出来的人就必须得奖,要不然就得卖钱,要不然就得成功,特别缺少一个自我。其实“我是不是高兴”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忙了半天全都不高兴,你努力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都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全都是在解决别人怎么说、别人或者社会怎么看你的问题,你永远都不会高兴的。拿作音乐来说,因为我们的教育都是功利的,所以目的很不单纯,作音乐是为了进哪个乐团,或者是最后能写出什么来。比如贝多芬写了九个交响乐,你是不是能写第十个呢?你写不出第十个,你就不是音乐家。所以,我们不是在享受音乐,而是必须作音乐,“作”和“享受”是有很大区别的。
出国后,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许多普通村里头的音乐家,可能都要比我们音乐学院出来的音乐家更明白音乐。我有一个朋友,唱歌剧的,拿了个金奖,他就说:“我就是为了拿奖去的,虽然我只能唱那么几首曲子,但我练得精;而国外的歌唱家拿不着金奖,是因为他们懂得的音乐比较多,兴趣太分散,什么作品都喜欢唱。”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音乐教育,培养的不是一个人对音乐的真正兴趣和敏感度。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美国、那些英国作家们,他们就不太考虑什么“移民”的问题。当时,在国外,看到一个村子,我就特别希望一辈子在这个村里不出去了,可以在村子里的教堂中做点音乐,或者给那个村子写点文章什么的。有些美国、英国作家,他们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当然,国家不一样,可能人的命运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想的是这种自我的满足。
杨 炼:应该说,在国外的中国诗人还是相当幸运的。因为人少,又代表了相当大的一个语种,所以在所谓的国际性的一些诗歌活动上,被选中参加的机会还是很多的。相比而言,英语诗人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这往往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中国的诗人在国际上非常成功。其实我自己清楚,那些都是假的,与其说是国际上承认你的诗歌质量,不如说是为了装饰他们的国际化而挑选了你这块面具而已,若换一块面具效果也是一样。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我“坐着说话不腰疼”,自己活跃在国际上,这个诗歌节那个诗歌节地跑来跑去,完了之后又跑这来贬低它一下,显着自己更高一筹似的。其实还真不是这样,有过了这么多经历后,我确实把这种表面的成功看得很轻。原因在于,跟攒一个句子,最终把你的感觉攒出来、攒到位的那种快感比起来,那些所谓的成功的快感弱得实在没法比。
赵汀阳:没错,成功没有一定的模式。有人可能追求市场的成功,有的人千篇一律地追求获奖、得奖的成功,也有人可能像你一样专门折腾语言。刚才你讲了很多东西,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你怎么用中文强迫、折腾他们的英语。正像你说的“诗歌是黑暗,但我在写,这就是光”,像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特别有趣,因为其中有某种叫劲的快感,这也属于一种成功。
杨 炼:我昨天参加了一个关于我的诗歌作品的讨论会,那种讨论气氛和讨论层次可以说令我是百分之百的失望,甚至说是绝望。因为所有的批评,基本上都还在谈论什么主题啊、内容啊,什么哪一个比喻啊等等,根本没有在诗歌形式之内的批评,根本没有语言之内的批评。比如这个作家他是怎么跟这个语言折腾的,根本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对诗歌进行讨论。我不得不说,关于诗歌的真正到位的讨论,只是在我和我的译者之间进行的。因为别的读者可以看两行看不懂扔一边就算了,只有译者他是不得不看完并且要弄懂你要说什么的人,然后他才能翻译出来,否则的话他根本翻不了。所以,我和译者的讨论常常是非常细节性地介入语言和形式,讨论这个语言和形式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一直强调一个“必要性”的问题,就是说不管这个形式看起来多么花哨,或者多么朴素,它和它的内涵之间如果没有那种“必要性”,那么这个形式就是多余的,哪怕它简洁到“极少主义”,它也是多余的。
邹跃进:我比较认同的是杨炼刚才说的,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不管在时空中间怎么变动、变换,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保持一种能够'感受的能力。他刚才批评了一种现象,认为如果没有感受到自己经验上的变化,就创作不出鲜活的作品来。我们做评论的考察问题,首先要找到一个自身的结构。可能创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每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但最终我们自身要有一个结构,我们要看你个人的经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上。刚才有人对你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一种历史主义的或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可能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更多的还是'善于'谈一些个性化的东西。
杨 炼:其实也不是。我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觉得对于一个好的评论家来说,'他的工作'实际上是对一个作品的再创作。你要评论他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就要反映他。简单的说就是,你所说的所有的社会、历史,包括地理等等这些东西,如果在我的诗里不存在,那么对于我来说它就不存在。当然,对于这种诗性的存在,如果你只是从简单的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只能得到一些简单的、初级的印象。作为一个创作者,如果我们被批评家们不得不简化了,那么算我们倒霉;如果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简化了,那么就是你的活该了!
邹跃进:其实我是说评论家评论要有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必须把你放在跟你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构成关系中,才能考察你的价值和意义。你所说的这种由于经验变化带给你创作上的影响,又使你更加坚定地认同了你的中文性,非常有启发意义,这可能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对话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
赵汀阳:我觉得国内有一个倾向不太好,老是“东西方”啊,“南北方”啊,“中国、外国”等等谈得特别多,比较空洞。而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信息共享的时代,无所谓什么西方或中国、古代或现代。你可以选择一个合适你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西方,也可以是东方,关键不在于地方,而在于感觉,你能否有充分的敏感去感受这个社会,然后还能有能力用一种语言方式去描述它,描述今天的一种感受。拿今天的艺术和诗歌创作来讲,跟今天的社会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关系越密切、越有创造力的诗歌艺术,越是好的诗歌艺术。那是我们无法用任何以前的判断模式去谈论的诗歌艺术,是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发展批评语言的诗歌艺术。所以我就一直本着这么一个想法,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能和一些诗人和艺术家朋友在一起,我觉得能找到很多共鸣。
我觉得,这次我们谈到很多概念性的关键词:一个是“认同”,一个是“漂流”,还有就是“背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关系链,而且相互间可能都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很复杂的交织的关系。比如说“认同”,有社会性的认同,还有自我个人的认同。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农村来打工的孩子,刚到城里,他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一个原初的朴素的他自己而已,谈不上什么“自我”,因为他就知道来工作、来谋生,最简单的生存。那么,如果这个人获得了一定的教育,开始学习,他就可以获得一种认同。很多国内的一些艺术家、诗人到海外漂流,主要是获得一种经验。在当代国际化的背景下,很多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是源于一种文化的碰撞,而交流是碰撞的前提。不同地质的文化相互碰撞才能产生火花,产生一种新鲜的东西、新鲜的文化、新鲜的精神、新鲜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漂流可以获得一种背景,在不同地方的漂流会有不同的背景。拥有这些背景之后,你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自我”,并以此区分你是不是“他者”,在“他者”和“自我”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带来成就感和不断的超越自我,以及获得另一种的认同。那将是一种理性的认同,就是说你知道你想做什么,你原来可能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超越也好,漂流也好,自我探索也好,认同也好,都是一个人寻找乡愁、归根、新的自我的一种精神轨迹,一切都是一个人的人生的历程而已。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刘索拉,1955年生于北京,祖籍陕西志丹。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现为作曲家、小说家、人声表演艺术家。1985年发表小说《你别无选择》,她的小说是我国新时期先锋派小说的首批作品。在音乐方面,她致力于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象进入世界音乐界。
1988年,刘索拉旅居英国。
杨炼,1954年生于瑞士。1976年下放到北京昌平。1978年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之一。出版了中、英、德诗文集《人间鬼话》《大海停止之处》。
1988年出国,开始在世界各地漂流。现居伦敦。
文字整理:云浩、杨卫、镂克
蛋若有情蛋亦笑
尤 今
以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骆明先生为团长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作家代表团3月来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