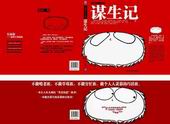陪都就事 作者:莫怀戚-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组。
三,乔芸斌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确系焦英苹;虽然为此非常的屈辱,但
认为自己的改名换姓,系“美帝国主义所犯罪行所致”,没有什么政
治阴谋,只为顾全个人名节。但在那个凡事都说不清的年代,她这个
解释根本不起作用。
四,接下来就是:确定她已被强奸。工作组长在会上说“她怎么可能
没被强奸”。为此还召开大会,不知从哪里请来了几位“解放前的见
证人”,回忆美军在陪都的暴行。
几位见证人都是朴实的老工人,他们的发言也非虚诓。四十年代,美
军吉普车在街头巡逡,见到漂亮女子,便悄悄靠近,突然将人抢上车,
一溜烟开跑,这种事很多。蒋政权要靠人害给钱给枪打共产党,所以
根本不可能认真追究。这类事情民愤很大,市民见到美军吉普就躲……
焦英苹承认那都是事实,但说“这并不能证明我的受害”。
于是又招来更多的大字报,有说“为个人名誉反替侵略者辩护”的,
有说她“根本立场是亲美的”……不胜枚举。
工作组反复给她做工作,要她“为了打击帝、修、反的千秋大业,勇
敢地承认自己的受害,并站出来揭发和声讨”。
对此她沉默了几天后,说你们去问我爱人吧。
五,焦的爱人不是本单位职工。对于这个问题,他非常肯定地说“我
们结婚时,她是处女”。
但,他承认自己并不知乔芸斌其实是焦英苹,“徐案”与她的关系自
然也不知道了。就是说,焦对自己的丈夫还是有“重大隐瞒”的。虽
然这种隐瞒可以理解,但仍然是“对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欺骗”。
两边的工作组配合起来了。焦的丈夫被隔离,做他的“思想工作”。
其间种种不必细诉,到后来,焦的丈夫虽没有彻底推翻“处女”之说,
但宣称“那时自己年轻,缺乏有关知识,所以对她是否处女没有注意”。
这样一来,焦的“最后挡箭牌”便粉碎了。她突然承认--我的确被
美国人强奸。
六,姓名为什么居然改成了?有一个偶然原因。
原来焦在正阳学院读书时,与一柯姓女教师相熟。柯老师是地下党员,
焦自然不知。五一年初,焦在南岸偶然碰见柯老师,躲不掉,只好敷
衍。柯老师说她现在巴县(属重庆管,离市区并不太远)的军管会里,
主持妇女工作,很需一批知识女性来任干部……焦灵机一动,便答应
下来。开介绍信时,焦便自书“乔芸斌”三字。柯老师是广西人,还
以为是自己“以往听错了”:当时还说了句:“看看,看看,我还一
直以为你姓焦呢!”
“乔芸斌”方正式产生,被共和国户籍承认。
七,焦英苹已于一九六六年底自杀--在禁闭她的那间办公室的吊扇
上挂了个绳套。绳子--说来令人唏嘘,对她本是有防备的,但给她
发现了室内捆在断腿藤椅上的一截麻索。
给她写交待材料的信笺上写了这样几个字:“美国人倒没把我把我……
倒是……”算是绝命书吧,其意也很明白。
这绝命书,工作组自然知道该怎么处理。对群众宣布,焦英苹死于
“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和屈辱”,“她的死,不是孤立的,有深
刻的历史原因”,云云。
八,焦英苹的丈夫,对妻子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为她的死痛惜,
另一方面,她向他隐瞒自己的身份及历史近二十年,他有怨恨也很自
然。他几年以后另处结了婚。现已去世两年。
“这位丈夫姓什么?”大律师问。
“姓霍。”
三位朋友相视一瞬间。
“焦英苹是不是有个儿子?”
“有,她死的时候,那孩子已经是个小伙子了。从来不招呼人,也不
说话。”
霍沧粟是焦英苹的独生子。
于情理上推测--
霍沧粟认母亲受辱,这桩仇恨积了几十年,在外国人大量进入中国时
找到了复仇机会。
早年,母亲被美国人强暴,现在女儿又被美国人欺骗和玩弄(他这样
看待戴维与小丽的关系)而将成为牺牲品;恰巧这个戴维的父亲老施
鲁德当年同“徐案”有关系,遂促成霍沧粟杀掉了戴维。
就是这样!肯定是这样!
--三个朋友一齐大笑起来。
想得美。
因为没有--证据。
因为靠分析是不能立案的;靠分析也是不能破案的。
随后便沉默。沉默了很久。
大律师突然问道:“《基都山伯爵》中那个复仇狂,有一点很奇怪--
他每杀掉一个仇人,总要告诉对方缘由。杀了就杀了嘛,何必多此一
举?”
武耀奇怪地盯着他。“复仇嘛,当然要让你死个明白!否则怎叫复仇?”
单延昭说:“汉斯豪斯的精神本能说里对于这个有理论上的解释。称
追求心理平衡是人类重要的精神本能……其中有一段谈到如果复仇结
果不能晓示仇人以使仇人同时遭受心理打击,复仇者的心理平衡便难
以获得。就是说复仇行为与生产行为之间有一重大区别:后者要获取
的是物质效应,前者则主要取精神效应。”
“说得好!”大律师称赞朋友。奥地利心理学家海·冯·汉斯豪斯是
弗洛依德的学生,与另一位学生弗罗姆是学术上的死对头。汉斯豪斯
有大量关于人类精神本能的著述,不知何故一直难以引起中国翻译和
出版界的重视。二十年前,尚在山中烧炭的知表大律师从一个右派分
子那里搞到几部俄译本,便开始了兴味盎然而又叫苦不迭的中译。译
成,终是不能出版,便将译稿在朋友中传看。
知青伙伴单延昭,回城后阴差阳错进了公安局,又鬼使神差干上了刑
侦;官至科长后,开始信服汉斯豪斯那一套。同契友大律师,在这个
领域,谈话最是投机。
“那么,”大律师又问道,“有没有这种情形:复仇已果,却不可能
昭示仇人?”
“当然有的。”单延昭说,还举了两个例子。
“那怎么办呢?复仇的精神效应从哪里去获取?”
“这个一定要获取,”武耀说,“否则复仇者会被自己‘我实际上未
能复仇’的念头折磨得自杀……我想,即使不可能昭示仇人,他总之
得告诉谁,例如知情者,或者仇人的亲人,甚至自己的亲人……”
单延昭同意:“他总之得告诉什么人。”
大律师再问:“假定不但不能晓示于人,而且舆论--我指的正式舆
论工具例如报纸、电视之类--认为那为仇人的死亡系另外的原因,
与复仇者毫不相关,会怎样?”
另两位朋友一致认为:复仇者会非常痛苦与郁闷,甚至会采取“纠正
视听”的做法。即使冒着危险也在所不惜。
大律师遂不再问。谈话戛然而止。
武耀与单延昭面面相觑,恍然大悟。
--用舆论的试探霍沧粟,让他自己出来“说一些话”。
当晚同已在美国的章律师通了话。
章律师说:老施鲁德说,之所以让儿子戴维去重庆投资医药事业,是
因为自己曾在那里生活六年之久,这在当时美国军人是很少的。
章律师淡淡地,仿佛漫不经心地告诉老施鲁德,自己在重庆“偶然地
见到一些有关陪都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性小说”,其中有的提到他。
“老施鲁德有点惊讶,看得出也有点不安,”章律师在大洋彼岸说,
“他也仿佛漫不经心地谈及了当年帮助蒋政权的事。就这样扯到了
‘徐案’。”
老施鲁德说:“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军队是勇敢
的,也是粗鲁和幼稚的。对被自己援助的民族不够尊重,就是表现……
对于‘徐案’,当时年轻的我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就连我的上
司对此也未对我说过一个字。但现在,我已老了,不知为什么,我却
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不是说,我在徐想跳车时将她按在了座位上
--我的确是担心她摔伤……而是,我应该对司机说停下,让她们走
……我默许了我的士兵。因为我同他们一样觉得,我们从平静舒适的
祖国,来到这乱糟糟的陪都,我们应该有所补偿……”。
次日起,一连几天,《渝洲唱晚》以连续报道的形式,登载有关“五·
二三”事件的内容。
△《章律师已经回国,委托重庆朋友处理善后》
(暗示读者,施鲁德家作为原告的形象消失;说“重庆朋友”而不说
“重庆方面”,也有已经“善罢甘休”的意味。
告诉读者,章律师回国向当事人述职后,施鲁德家已同意“意外死亡”
性质;文章故意让那些“准备看点热闹”的人失望,而且故意酿造
“失望氛围”。)
△《生命的贵贱没有区别》
(杂文。主题为:死了一个洋人就了不不得的时代已经过去。
文章“披露”了一些“政府官员”和“政法部门人士”的谈话,虽未
直接指出“五·二三”案,但告诉读者,现在的中国政府决不会因为
死者系“洋大人”而兴师动众另眼相看。进一步营造“失望氛围”。)
△《沿江小艇作何处置?》△
(作者:单延昭 重庆市公安局。文章批评沿江小艇非法出租现象;
指出“五·二三”与这一现象“不可分割”的关系;暗示该负责的是
小艇主人,什么“银娘”游轮,什么航管站皆无直接责任。
这篇文章的用意极深:一,将“罪责”推给小艇主人,又奈他如何?
他最多只是违反了有关规定,例如工商、税收之类;至于“违章航行”
--他根本不在小艇上,所以违章航行的正是戴维·施鲁德本人,与
他无关。二,这样一推--注意作者单位--当然让读者明白:“五·
二三”无戏可唱了,谁也没有罪责;死者自己负责。三,组织上,例
如市公安局吧,也不会指责单延昭,因为文中有“个人看法”之说,
况且批评的内容均属应该。)
…………
此类文章造成的印象:
一,死者死于不会游泳加上运气不好(租了不该租的小艇,遇上了大
船启航),自己负责;
二,死者家庭已明白这一点,且已平静了情感,取消猜疑,接受现实;
三,有关职能部门已无意再过问此事。
单延昭说:“如果是复仇行动,复仇者对于事情的败露的担心会消失,
然而代之而起以强烈的失落感……”
武耀说:“一定会有一种仇并未复了,只是白白害了一条命的感觉。”
大律师说:“我相信复仇者最希望的情形是:全社会都明白他已复仇,
然而法律却奈他不何。”
“当然罗!当然罗!”两位朋友都说,“鱼与熊掌兼得之。但是世上
哪有这样的好事!”
“不要那么悲观嘛!”大律师笑起来(这两个家伙--好象他们就是
那位复仇者),“我们将钓饵继续抛出。如果我们运气好,我们就可
以使人相信有那样的好事。”
····
随后,在《渝洲唱晚》的第八版上,突然出现一个栏目,叫“业余法
官”,刊登读者对案例或事件的争论。
第作版本是社会轶事和民间趣闻,谓“花边版面”,现在突然开出这
样一个板着脸孔的栏目,多少有些让同道摸不着头脑。
更奇怪的是,第一个被端出来争论的,关非肯体的案例或事件,而是
一个人物,报纸称他为“Y作家”。
近年来重庆人将一切不合格品统称为“Y货”。“Y作家”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