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军-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哥萨克战死,顿河流域这哥萨克的家园成了赤地和坟场。 布琼尼的骑兵军是幸存的身经百战的生力军。这一万多名的哥萨克,和他们手中的冷兵器——那一万多把马刀,使华沙的波兰军人不寒而栗。在之后的三个月的战争中,苏波双方将进行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空前惨烈的骑兵会战。 凶猛的骑兵军中来了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他是由处于俄国南部、黑海北岸的海滨城市敖德萨的共产党党委会派来的战地记者,叫科利奥·柳托夫。他一边随军征战,一边在《红色骑兵报》上发表宣传性的战地报道和军情速写。“柳托夫”的本意是“狂暴”,可他的身量、面目却和他的姓很不相称。他竟然带着一副哥萨克战士们最讨厌的细圆边儿眼镜,身材也不高,甚至有些未老先衰,这分明写在他的忧郁的脸上和已经开始谢顶的前额上。 见过他的人都说他举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只要直视他镜片后的眼睛,就会发现其逼人的穿透力——好像他能看到一切、明白一切。悲哀因之而生。这也是双猎人的眼,仿佛他随时举着枪瞄准,只要有活的生命从任何方向突然出现,他都能立即将其捕获射杀。那里面还有狡黠、反讽,甚至一个男孩儿的顽皮。这是一个心中藏着秘密的人。他是他的身份证上标明的那个狂暴的革命者吗?如果是,他为什么悄悄地、坚持不懈地在日记本中用铿锵的短句记录真实的所见所闻,同时又常常直抒胸臆——“这是一群有纪律的野兽”,“我控制不住我的悲伤”。——他看到了什么?他总是不断提醒自己:“描绘天空”,“记住他的脸”——分明在为以后的创作做准备。 果真,数年后的1923年,他把这些断断续续的意象锤炼成三十多篇短文,长的不过五六千字,短的仅有半页纸——这就是《骑兵军》,这本曾经震撼过世界、今天仍然震撼着我们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战场的质地被转换成文字的质感——字里行间传达出军情电报的短促、骑兵战术的迅猛、马背上时空的变形;而跃动的铁蹄也扭转了传统的叙述脉络,颠覆了旧有的故事结构。终于,战火硝烟、人喧马嘶从迷阵般的段落章节里轰然钻出,在纸面炸开了…… 八十多年过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这些有关苏波战争的血与铁、征服与反抗的结晶,比历史文献更真实——这是一颗颗多棱多面的钻石,每个侧面都有一个锥心泣血的意象,我们看到一个个霸气、豪气、匪气冲天的哥萨克壮士。而且,从中能窥见那消失的整体。一次大战、俄国内战、苏波战争重创了这个强悍的马上部落。哥萨克从此一蹶不振。现在,仅剩下幽魂飘散在乌克兰的森林和草原上了。而这些哥萨克生态的化石,其构造之坚硬,就是闪电也休想把它们击碎。 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真名叫伊萨克·巴别尔,于1894年出生于敖德萨的一个农机商人家里。他十八岁就曾发表短篇小说,1916年在彼得格勒结识了高尔基,成为后者最器重的少年天才。1917年他志愿到罗马尼亚前线服役,前线崩溃后,逃回敖德萨。在动荡不安的1918年冬天,只身一人冒死潜回彼得格勒加入了那里苏维埃政权组织的肃反委员会反间谍部。并且,在俄国内战期间,曾随莫斯科的征粮分遣队南下乌克兰粮仓征粮——这是一个积极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他为什么要在红色骑兵军中隐姓埋名?
王天兵:巴别尔的秘密(中译本序)(2)(图)
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哥萨克,正是所有犹太人的天敌。 在欧洲大陆上,对犹太人的迫害不是从纳粹开始的,也决不仅限于德国,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公元70年古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的屠城。从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等国都先后驱逐过犹太人。在1542年,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因为犹太人拒绝信奉他的新教,发表宣传册《关于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把犹太人称作屠杀耶稣的刽子手和妄想统治世界的罪犯,并号召烧毁犹太教堂、学校和住宅,以期最终把犹太人“像疯狗一样从大地上赶走”。这个观念流传至今。数百年后,德国纳粹仍在###上醒目地张贴路德的这份宣言。 1648年,在波兰和俄国第一次爆发了由哥萨克统领的屠犹活动,有十万犹太人被杀。对哥萨克来说,屠杀既是本性,又是职业。哥萨克原本不是一个种族,他们允许外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却从来拒绝犹太人进入他们的领地,更不准和他们共享共荣。此后,屠犹从未停止过。排犹不仅出现在沙皇颁布的法令中,而且也化为一种极端的情绪在民间盛行。1903年至1906年,第二轮屠犹在波兰、乌克兰爆发:1905年,曾遇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下达了屠犹令,指使其雇用的哥萨克骑兵在犹太人生活区烧杀。在沙皇的授权下,屠犹成了哥萨克发挥本性和专长的一次“业务”。在这次大屠杀(Pogrom)中,有上万名的犹太人被打致残,数千人毙命。1918年至1920年,又有大约十万犹太人在乌克兰的俄国内战战场被无辜地杀害。1920年,在苏波战场上,哥萨克的红色骑兵军从没有停止对犹太人的屠戮和暴行。 在巴别尔1920年的日记中,处处可见他的骑兵战友们对波兰犹太人无休止的血腥屠杀。巴别尔后来曾说:“我什么都能理解,但就是不理解排犹这个黑色恶魔。”在《骑兵军》中,巴别尔曾描述过一次哥萨克的屠犹场面。在波兰小城别列斯捷奇科,当入侵的骑兵军正准备召###议宣传革命时,一个年轻的鬈发哥萨克揪住一个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将其头夹到胳肢窝下,然后抽出匕首,利索地割断老人的脖子,身上未溅一滴血。事毕,若无其事地招呼人来收尸…… 一个犹太人来到哥萨克骑兵中,无异于一个犹太人加入了纳粹。这就是巴别尔隐藏身份的根由。在日记中,他管波兰的犹太人叫“我的人民”。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不但是一个俄国人,也是一个犹太人。实际上,他十八岁写的文笔还显苍白的处女作《老施劳埃密的故事》,讲的就是一个犹太老人因拒绝改信基督教而自杀的故事。当他主动要求参加哥萨克骑兵军的时候,他在敖德萨的家人,包括他1919年刚新婚的妻子,都认为他这是在自杀。 那么,戴眼镜的文学青年巴别尔为什么又要冒死加入到犹太人的天敌中呢? 让我们溯本求源,到俄国南方海滨城市敖德萨去追寻他的童年。敖德萨地区是一个民族大融合之所。从地理特色的角度来看,北方寒冷的海港彼得格勒欧化、时新,是开新风气之地;莫斯科是雍容、保守的内陆旧京;整个敖德萨地区则是温暖、繁忙的商业口岸,和排犹严重的俄罗斯内地相比,犹太人在这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自由。 犹太人也不是一个种族,和哥萨克一样,是一种文化群落。但和哥萨克相反,他们强调读书。犹太人中最受尊重的是教长——拉比,他们不厌其烦地注解经典、参玄悟道,为大而空的理论争吵得面红耳赤,苦苦追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敖德萨,重视教育的犹太人就把这种文化传统变成了商业资源。如果说哥萨克人一会走路就能骑马,一会骑马就能射击;那么这里中产阶级的犹太人一会说话就要读书,一开始读书就要考试。那些像豆芽菜一样的犹太神童们,从小就被家长逼着上各种音乐补习班,以期早早出人头地,能到圣彼得堡演出,从而名利双收、光宗耀祖。 从巴别尔有关童年的小说,不难推想他饱读诗书的童年、少年时光。他从小必须学太多的东西——英文、法文,还要在私塾学希伯来文。祖母曾疾言厉色地让他不要相信任何人,而要让所有人嫉妒他,就要读书、背书、做作业——要什么都懂。 巴别尔在其后期的名篇《醒悟》及续篇中,曾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在苦修中、在小提琴课上泡大的厌学的孩子,他因恶补终日而四体不勤,也不知大自然为何物,何况——在东欧犹太人的母语意第绪语(Yiddish)中,原本就只有两种花的名字,而且没有一个鸟的名字。但同时,他的想像力却在燃烧——他暗恋成熟的女人,饱受情欲的煎熬,为了自由地呼吸空气,以至逃学野外,他想知道每一只鸟的名字,并开始偷偷学习游泳。这是他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触摸自然和生命。可是,望子成龙的父亲发现后,立即威胁要打死他。 所以,可以想象当巴别尔从少年时代开始大量阅读欧洲文学时,为什么会尤其钟爱莫泊桑,因为他在那里读到了俄国文学中少有的灿烂阳光和旺盛情欲。在他二十岁出头时写的短篇随笔《敖德萨》中,他呼唤在这座城市诞生俄国土生土长的莫泊桑。他二十一岁时,彼得格勒当局曾指控他在短篇小说《浴室之窗》中描写色情。在这富于调侃的短篇中,他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趴在梯子上偷看妓女接客的青年,失足摔落被发现后,因为对妓女的声色不能释怀,又恬不知耻地再次爬上梯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王天兵:巴别尔的秘密(中译本序)(3)
他从小就是一个犹太文化的叛逆。他也立志要做阴沉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叛逆。 同在《敖德萨》中,他历数了迷恋于朝露、静夜、大雾、暗路的俄罗斯大家们,对俄罗斯文学中还从没有“真实地、鲜明地、欢快地描写过太阳”,感到震惊不已。巴别尔感叹阴冷的彼得格勒毒杀了生于南方乌克兰的小说天才果戈理。巴别尔推崇果戈理在乌克兰时期的名篇《塔拉斯·布尔巴》(1830),赞美这是在俄国文学传统中第一次能窥见了太阳。 而《塔拉斯·布尔巴》,讲的恰是十七世纪剽悍的乌克兰哥萨克人进攻波兰的故事。其中有一幕是说哥萨克布尔巴的长子被敌捕获示众,就义前向围观的人群大呼:“爸爸,你都看见么?”塔拉斯·布尔巴躲在观众中说:〃儿子,我都看见了!”普通的话语间,昭示了复仇的宿命。俄国画家列宾,曾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创作巨幅油画《扎波罗热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1891),画的是一群身处绝境的哥萨克们谈笑风生地给土耳其苏丹写信,拒绝投降。据说,前景中赤裸上身的就是塔拉斯·布尔巴。 巴别尔热爱的不只是果戈理在乌克兰时期的明丽文风,也向往充满生命和鲜血的原始风范。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哥萨克从来就不仅仅是冷酷的杀手、野蛮的屠夫。他们还代表了力与美,代表了不同于文明时代的古老的纯真岁月。 托尔斯泰有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就叫《哥萨克》,写的是一个莫斯科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奥列宁,厌倦了浮华世界,为摆脱空虚,远涉边陲,加入了哥萨克军队,希望那未经文明腐化的原始雄风,一洗自己灵魂中的污垢,他果真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哥萨克女人,而且,要和他的哥萨克情敌一决雌雄。 在《骑兵军》中,也有类似的一篇短篇小说,也讲了一个外来的“他者”、一个书生,加入到哥萨克人中的故事。这就是名篇《我的第一只鹅》,讲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在苏波前线加入骑兵军后下排第一天的事。刚到师部,年轻的哥萨克师长萨维斯基就嘲笑他的眼镜,怀疑他怎能和战士们合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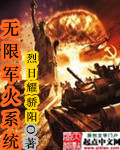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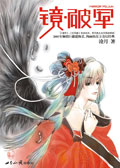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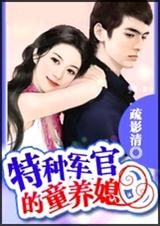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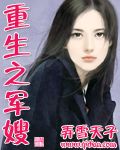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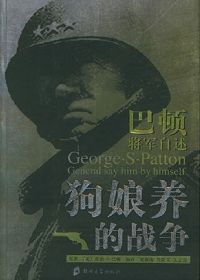
![军夫[网游]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