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军-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里不时闪出的那些跳荡的语式,甚至嵌合着充满想像的通感手法……〃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亡〃。巴别尔用诗和箴言的修辞装饰着哥萨克骑兵身后满目疮痍的土地,无尽的苦难从笔下堆积起来,却丝毫不像是蹙着眉头的描写。在任何悲怆时刻,他从未堕入海明威那样的悲凉心境,有时他会用词采斑斓的描述展开一个悲剧的序幕:〃……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这般亦谐亦庄的句子用来导述血迹斑斑的坎坷历程,相当耐人寻味。 《红色骑兵军》取材于作家本人在布琼尼麾下的战斗经历,但是这些战地实录式的故事绝非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战争文学,因为没有正邪分明的营垒,没有军事上的谋略较量,更没有浴血奋战攻城掠地的激情与豪迈。苏俄内战期间相偕而来的俄波战争至今留有许多悬疑之处,历史卷宗记载着1919年至1920年间红军向乌克兰、波兰辗转进军的日程,却把种种是非功罪的思索扔给了后人。在革命激流中成长的巴别尔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正义诉求,可是战争岁月的腥风血雨使他清醒地看到以恶制恶的负面效应……过度的暴力和杀戮开启了以革命的名义戕害革命理想的凶衅。所以在这部由30多则短篇组成的小说集里,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一种睥睨善恶颠倒的立场。巴别尔对他所描写的这场战争显然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旧制度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在忧虑战火对文化和宗教民俗造成的极度毁伤。《基大利》一篇中,他借那个开杂货铺的犹太老者的诘问点到了思想的痛处:〃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礼拜六是犹太教的圣日,如同许多传统事物一样,这些与旧制度相缠绕的东西并不能跟旧制度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萨克骑兵们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把斗争变成了癫狂,同时把革命这事情也给戏剧化了。巴别尔在书里大量叙说战争的日常暴行,写了游兵散勇的个人复仇,也写了那些〃思维健全的疯人〃。在有些篇目中出现了对比性基调,世俗人生的赏心乐事,犹太智者的质朴理念,他还津津乐道地讲述走江湖的圣像画师那种诙谐的民粹思想。他怀着希冀寻寻觅觅……〃寻找那颗怯弱的星星〃,用超越现实混乱的冷静关照传递着俄国新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巴别尔的叙述语体远比故事本身来得复杂。所有这些充满忧患的故事出自一种清朗明快的手笔,就像是用机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说摧肝裂胆的苦楚,有意使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拉开了距离,这种策略显然包含着叙事内容以外的话语意图。《红色骑兵军》虽云短篇,巴别尔却力图在这里勾画更为复杂的生活图景,表现那个时代诡谲万变的精神特征,所以采用了被文学史家称之〃狂欢化〃的叙述体裁。比之任何传统的自然主义创作,这种从古代〃庄谐体〃和〃梅尼普讽刺体〃发展而来的复调小说,不但有着更为贴近现实的仿真性,并且以讽刺性摹拟手法大大增强了艺术概括力度。巴别尔非常娴熟地把握着〃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在小说里大量采用各种插入性体裁,如书信、报告、复述的对话等等,甚至还有墓志铭。由此从不同角度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在互相追诘与驳难中凸展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从布琼尼骑兵到马赫诺匪帮,从私盐贩子到牧人出身的红军将领。在这个舞台上,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谎言,革命和反革命,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所有对立的因素构成了令人不安的互动关系,而人生的错位往往就在风云翻覆的情境转换之际。当然,生活有自己的逻辑,每个人则有自己的行为理由。 这里使人想起巴赫金用〃翻了个儿的世界〃的说法来归纳狂欢体叙述的一个逻辑:帝王变成奴隶,奴隶成了帝王,如此等等。在《红色骑兵军》的话语结构中没有给任何史诗化的东西留下一点地盘,却给读者拓开了更多的思想空间,此如巴赫金所言:〃狂欢化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已然成型的、现成的东西,全给相对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毫无疑问,〃相对化〃正是巴别尔追寻的哲理目标。
巴别尔:泣血的风景(图)
1940年1月27日凌晨,天寒地冻,阴风凄厉,卢布扬诺夫监狱又空出一个位子,被枪毙的不是别人,他就是由高尔基一手扶掖起来,后来被推崇为〃苏俄时代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家伊萨克·巴别尔,一个生性静默、长着一双小眼睛的犹太裔俄罗斯人。这一年他47岁。
巴别尔好像并不是从小就爱好文学,但他却能将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他尤其喜欢兰波的诗,受到法语老师的鼓动,他开始投稿却处处碰壁,那些编辑大人们劝他说:找家店铺当个伙计不也挺好。1916年,巴别尔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他幸运地遇见了高尔基。高尔基挥挥手打发他到人间去,这一去就是7年,到了1923年有了丰富人生阅历的巴别尔重新操觚并一鸣惊人,写出了后来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红色骑兵军》。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巴别尔时说,凭第一印象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巴别尔是一个作家,既没有悦目的外表,也没有丝毫的造作,更没有思想深刻的谈话。只有眼睛……那双锐利的眼睛,能够洞察你的全身,这双笑意荡漾同时又十分腼腆并充满嘲讽的眼睛能勉强暴露他的作家身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这段话对于我们认识巴别尔以及巴别尔的小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巴别尔是善于观察的,巴别尔的小说缺少宏大的结构,有的只是对于细节、对于真实、对于战争期间小人物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与良知的有力攥捏,这样的结果使我们在仰望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大家的鸿篇巨制的同时,又能在方寸之间得以窥视俄罗斯文学另外一番短小精悍的景象。《泅渡兹勃鲁契河》是巴别尔的名篇,傍晚,六师的辎重车队,车声辚辚地向前驶去,〃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像雨水一般飘落下来〃,战争的惨烈可以想象,紧接着巴别尔写道:〃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荞麦好似妙龄少女,亭亭玉立于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然而,温暖的生活景致抹不去战争的残虐。当犹太女人的父亲被杀死以后,我以为巴别尔小说中最经典、最令人难以释怀的句子出现了:〃我想知道,在整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我打了个激灵,一下子坐起来,又反复读了几遍,是呵,这个世界上惟独亲人是惟一的。巴别尔似乎在暗示我们一些战争之外的东西。
像布尔加科夫、纳博科夫一样,巴别尔也是在西方文坛先红火起来。海明威、博尔赫斯、罗曼·罗兰等大作家都钟情于巴别尔的作品。博尔赫斯说,巴别尔的《盐》写得像诗一样美。而《我的第一只鹅》,不仅写得优美且寓意深刻:〃农舍旁砖砌的行军灶上,锅里正在煮猪肉,热气腾腾的,像是从远方故乡的村子飘来的炊烟,勾起了我孤身在外、饥肠辘辘的乡愁。〃按理说这样的人似乎做不出伤天害理的事,然而他却揍了可怜的女房东,剁了她仅有的一只鹅。战争让人瞬间异化,甚至禽兽不如,鹅变成了飘香的鹅肉,文明化成了一锅油汤,良知像狗一样伸出了舌头:〃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巴别尔写了一只鹅的命运,在《通往布罗德的道路》中,他又写了一群飞舞在花丛中的蜜蜂。〃我为蜜蜂伤心欲泪,它们毁于敌我双方的军队,在沃伦地区蜜蜂绝迹了。〃美好的生活被埋葬了,战争换回了什么呢?巴别尔那双锐利的小眼睛没有给我们答案。
巴别尔为蜜蜂伤心欲泪,我为巴别尔的命运扼腕叹息。巴别尔死前,最后的陈述是这样:〃我是无辜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
今天,巴别尔对于我们大多数读者来说依然是陌生的,因为铁幕背后的东西依然混沌莫辨,或许还会像巴别尔这样的大师从漆黑的幕后闪出他们的身影来,爱好俄罗斯文学的人们似乎有理由多出一份揪心的期待。
仅仅记住伊萨克·巴别尔这个名字是不够的,要真正了解他最好的途径是读他的作品,那种直接得到的感受是可靠的。
; ; ; ; 。 想看书来
王天兵:巴别尔的秘密(中译本序)(1)(图)
1920年,波兰领袖毕苏斯基为了阻止建立不久的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向欧洲扩张,在法、英、美等列强声援下,指挥波军入侵乌克兰,当年5月占领了乌克兰首府基辅。此时,俄国内战却已接近尾声,红军在全线告捷。于是,列宁决定与波兰人交战。他希望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传到波兰,引发那里的工农起来暴动,推翻波兰旧贵族,最终导致德国的工人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高潮。 同年6月,苏军开始进攻波兰。苏波战争爆发了。 在苏维埃红军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未入波兰却已经令人闻风丧胆。 据曾在波兰军中服役的美国志愿飞行员回忆,他们驾机在空中俯瞰过这支劲旅。只见,在沙皇铺设的通往波兰的官道上行进着一支骑兵军,每行八人八骑。骑兵们有的头戴圆筒型翻毛帽子,有的身披戴头套的黑色大氅;他们背上斜挎着步枪,腰间悬着长马刀和短匕首,在尘土中浩浩荡荡地前行,几公里之外仍然不见尽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大规模屠杀机械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被机关枪、坦克、飞机彻底改变了的欧洲大地上,这支马上的军队好像正默默地从传说的背后、从历史的深处杀出。 这就是布琼尼统帅的哥萨克骑兵——在俄国内战中所向披靡的红军第一骑兵军。 哥萨克一词源自突厥语,意为“草莽英雄”或“浪子”——在社会中失掉归宿而在草原上觅得家园的人。哥萨克们是欧亚大陆上的斯巴达人。大约从十五世纪之后,他们的祖先,主要是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家可归的平民,开始在黑海以北、伏尔加河以西的顿河流域一带群集,渐而称雄。他们酷爱自己的家乡,但他们天生就是战士和杀手,以致不事耕种,只把大片耕地租给农民。他们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尚武的本性让他们从十六世纪就组织职业军队,十七世纪就曾在乌克兰、波兰边境爆发了由塔拉斯·布尔巴领导的残酷的独立战争;当拿破仑兵败俄罗斯而在天寒地冻中撤退时,是他们尾随蚕食了法国远征军,并因其残忍的兽性被拿破仑贬为“人类的耻辱”。俄国历代沙皇都很重视这群嗜血的浪人,平时组织他们进行屯守,战时则将他们征入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组建了十二支哥萨克部队。在1918到1920年的俄国内战中,有一百多万分属红军和白军的哥萨克战死,顿河流域这哥萨克的家园成了赤地和坟场。 布琼尼的骑兵军是幸存的身经百战的生力军。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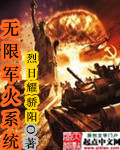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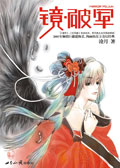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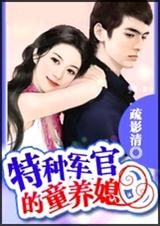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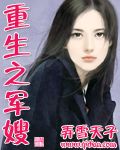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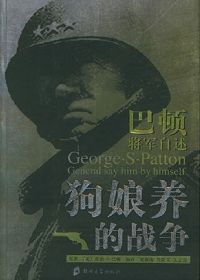
![军夫[网游]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