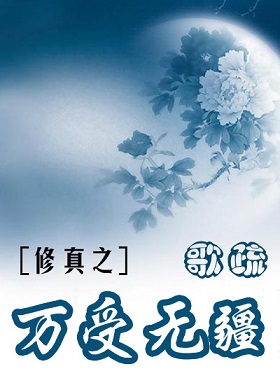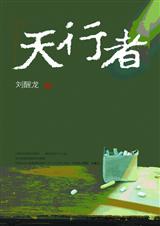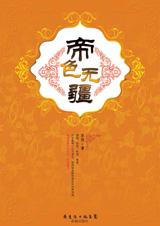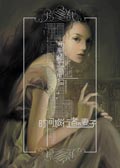行者无疆-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空空的书架
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越过,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请边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
———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我不知道这是当年真实的地下书库,还是后人为纪念那个事件所设计的一个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种,看了都让人震撼。心与书架一样空了,随即又被揪紧。反复地从四个方向看仔细了,再移步过来把海涅的那句话重读一遍。
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的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才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
可以想象,一切刚刚考入洪堡大学的各国学生都会来看看学校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块铭石,这个窗口。他们似懂非懂,注视半晌,然后进入书库,俯仰今天的书架。他们中的部分人也许会由此去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史,即使不去研读,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今天社会上一切讨伐文化的行为产生警惕。这些行为未必是烧书,现在连德国境内的“新纳粹”也不再烧书,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号下的毁损,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义下的恐怖,而这些又经常与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和争斗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学的第一师训,首项校规,不容轻视,无可辩驳,凿石埋地,铭誓对天。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落伍的疯狂
在柏林街头还能找到很多纳粹活动的遗址。留下了遗址,也就留下了记忆。
一切有关纳粹的记忆,并不是一场偶然的噩梦。这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的产物,具有研究的普遍价值。要不然,这些古老的街道和坚固的房子,这个严肃的人种和智慧的群体,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癫狂起来。
我认为,这是欧洲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口上一种撕裂性的精神绝望,这是社会各阶层失去原有价值坐标后的心理灾难。纳粹把这种绝望和灾难,提炼成了集团性的恐怖行为。
现代是一个平等竞争的自由天地,现代是放弃狂热迷信的理性普及,现代是对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级的渐渐轻视,现代是集权梦幻和极端思维的天然障碍。
这一切照理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已经逐步显现,但到了二十世纪,渐渐变成无可逆转的社会规则,尤其是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甚于其他国家,转眼间在德国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失败者和失望者,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坐立不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制造了“雅利安人高于一切”、“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迷思,又提供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许诺,失望心理有了一个收拢点。
一九二四年,还没有成事的希特勒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在他笔下有一种“你死我活”的性质,表达了因失去空间而难以生存的危机心理。问题是当时有这种心理的远不是他一人,否则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拥护他的独裁政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共同感受到生存危机呢答案是,社会正在转型。
在社会转型中感受到了生存空间的危机,只能产生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来扩大空间;第二种是毁损别人的生存空间来扩张自己。显然,第一种是良性方式,第二种是恶性方式,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选择了第二种。
他们首先通过毁损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来验证自己的概念,这一招很有迷惑力。因为一般民众都希望把自己的困境归因于某个人或某个群落,于是比较崇尚实利主义、娴于商业运作的犹太人成了替罪羊。明明是自己受了时代的挑战,却被解释成一个高等民族遇到了低等民族的侵害。多年来压抑心底的嫉妒之火、无望之火、失落之火一时被堂皇的理由点燃,仇恨也就立即上升到围攻,上升到暴力。
剥夺了犹太人的生存空间,纳粹又要剥夺别国的生存空间了。
纳粹的这种行为逻辑至今还发人深思。任何社会转型落实在人群中,主要表现为生存空间的盈缩,生存方式的转移。这虽然不无残酷,却是历史的必然。旧结构的代表者以破釜沉舟的决绝方式来抗拒转型,因此会出现一种惊人的整齐和狂热。现在世界上各种以原教旨主义作标榜的宗教极端分子也是既整齐又狂热,把逼近自己身边的现代生活当作必须搏杀的魔鬼。
这大体能够说明这样一批纳粹为什么会受到总统兴登堡和旧军队的支持;而且为什么直到最后,除了那些被直接入侵的国家之外,越是现代理念强烈的国家,如英国、美国,越与它势不两立。
现在德国又出现了“新纳粹”。几乎都是年轻人,剃平头,着靴子,成天用仇恨的目光面对世界,一意要寻找攻击对象。从某些形态上,他们有点像“朋克”,但“朋克”只表现生态上的反叛,不怎么攻击他人,而“新纳粹”则以攻击他人为第一特征。他们已用恐怖袭击的方式杀害大量的外籍劳工,但即便是本国的正派人也不愿与他们靠近,怕他们寻衅攻击。
我们的德国朋友郑碧婵SigrumGarthe小姐这次从西部赶到东部来接我们,路上就遇到好些“新纳粹”。碧婵说,这一带的“新纳粹”有点特殊,主要是原东德地区经历大幅度社会变型所产生的社会渣滓。本来可以依赖的势力系统解体了,自己又没有学会谋生的本领,完全无法面对两德统一后按照市场规律而进行的正常竞争,只好诬赖外籍劳工把他们的工作夺走了,便反过身去进行伤害。因为伤害的是“外籍”,便重新弹起了老纳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大日耳曼主义的老调。
碧婵说:“本来西方政论界习惯于把极端分子分成左翼和右翼,但他们这批人,本质倒退,形态时髦,已经说不清是什么翼了。”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想,中国的文革在本质上也是反现代,尽管那些红卫兵、造反派都举着“破旧立新”的旗帜;而结束文革,就是开启现代。
碧婵在边上问:“现在你们中国也进入了社会大转型,这样的群体也会有不少吧”我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漫应之曰“唔唔”。
“新纳粹”的愚蠢在于这个名称使他们必须承担老纳粹所造成的全部血腥债务,而这恰恰是老纳粹起事之初所未曾承担的。因此,在我看来,只要他们举起了这个旗号就不再可怕。新的恶行一定有新的伪装,有时还故意表现出对历史恶行的清算姿态。人们必须穿越这些烟雾,去审视它与波荡不定的群体心理是否构成了危险的交接点。
为此,我还特地去关注了一个希特勒当年在民众中演讲的状况。
早就知道希特勒当年在纳粹党内初露头角是因为他的演讲,连他自己也惊讶自己怎么会有控制全场听众的本事。我这次在欧洲几次看到希特勒演讲的电影资料片,知道了他受到欢呼的直接原因。每个演讲现场都是社会情绪的浓缩,每个听众都是一张绷紧的弦索,只需在敏感部位挥动几下就嗡嗡响成一片。希特勒的演讲不在乎逻辑,不在乎论证,却有一套有效的心理鼓动程序,在这方面实在堪称专家。他一般是哑着嗓子开头,似重病在身,似喁喁私语,与刚才慷慨激昂的其他演讲者一比好像不合时宜,但这种反差却立即打破了听众对演讲惯性的厌倦,全都提起精神来侧耳细听。就这么讲了一会儿,冷不丁地,他突然咆哮,一声比一声响,似口号,似反问,似呼吁,这自然把全场搅得掌声如潮。掌声未落他又轻声,没几句又转向洪亮。此后,高低声腔更替的频率加快,最后几乎全身用力,手舞足蹈,又戛然而止。这么一闹,无异于在一把把揉压全场听众的情绪,最后当然会迸发成集体疯狂。但是应该看到,正因为被揉压的万千心灵在当时有共同的脆弱、共同的敏感、共同的亢奋,才会贪婪地吸食他那些并不连贯的句子而陷入痴迷状态。
虽然是陈旧的电影资料片,看了还叫人害怕。即便是那么讲究理性的民族也会突然失去理性,被一种急切想通过伤害他人来扩张自己的卑劣情绪所裹卷,只待有人把这种卑劣美化成正义,便血脉贲张,摩拳擦掌,不再有起码的逻辑判断和道义防范。
我一再地设想,希特勒如果生活在今天,凭着他这样的演讲,可能什么事也成不了;但是,如果让他少一点外部表现上的歇斯底里,又找到一些不公平现象或不公正待遇的话由,再加上某种宗教成分,外貌稍稍好一点,今天的听众会怎么样历史,该如何避免或绕过这样的泥潭理性的启蒙、良知的传递、文明的呼吁,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这类恐怖的灾难不知道。大家多加小心吧。
致命的象征
柏林斯泊利河畔有一幢白色的古典建筑,现属普鲁士文化基金会,一百多年前,是中国公使馆的所在地。
整幢楼房坚固华贵,今天看来还没有陈旧之感。大花园,高铁门,阳光下整个庭院一片宁静。
这幢楼本来属于俾斯麦的财政部长,租给了中国。大清王朝原先哪里看得起遥远的番邦因为看不起,所以也不屑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因为不知道,所以更看不起,直到被他们欺侮得晕头转向,才迟迟疑疑地改口把他们叫做“列强”。后来又逐渐知道了一点国际关系规范,开始向西方列强派出外交使团。
中国公使馆设在这样一幢楼里,还算是有一点气派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最初几页充满了大量可恨可笑的辛酸事,很多没有记录下来,其中一部分就发生在这幢楼里,再也无人知晓,而这白森森的墙壁门窗,又都不落痕迹,默然无语。当年的中国外交官穿着清代的标准服装在这里进进出出,而清代的男装实在太不好看,把身材全都吞没了。这些外交官心情都不太好,其中几位,已经开始皱着眉头作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思索中华文明落后的原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