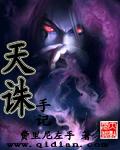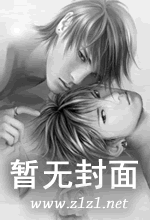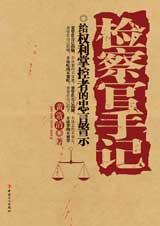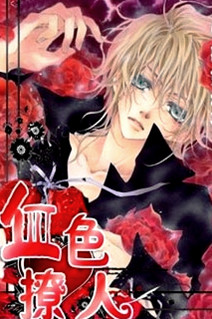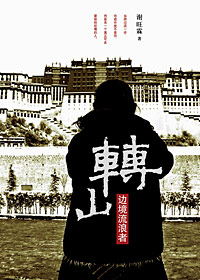边境插队手记-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缘了。”
带着犹豫和困扰,我去县里应试文化和检查身体。
语文、数学、政治,过了。
内科、外科、透视,过了。
推荐的人被涮掉一半,我顺利通过。
83、如花逝去 '本章字数:136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5 13:29:27。0'
正当我在为要不要去上中专纠结时,接到了一个噩耗:沈爱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是老知青,1969年插队前,她叫沈爱芳。
1970年,我们来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大队党支部书记领我们来到黑龙江边说,江中的主航道就是中国的边境线,你们来到了中国最北疆啦。
他很得意地介绍:“在你们生产队的知青中,有三个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改成了边疆的疆,成为黑龙江所有知青的一段佳话。”
我们听得瞠目结舌,心中对“三疆”充满了钦佩。
沈爱芳就是其中一个,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沈爱疆。
“三疆”只比我们大一二岁,那时不过才18岁。
一个像老大哥,宽厚照顾;
一个像老大姐,细心体贴;
唯独她,很少听到她的声音,也很少看到她的笑容。
这是我们新知青与她只有半年多相识的时间里,留下的印象。
在所有知青中,我们新知青对她的了解是最缺乏的。
下乡第一年,对我们知青来说,日子过得竟然是这么快:
一会儿外出去水库挖水渠;
一会儿外出去兴安岑修战备公路;
一会儿外出去小三线抢收小麦;
53个知青,东分西散,从来没聚齐的时候,半年下来,人头儿才算刚刚混熟。
黑土地的粗粮让我们这些纤细的城里人变得胖了,
田野上的太阳让我们这些白脸的年轻人变得黑了,
唯独她,脸色一直是黄黄的,整天心事重重,身体也很虚弱。
每次回到生产队,见到的是她黄色的脸,沉闷的心事,还有不断增长的脾气。
转眼,到了1970年年底,当知青结束了没完没了的外出回到生产队时,她已经回上海探亲去了。
第二年春天,探亲的老青年结伴而回,她的身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听说,她得了脑瘤,病倒在床。
又一年过去,东北大地春风吹过,在春风的背后,铺开了万紫千红的田野,婆婆丁、蒲公英、马兰花儿开了那么多。黑龙江也已经化冻,满江里都是洁白的冰块,撞得叮叮咚咚地响。
然而,沈爱疆却再也没有力量撑过生命的这一道坎,最终医治无效,她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才刚刚开始的世界。
如花的年龄,就这样走了。
1972年,她20周岁,成为知青中最早的逝者。
至此,我们才理解,她为什么脸色黄黄,为什么心事重重,为什么脾气增长……
我相信,一个曾经满腔热情把“爱芳”改成“爱疆”的青年人,一定对未来充满了志向。
是病体让她无能为力,壮志难酬。
她在远离父母的边境线上,曾经独自一人支撑着快要熄灭的生命。
其心之苦,其路之危,是她难以言表的。
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丝豁达:好死不如赖活,什么中专大学,相比生命的幸存来说,那算得了什么呢?
好多好多年以后,她的脸庞,在我们的印象中,逐渐模糊。
有人已经忘记有一个叫“沈爱芳”的女知青,只有提起赫赫有名的“三疆”时,大家才会想起,说:哦,还有一个沈爱疆。
她,尽管像风儿一样轻轻地掠过,但依稀还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她当年的热血,她当年的激情。
以及她当年留给我们的钦佩和留给我们的伤感。
我还记得和她只有一次私下的交往:一天,她见我在看一本《乐观集》,这本书的词句很华丽,作者是史凝,196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她满心喜欢,开口向我借去。
她匆匆回上海时,我正在金水的小三线抢收小麦,书没有还给我。
沈爱芳离开这个世界后,女知青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这本签着我名字的书,书又回到了我的手里。但随后又被别的知青借走了,再没有回来。
那个年代,面对生活艰辛、劳动苦累、前途渺茫,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寻找能让自己乐观起来的理由。
沈爱疆却从此不用再寻找,那个世界,没有病痛,只有乐观!
84、雷管鞭炮 '本章字数:124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9 12:03:42。0'
邵子昂平时是个十分成熟的人。
今天晚上,却像个孩子一样,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个雷管,满脸是笑地对我叫着:“我把它放了!”
我正抱了一堆柴禾想去烧炕,觉得他有点反常,就问:“放那有啥意思?”
邵子昂笑得嘴都合不拢,说:“待会儿告诉你。”
他拉我到院子里,只听见“砰”一声,雷管炸了一响。
邵子昂说:“就当放鞭炮庆祝了。”
然后,他告诉我:“刚接到了大学通知,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周后报到。”
我傻傻地看着他玩。
自从生产队推荐他上大学后,就有了他肯定要走的心理准备。但等到他马上要走时,不免有点心酸:又一个好同伴、好兄弟要离开知青点了。
我想起一年前,我、邵子昂、施卫疆三人说过“大家将来肯定不会在一起”的话,如今一点点地真的来了。
施卫疆走的时候,我流过泪;现在,邵子昂要走,尽管心里难过,但我不再想流泪。
有人说我这个身上有很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也弄不清楚:自己平时再苦再累流血流汗都不流泪,就是在兄弟分手时要流泪。
这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吗?那么古代没有小资产阶级时,离别流泪,那算是什么阶级的情调呢?
为了不让别人再说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决定这一周都到大田里干活去。
试试看,劳动阶级是不是还会流露“情调”?
邵子昂临走前提议我们几个陪他到南树林一游。
正当春季,绿葱葱的松树十分精神,林子里鸟语花香。
我们往林子深处走,一直走到与外世隔绝的密林之中,才坐下休息。
这里的松树有两人合抱那么粗,到处弥漫着松油的清香。
中午,暖暖的。“布谷鸟”叫了。
邵子昂想起那首:“漫绘远景笑田头”的诗来,又来了一句:“插兄插弟携手来”。
我紧跟一句:“空腹饱赏南林海”。确实,已经中午,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第三句想了半天,当我们拿锹去挖一棵小松苗时,云龙想出来了:“栽松留念意味凡”。
在知青点食堂的南窗下,我们把这棵小松苗种上,王雄涛把最后一锹土盖在松苗根上,然后一拍大腿说:“愿与青松共成材”。
就当是一份祝愿吧。
晚上,知青点开了欢送邵子昂的会。
插队干部老孙也从黑河赶回来,告诉我:“你上黑河师范的事已经没有问题了,但上学的时间要延后。”
我本来就对去黑河上师专没什么兴趣,开学时间延后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其实,我更乐得在生产队多待些日子。
第二天早上起来,邵子昂还没上车,发现食堂南窗下的那棵松树苗只剩下一根光杆了。
高朗说:“早上看见两只羊在啃。我以为羊又不吃松叶,它们啃着玩的,没想到啃得这么干净。”
邵子昂苦笑,摇摇头走了。
邵子昂走后,队委会决定增加新的队委。
考虑到我也要走,有人建议增加两个。这两人都从知青中选出:王雄涛和蔡景行,分别顶替已经走的邵子昂和即将要走的我。
知青班子开会,王雄涛在会上说了一通话,认为自己一年多来想干事却到处碰壁,现在终于好出头了。
晚上,去头道沟看电影“平原游击队”,昊宇一路上对我说:“王雄涛说那话是什么意思?他是指邵子昂过去压制了他?”
我对昊宇说:“王雄涛那话说的是不对,但我们也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将来要提倡一种风气:为人直爽真诚,处世老实谦虚,办事自然果断。归结起来是光明正大。”
昊宇不再说什么。
85、满盖鸟蜕变 '本章字数:156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7 09:58:45。0'
信息的传递真是太慢了。
上海到爱辉,信来回一趟要十天。
所以,家中父母知道我要上学,但并不知道我会去哪里上学,来了一封信问我:“哪个学校?”信里还例举了一些全国性的大学,主要是尖端科学、国防科学、理工科的。
他们知道我从小喜欢数学,喜欢理工。
无奈,上小学六年级时,文革开始,学习中断。我能读到的书以及我有能力自学的范围越来越狭窄,最后就只剩下我从小并不喜欢的文科了。
但无论怎么再苦的时候,我都乐观地、拼命地为希望读着书。就像老农所说的:就算是天塌下来,也得把地种上!
我用仅有的雨露浇灌我自己这块贫脊的土地。
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当别人都睡着了以后,我还醒着。
我在做两件事:记日记,背诗。两本手抄书王力的《诗词格律》、少儿读本《古代诗歌三百首》已经被我翻烂了;碰到不懂的字和词,我就查看《新华字典》和《康熙字典》。
下乡两年里,我已经背完了那本书中的300多首诗;我的日记则记录了北部边境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和社会底层农民的生活。
那时,还看过其它一些书,如:《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马克思传》、《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兰西内战》、《劳动创造了人》……
只要能拿到手的书,都看,看了还记笔记。我想过,在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之后,我起码还可以做一件事:当一个农民作家,写出我经历的农村故事。
我不知道如何回这封家信。
因为我想有两点父母会很失望,一、我要去读的不是理工科;二、我要去读的也不是大学。因为在我收家信的同时,我已经收到了黑河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
其实,这是一份录取通知书,上面没有开学报到的时间。
接到黑河师范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后,我上队里套牛车干活,有的老乡看出我的情绪不佳,就问我是不是对去黑河师范不感兴趣?
我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想了半天,还是把要不要去上学的犹豫心情,给父母写了一封回信。
春天的黑龙江畔,如图画一般,特别是我们这个知青点,在几棵高大的杨树遮盖下,显得生气勃勃。
不知怎么的,自从接到黑河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后,我对这儿就留恋起来了。我会久久坐在知青点院中的石盘上,注视着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这儿曾有过欢笑,曾有过哭泣,曾有过许许多多的故事……
在中国,属大龙小龙的人是人口急剧膨胀到极端的一代人,无论“大龙小龙”一生处在什么阶段,都会造成这个阶段的社会资源极度匮乏。因此,他们一生都会演绎出特殊的故事。
我突然想起村里的老人曾跟我说起的“飞龙鸟”的故事。
飞龙鸟,也叫花尾榛鸡,生活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中。它的体形很象鸽子,比家鸽稍大,体重在六两到九两之间。
雄鸟体长近40厘米,羽毛烟灰色,尾端有黑色条纹,眼栗红色。雌鸟稍带褐色,喉部棕色。
飞龙鸟多栖息于灌木丛或松桦树混交林中,春夏时雌雄成双成对,形影不离,有“林中鸳鸯”的美称。冬季则结成小群,钻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