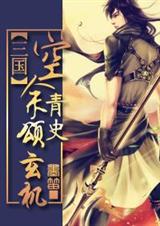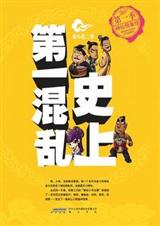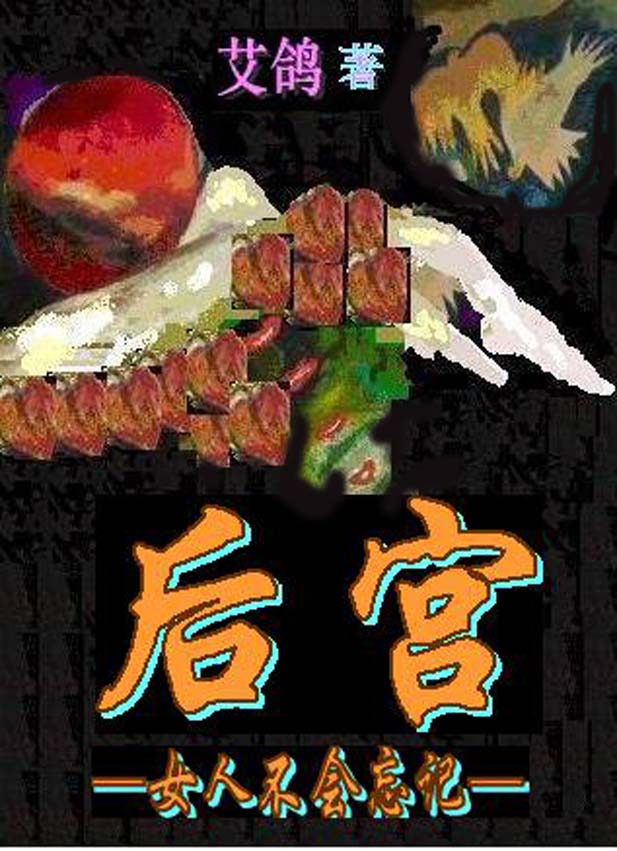中国知青史-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高皇帝远”的偏僻环境,为知青们交流学习心得提供了便利。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下,如果说还有一片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的“绿洲”的话,也只能存在于插队落户的知青群体间了。这种曾被有些知青自嘲为“躲在黑屋说黑话”的交流方式,的确起到了启迪发凡、析疑解惑的作用。
(二)“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
怀疑,是摆脱盲从的第一步,然而要迈出这关键一步,对许多知青来讲却相当艰难。农村封闭的环境和传统观念的弥漫,往往不利于知识青年接受新鲜思想。他们思想的逐步成熟,除了受益于坚持读书自学、彼此交流心得外,主要还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丰富的阅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他们的头脑逐渐变得复杂起来,于是以往奉若神明的东西开始受到质疑,一贯恪守的准则被打上了问号。“###”后期,极左教条已无力束缚广大知青的头脑,一个突出表现是怀疑论的普遍流行。
知青觉悟的历程(3)
1976年4月26日和8月28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题,连续两次刊登下乡知识青年黄一丁与刘宁的通信。在通信中,这对昔日的好友就“扎根”、“农业学大寨”、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辩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进行的这场“讨论”,当然不是一场公平往来的唇刀舌剑。在报纸上,代表正统观点的刘宁的两封长信均被全文刊载,持“怀疑论”观点的黄一丁的两封信却被大加删削。前者的信虚张声势,套话连篇,但依仗政治后盾,犹如不战而胜;后者的信实实在在,不乏真知灼见,但观点或被曲解,或被阉割,又没有畅所欲言的起码条件,在对方的猛烈攻击下,很快宣布“缴械投降”。但这场“讨论”很难以形式上的成败论英雄。人们正是通过这场轰动一时的“讨论”,对知识青年中广有市场的怀疑论的基本观点,有了较多的了解。而怀疑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也借这次“讨论”得以阐扬。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黄一丁与刘宁自幼相熟,从托儿所到小学,又到中学,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友。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他们一同从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以后,刘宁上调团政治部宣传队,黄一丁始终留在基层连队。1975年黄病退回京后,承刘母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作为老朋友,他在信中无所顾忌,对一些社会现象表示了怀疑和困惑:
关于“农业学大寨”,他表示支持和理解,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表示怀疑:
我觉得,如果乐观一点看,它也许能够决定今后农村的命运,也决定我们兵团的命运,也许我们农工们会不再像今天这样受人愚弄,被人瞧不起,被人随意摆布了。因此,也决定我本人的命运。我常想,有许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
关于大张旗鼓的“扎根”宣传,他也表示了异议。对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树立的“扎根”典型高崇辉的事迹,他认为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
对那些长期束缚青年头脑的政治教条,他用一种含蓄的口吻表示质疑:
有些政治教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去总是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
黄一丁信中的看法,应是他矛盾心理的真实表露,他曾经虔诚地参加过“农业学大寨”运动,鼓吹过“扎根”农村的大道理,也深切地体验到“###”以来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自幼接受的是工农当家做主的教育,面对的却是农工任人摆布的命运。政治的信条经不起社会现实的撞击,难怪他要对其可靠性产生疑问了。
他将这些解释不清又想弄明白的疑团诉诸笔端,不过是希望得到好友的点拨,谁知却因此酿起一场风波。他的信是1975年11月29日寄出的,大约半个月后,刘宁给他回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冗信。信中斥责黄一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又一悲剧”。并用耸人听闻的语气警告说:“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如果这只是朋友间私下里坦诚进行的思想交锋,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刘宁在复信的同时却把双方通信的复本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领导了。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团党委立即从黄的信中发现了政治异端气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后者也不甘寂寞,又当作重大事件上报兵团政治部黄一丁:《我和刘宁》,《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知青觉悟的历程(4)
尽管事态不断扩大,受到伤害的黄一丁却仍旧蒙在鼓里。接到刘宁来信后,他意犹未尽,又给刘宁寄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刘宁的喋喋说教颇不以为然,对受其攻讦的怀疑论反而推崇备至。他强调说:“人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的……而且我请教一声,难道现实中的许许多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和一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的存在都不值得怀疑吗?仅仅轻描淡写地用‘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服。”他还用以往的教训驳斥了对方的指责:“我们以前被社会左右得这样厉害,难道不正是因为太少怀疑的缘故吗?社会本身是辩证的(###主义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人的怀疑只不过也是尽可能地辩证一些的自然要求罢了。总而言之,怀疑怀疑,天塌不下来,没有怀疑,###主义是不能前进的。”
“###”中不可一世的极左势力,最容不得的就是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不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他们给芸芸众生定下的“天条”。在思想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反复申说“怀疑”的必要性、合理性,主张对社会现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无疑是知识青年中一种积极的动向。他们只有从怀疑起步,才可能达到理性的彻悟。
黄一丁在信中还坦言相劝对方;别用信奉宗教的态度来信仰马列主义。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
黄一丁的基本观点虽无可非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还是被归结为三大错误:反对学大寨;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其中以最后一条性质最严重。1976年初,极左派的风云人物谢静宜从《北京日报》的内参了解到黄、刘的通信,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返城风”的好材料,主张公开见报。于是4月26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通栏标题,将黄、刘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刊出。同时发表的《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反映,并称赞刘宁的复信“生动地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锻炼的青年一代的战斗风貌”。
这时的刘宁早已志得意满。他先被团党委授予“先进青年”的称号,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会议,实现了入党的夙愿。不久,即作为专吃“政治饭”的先进典型荣归北京,以便对黄一丁展开工作。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和组织部也派人找到黄,意在要他返回兵团。每星期,黄一丁都要多次到《北京日报》“谈思想”,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对怀疑论的围剿并没有到此鸣金收兵。8月26日《北京日报》又刊出被删节的黄一丁给刘的第二封信和刘的复信。刘在复信中继续就怀疑论大兴问罪之师:
我以为你怀疑的不仅是个“力量”问题,你实际上(不管是意识没意识到)在怀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实现,怀疑群众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怀疑###主义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你就会完全不相信###主义,和党离心离德,和群众的革命实践格格不入。这样危险的后果,你想到没有?
这场“讨论”的结局以黄一丁在《北京日报》上被迫发表《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而落下帷幕。文中,黄自称在接受“深刻教育”后开始“猛省”,“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激烈斗争的刀光剑影”,进而批评了“怀疑论”的五种“骗人手法”。这些违心之沦,只能表明思想专制主义的可怕。。 最好的txt下载网
知青觉悟的历程(5)
对“怀疑论”的批判当然不是针对黄一丁个人的。黄的一些观点,在知识青年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正因为如此,这场所谓的“讨论”才在知青中引起强烈反响。刘宁的复信空洞无物,热衷于无限上纲,加之将好友私信上交邀功的行径有玷为人行止,故被广大知青所不齿。黄一丁的书信则完全是推心置腹式的,不乏真诚,何况道出许多知青的真实感受,在充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中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的遭遇赢得广泛同情。云南西双版纳某农场机关在组织各队知青讨论刘宁和黄一丁的通信内容时,大多数知青公开与官方舆论唱反调,认为“黄一丁的信有水平”,符合现实;而刘宁“太激进了”,“唱高调”,“动机不纯”北京市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关于橄榄坝农场现状的调查报告》,1976年7月20日。。黄一丁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人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向他致意或表示支持。
(三)真理的呐喊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追求真理,犹如披沙沥金,只有锲而不舍者,才有望得到它。在农村简陋的棚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始终有一些知识青年孜孜不倦地从事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苦斗于社会最基层的经历,不但没有消磨他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反而促成了其思想的成熟。在一个不允许思想的年代,有思想便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罪过”,思想者受到###也就不足为奇。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是一代青年中最富理性、有思想、最具批判精神的精英。
在知识青年中,较早深入理论研究,并且提出独立见解的代表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遇罗克外,还有罕为人知的张木生。张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在“###”即将开始的1965年7月,他和同样出身高干家庭的同学陈伯达之子陈小农,以及李秋梦等人带头到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落户。当时,他们已约略得知毛泽东与王海蓉、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在校期间,他们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程学习反倒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取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坚信凭着一腔热血可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就是他们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原因。刚下乡,为了表决心,张木生写了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任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诗中抒发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自己的志向。陈小农批评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