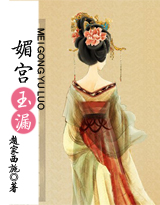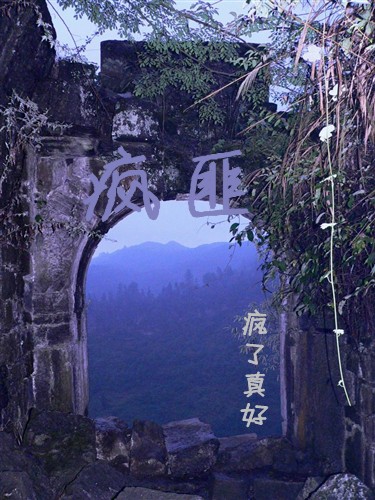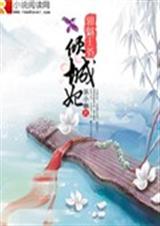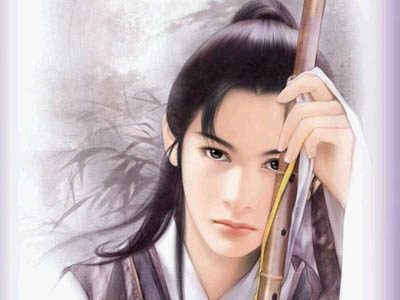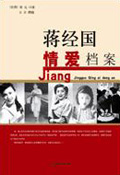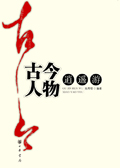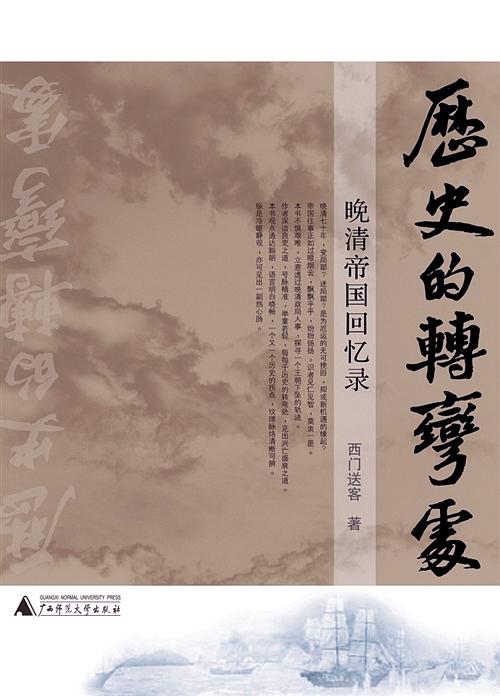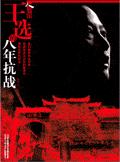第一章 楔子一声莺啼婉转,划破滴翠的树林,空灵回荡。阳光从密密的枝叶中细细地抖落,洒在碧草野花铺就的溪涧旁,扑闪着金子般细碎的光亮。莫莫把衣裳轻铺于溪面,流水潺潺,粗布衣物竟如丝绸般展开,柔顺飘逸。“真美!”她叹道。手指轻拂着衣裳,凉凉的溪水在指尖滑过,惬意如春末柳梢上的骊鸟,左手腕上豆大的朱砂痣在水里越显灵气。她从没有触摸过锦缎丝绸。在她的臆想中,那是仙子的天上物。和爹赶集的时候,她见过宝马雕车里的公子小姐,鹅黄柳绿,轻罗软烟,似是富贵落人间。好看是好看,可她也不强求。莫莫笑笑,敛了水里的衣裳,一把一把地拧干。该回去了吧,二娘要是知道她偷偷来了后山,又是一阵叨唠。山间茂密的蔓叶遮蔽了正午烈日的炙烤,空投下一片又一片的阴凉,清漪的山涧汩汩地冒着,清冽的凉意吸引她住了脚步。...
第一章“他们叫我疯了!” “我出生的时候也想其他孩子一样嚎啕,但不到一分钟我就转涕为笑,他们说我会为家人带来灾难。” “三岁那年,我缠着妈妈陪我玩,妈妈苦于要做手中的活,倒了一点酒给我,我学着爹爹的样子一口一口的咋着酒,妈妈看我有模有样,正好可以做手中的活。不一会就看到我一摇一摆的爬家里的地瓜干堆。” “我四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到山上去了,因为妈妈告诉我是从山上捡来的,我真正的妈妈家里是卖泥人。于是我就去找我真正的母亲。当我爬到半山腰上的时候被隔壁上山打柴的大伯碰到,强行将我带回来。” “七岁的时候爹爹送我去念私塾,私塾老师在我们依依呀呀的诵书中睡着,有人问谁敢帮老师拿去头上的柴草。我想也没想就走上讲台,结果被老师逮了个正着,说我朝他头上放东西,捉弄老师,狠狠的打了我十戒尺。”...
齐白石—一次自然生命的铺展(1)一 站在齐白石居住了31年,直到他生命最后的小屋门口,可以看见四周已经挤满了巨大、僵直、硬挺的高楼,开着玻璃窗,袒露着明晃晃的心脏。它们轻声地凑着靠近过来,像黑夜的狼群一样伺盯着眼下这几间破败的老屋。 门上写着的“谢绝参观”,把我挡在了齐白石生前生活场所的视线之外。这个房子是一个并不太大的器皿,装满关于他的记忆后就再也装不下别的东西了,可是奇怪得很,这里一开始,还盛装着供成群结队的人用来润喉咙的清水,然而,现在竟倏地在急忙赶来的人面前,变成一个湿嗒嗒的、发黏的土罐子,只装了无尽的荒凉和为数不多的几声孤寂的咳嗽。浓厚的阴影重重地压在这个小院子的胸口上,于是这小院仿佛是一个正趴在母亲膝上酣睡的孩子遇上汽车相撞时,猛然被震动惊醒了。它试图埋下头,把眼睛再睁大来看,是不是还没脱离刚才混混沌沌的梦?然而,它的怀疑已没有了容身之所。...
“你是谁?” 叶馨勉强坐起来,身子僵硬,估计是冻的太久。头很痛,让她有些理不清,她只记得自己冲进了马路中间,车子全都向她奔来,最后身体被撞飞了,意识一片混乱。 可是目前,是什么情况? 抬头一看,万丈悬崖,自己好像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巧的是,好死不死的落在了面前这个人的怀里。 那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子,盘着两腿,就这么坐在冰天雪地里。墨发挑起一半束于头顶,一身轻紫色衣衫,嵌着他颀长的身形。莹白玉簪散发着淡淡的光华,双眉微微斜起,张扬又邪气。 但是,落了就落了,鬼知道这么高的悬崖下面居然有人,至于这么暴脾气的把她甩开吗! 男子黑眸有几缕火焰在跳,瞪视着她,低斥怒吼着,“我还没问你呢! 死的方法多的是,北苍的悬崖也多了去了,你这个没脑子的女人,怎么就偏偏跑到这里来跳,你没死倒是要把我砸死了。”...
书名:《俾斯麦的一生:尘封信札背后的真相》作者:(美)乔纳森斯坦伯格译者:王维丹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内容简介作者简介乔纳森斯坦伯格分别于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其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多年在剑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曾任美国现代出版业巨头、慈善家和外交家沃尔特安纳伯格的欧洲现代史课程教授。书摘正文俾斯麦的“自御”奥托冯俾斯麦缔造了德国,但从未统治它。他曾是三位皇帝的臣子,却没有任何一位帝王可以随时解除他的职位。1890年3月,有一位皇帝这么做了。那一次,俾斯麦的公开讲话缺少了所有我们通常称之为魅力的特质。而就在1878年9月俾斯麦个人权力与名誉达到巅峰的时候,当时的一家报纸《施瓦本商业之神》(Schw-bischeMerkur)还这样描绘俾斯麦在德国国会的一次讲话:...
韩菲梦也走了过来,一脸探究的望着慕芳菲。 “不过是那么一会,能出什么事。”慕芳菲笑道,“韩姑娘,非常抱歉我并没有寻到你的玉佩。” “你方才没出什么事吧?”韩菲梦狐疑道。 “能出什么事,若是出事我还能这般平安回来吗。” “真的?” 慕芳菲诧异,听这话怎么好似盼着她不好一样? 韩菲梦也觉不妥连忙道:“后山有匪徒,我是担心你。既然无事便好,你方才回后山可还见到什么人?” “嗯?韩姑娘此话何意?莫非你是想在后山寻什么人?” 韩菲梦干笑,“哪有,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哦,也是想知道是不是别人把我的玉佩捡走了。” 韩菲梦敷衍几句便道自己身子不爽利就回自个屋子里去了,慕芳菲心中疑惑更多,这个韩菲梦怎么古古怪怪的。...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长歌行 作者:吴沉水 第 1 章 有人跟我说:名字只是一个符号。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说,一个人叫什么,只是为了称呼上的方便,如此而已。因此,叫什么并不重要。 真的是这样吗?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一个人叫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的东西太多。他的出身、他的家庭背景、他自身的修养、他所拥有的财富,他父母对他的期许,他内心的盼望、他站到人群里,周围的人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他。 名字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符号。 或者应该说,符号从来都不仅仅是符号而已。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说着句话的人,在我看来,都属于幸运的人。...
当尹翊诺醒来的时候四周一片黑暗。 “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在这里?” 尹翊诺掀开被子刚坐起来,房门就被打开了。 灯也随之而开,眼前突然被一片明亮的灯光所照亮,还没等她看清眼前的一切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拥抱打断。 “诺诺啊,我的女儿啊,你醒了吗?有哪里不舒服吗?头还痛吗?” 拥抱太用力,尹翊诺被抱的喘不过气赶紧用手轻轻拍了一下那个人的后背。那个人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松开了手。 尹翊诺把身子坐直眼睛眯了眯看清了眼前人的样子。 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看起来只有30岁左右,非常年轻,只是她的表情看起来非常激动,脸上布满了泪水。 “怎么不说话?怎么不回答妈妈?还痛吗?”漂亮女人又用手捏痛了她的掌心尹翊诺才反应过来。...
小蒋彻夜难眠 医师代罪羔羊(1)记得是1965年间,蒋经国因为政务繁重,工作过劳,导致长期严重失眠,精神不济。老先生知悉此事后极为关切。有天,蒋介石把蒋“太子”找到士林官邸,垂询他失眠的情况。他告诉老先生,为了睡眠问题,他吃的安眠药剂量越来越高了,可是吃再多的安眠药,仍然不能安然入睡。是时,蒋经国已经升任“国防部部长”,工作量较过去尤为吃重,任务繁重导致精神压力不堪负荷,是他失眠的重要肇因。 老先生告诉蒋经国,光是吃安眠药是不行的,心情一定要想办法放松,睡觉的时候不要再想事情,否则吃再多的安眠药都于事无补。蒋介石当场命令蒋经国,强制休假两个礼拜,交代他去日月潭涵碧楼度假,放空一切,什么事都不要想,在压力缓解的情况下,严重失眠应该会显著改善。为了强迫蒋经国休假,蒋介石特地指派了两位侍卫,名为陪同随护,实则要紧盯蒋经国,强制其寄情于山水之间,以放松心情。...
古今人物·自序喜欢历史的人,很少不对历史人物发生兴趣。难怪有人说:一册历史书在手,就好像和故人会面一样。 对待历史上的故人,生固桀纣、死即尧舜的不谓不多,爱而加诸膝、怒而坠诸渊的更不在少数。这可说是后人读史的态度暧昧,都不是公正不阿、左右不偏的读史人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历史书既然是记载历史人物的史籍,“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等,好像是惟一用来发掘历史人物的圭臬。作者却不敢作如是想,稗官野史、笔记杂札也不无可取之处。特别是历史以外的东西涉猎愈多,愈会发生疑问。原来,“董狐之笔”只不过是史官的理想,司马迁的《史记》已属难能可贵的史书了。 评判历史人物,最忌囿于时势,惧畏权威。如果抱这种态度,写出来的历史与人物,不是人云亦云,就是亚流之作,不看亦罢!但是,自作聪明、语必惊人,也不过是一新耳目而已,看又何用?因此,诸说要罗列,正稗共掇取,始能尽量做到存真求实,以免...
我们的民族确实会受到一时的挫折,但永远不会被击败。前 言 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难倒了不少学历史的朋友。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曾说过,历史书本应成为女孩子梳妆桌上的读物,随手可以拿来翻翻,但如今的小姑娘们看到历史书,就像见了瘟疫一样,仿佛历史书已经发霉发臭。这些哑然失笑的事实,都从不同侧面折射了当前历史教育和研究的困境。简单粗暴的庙堂史学和故作高深的学报史学,显然不是国人所爱,如今历史学家想做出既科学又艺术、又好吃又好看的学问,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 晚清历史的发展就像一个变化多端的股票市场。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帝国在一个封闭的经济圈里运行,但被卷入全球经济后,西方列强就像一些凶悍的外国机构投资者,让帝国再无宁日。譬如前两次鸦片战争,就让不熟悉国际规则的帝国股票市场大幅震荡甚至飞速下挫,直到洋务运动自觉的进行调整,才开始趋于平静并有了一波小行情。然而,甲午战...
作者自序(1)我是被王选感动的N个人之一。 王选的目标是感动世界。 在认识王选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六十年前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我的印象里虽然有一点模糊的关于731部队的残暴,但对于细菌武器对中国的攻击,我的知识是零。 某种程度上说,这不能怪我,因为在我所受的教育的知识体系里,有关细菌战与细菌武器的知识是零。在我所能接触到书籍里,也几乎见不到这样的叙述。 后来我知道,这样的感受和经历不止我一个人,2005年7月7日我所写的关于细菌战的报道在《南方周末》以特刊的方式登载出来,在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大多数的人都在惊呼:世间竟有这样的事,怎么以前会不知道! 王选,这个为细菌战奔走呼号了十年的女人,在她四十二岁的时候才知道了细菌战,她也发出惊呼:我怎么到现在才知道,是谁抹去了我知道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