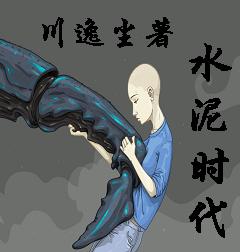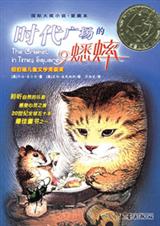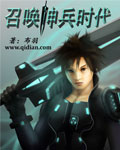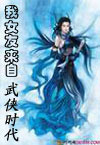群氓时代-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江兄返来,不拿自己当外人,大爪子抓起米饼就往嘴里塞,大嚼两口,直叫“给我称五斤!”香甜满嘴,香甜满额估计老哥们想起了他那猪油拌饭都是奢侈梦想的穷苦少年时代。
艳阳高照,忽然大雨倾盆,回程路上,南昆山的山中小气候显出威力。扭头看看恹恹思睡、嘴边流涎的江兄,觉得应该六月下雪才对,如此美景如此美味,竟然大半都落入此等俗人的腹中和眼中,真真是千古奇冤!
如此“简朴”、“绿色”、“惬意”的旅程,是否值得向大家炫耀呢?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在荒谬中成长
我们吃,我们玩,我们到处奔走,四处留下踪迹和脚印,上述种种,其实目的都是一个:我们要摆脱这平凡的生活!
可悲的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本身就是宇宙定律中最荒谬绝伦的表征——时空的扩展,其实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最后的归宿就是天文学的巨大黑洞。
由空间与时间构成的速度,难道比其他的构成有更深刻的意义吗?我们是否能找出一种使得空间、时间归于无联系的概念来吗?
在我们步履蹒跚的旅行过程中,我们所获得的那张童稚般的*,不过是一种消除烦躁的沉溺而已。我们在力图抹杀时空的界限,仅此而已。
生命,并不能通过眼球看到的更多风景和喉咙吞咽的更多美味而改变形式,也不能在有限的生命时限内消耗更多的生命空间而使得我们的客观宇宙改变维度。
但是,熙熙攘攘中,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却能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我们生命活力的某种刺激物,让我们乐此不疲。
生活,充满了悖论。我们的创造力越来越巨大,在精神的层面却不会改变和提升什么。似乎我们都能主宰浩渺的太空,却把握不了自己无常的命运。在如此富足和物质充盈中,我们却如此贫困无依。在到处人满为患的氛围中,谈起田园,谈起理解,谈起道义,谈起美德,谈起纯粹的精神享受,总是让我们心中涌起某种恶意。
无论我们读了万卷书,无论我们行了千万里,精神的偏狭,都决定了我们依旧是井底之蛙。面对一个日新月异的深奥的、无法揣测的世界,在我们唧唧喳喳的吵闹声中,在我们大呼小叫的暗自窃喜中,如何摆脱樊笼进入纯粹的自由,似乎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可能性。
很多文人大嗓门,叫嚣“金钱买不来幸福”。其实,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购买幸福而已。
我们的人生,恰似漂浮在一个无比巨大的池塘之中,我们既是水滴,也是空气,融入,就是幸福感的来源。夸耀性的物质消费所带来的*,与真正的幸福感,是大相径庭的。
在“群众”的声音引导生活潮流的时代,精神总因散漫而消亡,所有高贵的知识,都被商人们处理到某种平均的智力水平,这一切都是源于卖钱的冲动,从而使得文化变得日益浅薄和普遍降格,进而导致我们的价值观普遍贬值。
事情发展下去,所有的一切,恰恰应了雅斯贝斯的论断:
“人们迅速厌倦于他们已经听说的东西,所以不停息地猎奇求新,因为没有其他东西能够激发他们的想象。凡是新奇的东西,都被当作人们正在寻求的最重要的知识而备受欢迎,但随即又被放弃,因为人们所需要的,都只是一时的轰动。渴求新奇的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新世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历史不再被考虑的世界里。因此他老是不断地空谈‘新事物’,好像‘新事物’就因为其新就必定是有效的。他谈论‘新思想’、‘新的生活观念’、‘新体育’、‘新的客观性’、‘新经济学’,等等,等等。任何东西,只要是‘新的’,必定具备肯定的价值;如果不是新的,便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那些想当“大师”的文化人(1)
记得春天的某个早晨,因为要坐早班机出差,一向有出差紧张神经官能症的我,醒得比鸡还早,昏昏沉沉地坐在沙发上等着天亮。
浪费时间和虚度年华,最有效的手段是看电视,我拧开了这种任时光无限消磨的机器。
噩梦一般,电视台在播放余秋雨的“秋雨时分”——余教授正襟危坐,依旧是那副道貌岸然的、凛然不可犯的神情,依旧是天下苍生尽被怜悯的笑容,面对眼前围坐一圈的美丽如花、天真有邪的名牌大学女生,他正口若悬河地讲述着北魏孝武帝改革的宏大历史叙事。
很显然,百家讲坛老教授们的“学术超男”的火热势头让余教授窝心上火,于是丢开他最拿手的*式激情澎湃的散文,开始到电视上来铺陈历史了。
人,不能没自信,但也怕太自信。过于自信的人,往往有挣脱地球引力飘飘上天的良好感觉。其实,对于一向巧言令色的余教授来讲,历史,是他的一个死穴和软肋。试想,他仅仅写了几本汪洋恣肆的文化散文,就能把“致仕”当成“当官”来解读那样的低级错误,愣能让金老先生弄出整整一本《石破天开逗秋雨》的书来给他挑硬伤。文章、学识如此伤痕累累,依理说,他应该暂时偃旗息鼓,恶补一下历史才对啊。
不!他不!越是艰险越向前、死不忏悔的余教授,他不仅没有安静下来补习历史,在夹枪带棒地讥讽那些对他提出善意批评的人是他先前的“政治”对手的同时,他又不甘寂寞地频频露脸,常常在类似“秋雨时分”这样的电视节目中重新抖落才学,卖弄悲天悯人。为了显示博学,为了让人觉得自己莫测高深,他总是用书面语来讲述本来就佶屈聱牙的历史。
看着电视屏幕上那张雾气腾腾的油脸,我满怀恶意地想听听余教授的高见。结果,我只是听到了系列的大言铺陈。对于北魏的历史,余教授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估计他连冯太后是孝文帝的奶奶而不是他妈这样的历史事实都不知道。
怀着惯有的傲慢和骄横,他大讲特批汉人知识分子的“民族沙文主义”。余教授啊,在南北朝时期,是北方汉人生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连士族高门都要依附胡族政权才能生存,哪里还谈得上“汉族沙文主义”?
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我忽然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余教授,其实连古汉语的断句都不懂——在讲述这段历史时,他讲了一段这样的故事: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孝文帝到了一个城市,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妇女坐在车中,作鲜卑打扮,就让人去唤那个城市的“小皇帝”过来(余教授真逗,北魏的城市还有“小皇帝”),问他为什么改革措施没有落实下去……
这个故事呢,确有其事,讲的不错,原本是为了说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坚决态度。
但是,余大教授所说的被孝文帝唤来责问的那个“城市”的“小皇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好在我家里有两套中华书局出版的带注释的、全本《资治通鉴》,于是我翻到第142卷,发现有这样的句子:
“魏主(孝文帝)谓任城王(元)澄曰:‘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对曰:‘圣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著小袄,何谓日新!’对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王),此何言也!必欲使满城尽著邪!’(元)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
那些想当“大师”的文化人(2)
也就是说,在余教授蜻蜓点水般的、自以为是的电视演讲“备课”过程中,可能还真翻了几翻古汉语的原文,但他竟然把“任城王”这个名词都理解错了,就这三个字,他囫囵吞枣地理解成为是某个人“担任”一个城市的“王”(即他所说的“城市”的“小皇帝”)。如此错误,看似不大,却彻头彻尾地暴露了余教授连基本阅读古代典籍断句的功夫都不具备,真真让人齿冷,同时让人心寒——这位“大师”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名人啊!
本来睡眼惺忪的我,怒火中烧,当时我真想扑入电视,把余教授拉出来,扇他两个大耳光,而且还要语重心长地怒斥他:“你写文章丢脸,还有个阅读的延迟性,还可以再写文章抵赖、反驳、辩解。但是,连简单粗疏的文案工作都如此马虎,看了几眼历史书,连断句都不会,囫囵吞枣,就匆匆上台,在电视上丢人现眼,有影有音,证据确凿,授人以柄,太掉教授的份儿!”
当然,余教授一向是很强硬的,他从来不认错,哪怕是白纸黑字,哪怕是黑影白屏,这位自诩为中国第一文化学者的精英,从来都是利齿钢牙。我觉得,余教授肯定读过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语,自以为是地觉得知道如何驾驭读者:
“(群众或读者)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的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尚自由……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它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
过了几个月,我看到学者王晓渔的博客,这样写余教授:
“一度沉寂的余秋雨先生,6月因为含泪劝告地震灾民不要请愿、不要被反华媒体利用成为公众焦点。9月,两地政府分别送来礼物:先是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的老宅正经有关部门上报申请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随后上海市教委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对于故居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余秋雨先生多半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已经易主的老宅,正是由他本人买下转赠当地政府;对于自己被称为大师,一贯严肃的他难得幽默地说:‘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看到余教授这典型上海味的“幽默”和谦虚,我面前立刻浮现出他那张戴着大眼镜的文人脸。他的那张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虚伪,浅薄,粗鄙,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急功近利,又当名妓又立牌坊……
特别感到可笑又可悲的是,人还没死,余教授就已经自己给自己安排“生祠”,真比魏忠贤不如!
遥想当年“九千岁”魏公公,人家活着的时候建有生祠,也不是自己花钱买房子给自己弄的。天启六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以机户感恩的名义,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活人纪念馆),地点位于关羽庙和岳飞庙之间。为此,潘巡抚上疏表奏自己的“公心”,谀赞魏公公“心勤体国,念切恤民”。由此一来,天下阿谀官员群起效仿,魏公公生祠遍天下。
从规模上讲,余教授现在的“生祠”,乃破落一间房耳。但从诛心之论讲,余教授还不如魏忠贤——因为茫茫天下,并无人拍马附和,乃只是他自己想出的馊主意。
人家魏公公的生祠,规模巨大,九进殿庭,肃穆如太庙,壮丽如帝居。当年大同、湖广、蓟州等地的生祠中,魏忠贤坐像皆系纯金制成,头戴冲天冠,手执玉笏,俨如上天尊帝派头。由于巧匠众多,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

![[种田]新石器时代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0/28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