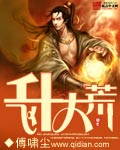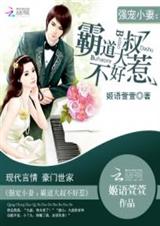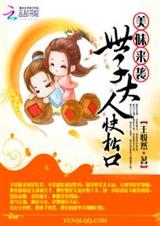论北大-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动中知识分子在民间的中心地位的历史经验的鼓励,他现在所要追求的是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中的中心地位,是要成为政治家的指导者,甚至自己就来充当拥有强权的“领袖”。如果说洋务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的位置都在国家、政府的权力中心的周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第一次从国家、政府走向民间,并试图建立北京大学这样的民间思想文化中心,以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抗;那么,现在,胡适又试图回到国家、政府的权力结构,并试图自己去占领中心位置。——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位置的移动”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9)
我们的讨论再深入一步,就会遇到这样两个问题:其一,胡适们的“专家政治”的实质是什么?其次,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胡适们的“专家政治”的理想能够实现吗?在中国现代政治的结构中,他(他们)最后将实际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注意到,前面引述的那篇《再论建国与专制》的文章,是在1930年代关于“开明专制”问题的论争中发表的。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的发动者,都是胡适圈子里的朋友,他们鼓吹“开明专制”的主要理由是:欲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政治乎?》,原载《东方杂志》31卷1号。,这与胡适“好政府主义”强调“强有力的国家”是同一思路。但胡适本人却是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在《再论建国与专制》等文中陈述的“理由”却很耐寻味。他说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并且“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或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不难看出,他只是认为“中国今日”并不具备实行“开明专制”的条件,却没有否认“开明专制”本身。当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时,就说得更清楚:他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有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它“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可以“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因而是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但从根本上说,胡适所追求的还是“英杰的政治”《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4—378。,“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弘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一年来关于民治和独裁的讨论》,《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9。这就是胡适一直鼓吹的“专家政治”,他又称之为“研究院的政治”——这一命名所揭示的正是“进研究室主义”与“好政府主义”的内在联系:胡适说得也很明确,“现代教育”(大学教育与研究院教育)就是“专门人才的训练”,“领袖人才的教育”《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6。,径直说,就是要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为从阿斗们的“民主宪政”过渡到诸葛亮们的“开明专制”创造条件与机会。《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8。胡适并不回避:他所提倡的“专家政治”就是“开明专制”,他称为“现代式的独裁”或“新式的独裁政治”。《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4、505。这本是“专家政治”的必然逻辑:既然“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就必然要排斥“阿斗”的参与,将权力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领袖人才)、技术精英(专门技术人才)手里,实行精英专制独裁。但胡适又宣称,这样的“专制”是“开明”的,是能够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中的“为民作主”而已。很显然,在胡适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开明专制”的现代化模式里,是根本拒绝公民(即他所说的“阿斗”)的政治参与的;他也直言不讳:“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30。曾有一位学生在读了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后,给《现代评论》写信,对胡适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民族解放的命运应完全取决于政府之手;人民做到民气的表现,就算尽了天职,其余都可以不问而惟从事于个人的修养了。”应该说,这一概括是相当准确并且抓住了胡适的要害的;但胡适在写信回应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参看刘治熙:《〈爱国运动与求学〉》及胡适“附言”,载《现代评论》2卷42期(1925年9月26日)。胡适的“附言”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题为《刘(漏一“治”字)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在胡适这样的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眼里,民众与民众运动总是非理性的,他们有着几乎出于本能的防备与疑惧;在他们看来,民众运动如果有意义的话,不过是表达一种可供利用的“民气”,最后还是要靠自己这样的“负有指导之责者”。而这,其实也正是一切独裁的统治者的逻辑:国家大事由他们来掌管,老百姓只要做好本职工作,“救出你自己”(这是胡适《爱国与求学》里的话)就行了。这就暴露了一位研究者所说的自称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代表的胡适“潜在的反民主的倾向”,构成了他的内在矛盾。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06、249。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0)
而更使胡适陷于尴尬的,是他无法回避的现实:不管他怎样鼓吹“好政府主义”,提倡“专家政治”,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所面对的中国政府,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洋政府,还是之后的国民党政府,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领袖的独裁”、“一党的专政”政权。《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5。按胡适的理想,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责任是“监督,指导与支持”;但独裁政权是根本不允许“监督”,更谈不上“指导”的,于是,就只剩下了“支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在与宋庆龄等在“保障人权”问题上发生争议时,胡适就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为,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民权的保障》,《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295。这样,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对反抗力量的“制裁”、镇压,在胡适这里就具有了合法性;胡适也就走向了为一切“事实上的统治政权”辩护的立场。在1920年代,胡适在最初提出“好政府主义”时,还曾坚持“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样的“浅显的革命原理”,甚至表示:“(政府)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的手段的必要了”;《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718—719。而到了1930年代,他竟转而为“独裁政府镇压反抗”的合法性辩护,这正是表明了胡适政治上的日趋保守,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好政府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另一个不可解的矛盾是,他的“专家政治”、“知识分子参政,并指导国家、政府”的主张,在专制体制下,始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梦想。在胡适等人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以后不久,签名者中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就获得了一次组阁的机会,胡适们也确实兴奋了一阵子,组织了不定期的茶话会,经常在一起议论政治。但很快王宠惠内阁就因一事无成而倒台,罗文干本人还被诬陷而入狱。据胡适说,汤尔和在王内阁下台以后,曾对他说:“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大家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这一周·63解嘲》,《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65。不仅是政治(政治家)与学术(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与行为逻辑,更重要的是,大权掌握在军阀手里,这些被视为“好人”的学者参政,事实上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相反,却会有被利用的可能。胡适对此似乎有所警觉,他转而赞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特别是他对“有奶便是娘”的“助纣为虐”的“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的批判,支持他“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的号召。《这一周·55》,《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55。胡适显然看到了在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的参政有成为独裁政治“帮忙”的危险,因而对拟想的位置作了一个调整:议政而不参政。其实他在此之前所写的《政论家与政党》里,就已经提出了作“‘超然’的,独立的”,“身在政党之外”,却通过“造舆论”,发挥“调解,评判与监督”作用的“政论家”的设想。《政论家与政党》,《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70、71。现在,胡适更是断然将《努力》停刊,宣布“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情”,“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97、398。但胡适事实上并没有放弃议政以至参政的努力。1930年代,他先是创办《现代评论》,以政论家的身份从事舆论的监督,但同时又几度试图与国民党政府及其领袖对话,以后就始终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直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以发挥对国家的“指导”作用,这一“专家政治”的理想,对于胡适,有着永远的诱惑;但他又时时小心地要维护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构成了胡适的选择的基本矛盾。他因此多次跃跃欲试地准备参政(入阁、组阁),但到关键时刻,又总是抽身而出,最后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这样,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胡适最终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他的最后定位,是充当国家的“诤臣”与掌权者的“诤友”。在1935年所写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胡适明确地提出,“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诤臣义士”。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660。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1)
而鲁迅却作出了另外一种选择,并且对胡适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鲁迅首先质疑的,是他的精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