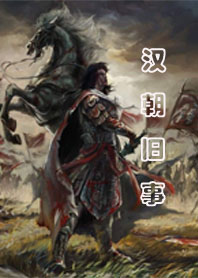汉朝旧事-第7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也,势也。
“着廷尉府严查邓通贪赃枉法之罪状!”晁错高声宣道。
张释之恭敬地接下谕旨,晁错也不跟他多说话,便转身上轿离去。
张释之手捧谕旨,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这邓通还未审问,罪状未明,何来‘贪赃枉法’之说,况且,一道谕旨也无需晁错这种新任权臣亲自来颁布吧,这一切看似莫名其妙的事情,似乎透露着什么讯息。如果真有,那么解释只有一个。
张释之长叹一声。进入书房,思虑再三写下一份辞官书,放入暗箱锁住。
以他的判断,邓通是在劫难逃了。邓通一倒,那么下一个或许就是自己!
这就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吧,当今天子性格急躁那是全天下皆知,他若认定的事必然会急着动手,即便将来后悔也是在所不惜。等他动手,倒不如早日离开。
刘启毕竟不是刘恒啊。
张释之打定主意后,仰头向天际望去,刘恒的音容笑貌尽在眼前,他喃喃道:“先帝啊,臣不能为江山社稷尽力了啊!”
邓通被打入大牢的消息不胫而走,往日皇帝跟前的红人成了阶下囚,凡是跟邓通有过节的人便趁势落井下石,不日关于邓通的罪行就像雪片一样飞到刘启的龙案前。
刘启看着堆积如山的弹劾揭发奏折,让他没想到平日看似左右逢源,八面威风的邓通,父皇依赖的近臣,竟然会如此劣迹斑斑。
刘启虽然性格急躁,但却也极善于见微知著,他的心情并没有因为抓到了邓通的罪证而高兴,反而更加阴郁了。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父亲会倚重如此奸佞之徒。父皇无疑是圣明的,然而如果邓通如此不法,他又怎能毫无察觉?圣明如父皇者,尚且无法察觉奸猾之徒,那我呢,我能做到吗?
刘启无心阅读奏折,他要想通这个问题。他走出前殿,踱步来到前殿正面百步之距的天禄阁,天禄阁与石渠阁是宫中藏书之地。刘启开始翻动着以里面的各种藏书,希望从圣人言论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刘启依稀记得自从板杀吴王太子时,他便被父皇关在天禄阁里习诵圣人言语,一面以示惩戒,一面学习礼仪,所谓礼让而温。整整一个月啊,那是怎样的煎熬?!他还清晰地听到母后在阁门外的哭泣和哀求,他也清晰地听到父皇严厉的声音:“国之储君,不知礼,不守法,急躁处事,暴虐杀人,将来便要误国误民!”
急躁处事,暴虐杀人。。。刘启当时听到父皇的断语,连死的心都有了。但年小的他熬过来了,虽然整天被禁囿在狭小的阁楼里很是枯燥无味,在天禄阁里,除了一遍遍地翻看那夹杂着发霉气味的竹简,实在无事可做。
但刘启却在那时,真真正正地学会了思考。
以后每当他有想不明白的事,他便会在天禄阁与石渠阁转悠,往往有意外的收获。
刘启看着眼前无尽的藏书,急躁的心情顿时平静了下来。
在翻阅到韩非子的<;说林>;<;孤>;<;愤>;之时,猛然间,他豁然开朗,邓通是愚钝之人,无非是贪利,对国家对朝廷并无大的破坏作用。可恨可怕的是那种伪善而有心机的小人。
父皇不会不明白邓通的劣迹,但他却把他留了下来,也是冲着这一点,这是一个愚钝没有心机的贪利之人,而且还有一些雕虫小技。但是这么多弹劾邓通的奏章又怎么解释?
唯一的解释是,世态炎凉!树倒猢狲散,人走茶凉,其中有些是真的,但一定有大部分是捏造的。我大汉煌煌五十载,世态炎凉便已如此一般,国之不幸!
想明白这些,刘启已经想清楚了对邓通的处理。
巧的是,廷尉府已经把邓通的罪状已经呈了上来。
刘启打开一看,无非是邓通利用严道铜山中饱私囊的罪名。至于什么结党营私,意图谋反等等之类的纯属子虚乌有。当他看到奏章上写着邓通十分配合,对罪状供认不讳之时,刘启竟然大笑,他心想:“以邓通的个性,即便安他多少个罪名,只要能少受点牢狱之灾,他定然都会供认不讳,这个张释之,判案倒真是公正无私!”
刘启基于邓通的罪证,更为了打击树倒猢狲散的不正之风,决定没收邓通所有家产,连饭钱也不要留下,贬为庶民。
邓通由天下首富骤然变得身无分文,而且加上养尊处优惯了,加之年纪大了忘记了劳动,无权无势的邓通到哪都不讨好,不仅是好友,甚至是亲戚都躲得远远的。馆陶长公主见他可怜,不时赏他几口饭吃,后来长公主忙于储位之争,就无暇顾及邓通了,饥贫交迫的邓通最终饿死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冬夜。其状之惨,让人唏嘘不已。
二十年前,有个相士说邓通会饿死。二十年后,邓通真的饿死了。
不管是真是假,有那么句话说出来警醒世人,出来混,总要还的。做人,还是得常怀敬畏之心,少发不义之财。
邓通在朝廷消失后,一个深夜里,张释之褪下官服换上便服,把廷尉大印封存放好在几案上,然后对着官印拜了三拜,对在府外等候的家老问道,“夫人和公子都安排好了吗?”家老点头,他便头也不回地钻进了轩车之上。
轩车直往长安东南角驰去,半个时辰之后,张释之下车来,对着肃穆的霸陵行九叩大礼,便又上车缓缓离开了。
翌日,一道奏疏摆放在刘启的龙案上,刘启打开一看,大吃一惊。
第81章:申屠嘉喋血
“可恶,竟然不辞而别,张释之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刘启将张释之的辞官书重重地摔在地上。
陪侍一旁的内史晁错默不作声地将辞官书拾起,摊开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老师,朕想把他抓回来活剐了,让那些个不能为朕所用的臣子引以为戒!”
晁错见刘启脸色气得通红,并未马上应答,而是眉目半睁,似乎另有所思。多年与刘启的相处,他对学生刘启的个性再清楚不过,他清楚刘启只是说一时气话而已,如果在此当口,便答疑解惑,只能推波助澜,无助于事情之解决。
刘启并未得到老师的回应,渐渐平静下来。刘启同样清楚每当晁错有异议,都会摆出如此神态,等他刘启发完脾气再进言。
所以,刘启稳住自己的情绪,想听听老师的想法。
晁错微睁的双眼突然一亮,向刘启说道:“陛下,切不可对张释之施以惩戒!反而应嘉赞其劳苦功高!”
“何也,朕为何不能惩处一个擅离职守的臣子,却反倒要嘉赞其功,如此一来,国法纲纪何在,如此一来,朝廷不是成了想留便留想走便走之地,朕的脸面何存?”
“陛下,臣之谏言意义有三,一则陛下初即帝位,当以凝聚人心为要,张释之乃先帝重臣,身背遗命,何况他在民间极有威望,若决然杀之,恐致天下失心,需知恩威并施为驭臣之道啊,此为一;二则,张释之与陛下有隙天下皆知,若陛下不但不追究其擅离职守之罪,反而厚重待之,那天下人定然会以为陛下仁圣,此为二;三则,张释之辞官而去无非畏惧陛下追究之前不敬之罪,而陛下此举定然能让张释之对陛下感恩戴德,陛下可下旨斥责他不辞而别,同时同意他辞去廷尉一职,但得令他改任淮南相,为陛下钳制诸侯,此为三!”
刘启一听,一时茅塞顿开,爽朗笑道:“老师当真高明也!朕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好,就按老师说得办。老师相才,朕之大幸也!”
晁错也不谦让,捋着三角须脸露微笑连连颔首。
不久之后,主动辞官的张释之便赶往淮南国赴任淮南相,对于已对仕途绝望的张释之来说,只要能离开京城是非之地,已是万幸了。
晁错处理张释之的谏言,为新天子赢得了不少的赞誉和人心。
紧接着,在晁错的谏言下,刘启下令减轻刑罚标准,并减轻田租税赋,而且继续加大募民徙边的力度。
在文武大臣议政之时,刘启因为经验不足,面对群臣有些惶恐,每当这时,他便习惯性地询问晁错:“老师以为如何?”
晁错自然耐心为之一一谋划,晁错眉飞色舞,唾沫横飞的时候,一旁的申屠嘉只能气得浑身发抖。
到底谁才是丞相?申屠嘉心中不解。
已是而立之年的刘启并非不能察觉现场微妙的氛围,但现在的朝廷,他能信任谁呢?
九卿当中目前只有郎中令周仁,廷尉张欧是刘启的老部下。
然而这两人在朝议上几乎帮不上什么忙,周仁擅长武职,张欧忠厚老实话也不多。
唯独晁错,能言善辩,独断多谋,熟谙政务,在他的教习下,刘启也渐渐地找到了为君之道的感觉。
朝政的运转在刘启即位后竟然以内史府邸为运转中枢,而丞相,御史大夫却被撇在了一旁。
老丞相申屠嘉因此变得坐立不安起来,天子只听晁错的,根本不在意他这个老臣的言语,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申屠嘉认为自己是历经四朝的*,不当受到如此待遇。他一步步从基层干起来的,从材官到队率,从队率到都尉,从都尉到郡守,再从郡守到御史大夫,乃至丞相,都是一刀一枪,一点一滴,积一生之苦干累干换来的。可他晁错呢?仅凭几篇文章当上了太子的老师,如今小人得志,便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凭什么?凭他的才学,错,大错特错,要论才学,贾谊是他万倍,然而贾谊却没有他的运气,归根到底,晁错凭的是运气,非真才实学。此等奸伪之人,我又何必处处退让,被他逼入死角。
申屠嘉越想越气,对晁错的嫉恨之火正愈来愈浓烈地灼烧着他的心灵深处。
申屠嘉本是正直肯干之人,待人厚道,从刘邦到刘恒,正是因为勤勤恳恳,待人厚道,所以屡屡升迁,最终攀上人臣的顶峰,凭借着四朝*的资历,他就连袁盎这种牙尖嘴利,心高气傲的人,都能引为座上宾,可偏偏这个晁错,他却如何也压抑不住对他的嫉恨!
晁错的咄咄逼人让申屠嘉感到了巨大的生存危机,原本以为新皇帝上任,对于心腹大臣自然会倍加倚重,现在看来,不光是倚重,刘启是要晁错取他而代之。
这位年逾花甲,一辈子忠于职守的老头被一股巨大的耻辱感包袭全身,竟然寝食难安起来。
只要见到晁错,申屠嘉必然怒目相向。
晁错却不以为然,在他眼里,丞相的位子迟早是他的,申老头迟早要下来,只不过现在缺少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已。晁错的得势为他招徕了无数的投奔者,也招徕了无数的敌人。
这其中便包括同样言语犀利的袁盎。
袁盎早年跟晁错便多有不合,两人经常在朝中争执不休,谁也不服谁。争执的恶果到后来,终于演变成深深的忌恨,乃至于有袁盎的场合必定找不到晁错,有晁错的场合必定看不见袁盎。
袁盎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当年他在朝廷初展头角之时,很受刘恒赏识,袁盎因此屡屡犯颜直谏,刘恒一怒之下把他贬出京城,贬到了陇西当都尉,因为治陇有功,迁为吴王相。
虽说吴国相距长安甚远,但袁盎一直是身在边疆,心系朝廷,为此还专门游说丞相申屠嘉,成为他的座上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