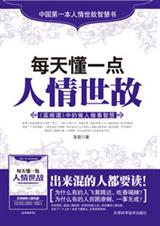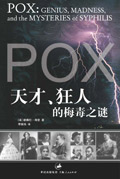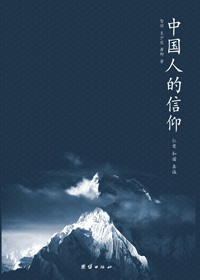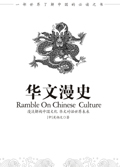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臧克家与闻一多
臧克家与闻一多的相识是在青岛,那是1930年的夏天。臧克家是青岛大学英文系的新生。开学之后,臧想转到中文系,就去国文系主任办公室找闻先生。当时有几个学生都想转,问到臧时,先生问:“你叫什么名字?”“臧瑗望”(臧是借臧瑗望的文凭考入青大的)。“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就这样,臧以《杂感》中“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诗句见之于闻一多先生了。
此后,臧克家读了闻一多的《死水》,便放弃了以前读过的许多诗,也放弃了以前对诗的看法;觉得如今才找到适合自己创作诗歌的途径。
对《死水》,臧克家几乎全能背诵,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对臧的诗,闻是第一个读者。一次暑假,臧克家把自己的《神女》寄给老师,寄回来时,在自己喜欢的一个句子上有了红的双圈,让臧克家高兴得跳了起来!
1932年夏天,学校里发生了*,是为考试制度定得太严,同学们把责任全推到闻先生身上,有些人写打油诗骂他,他泰然处之。暑假之后,他便转到清华大学去了。他在给臧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1932年六月底的一天,臧到清华园去看闻先生。闻住着一方楼,一个小庭院,四边青青绿草,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桌上的大本子已经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了。这时的闻一多不再写诗。“七七”事变,使臧再访闻先生的事成了泡影。七月十九号臧离开北平,在车站上碰遇到闻先生一家。臧在德州下了车,辞别了闻先生:是永远辞别了他。
以后,臧一直在战地上跑,偶尔在画报上看见闻先生的照片,胡须半尺长,成了清华有名的四大胡子之一。臧每隔一年半载就给先生写封信,以表怀念之情。后来,闻终于回了一信。臧自是十分惊喜。劈头第一句:“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信中对臧想到闻身边工作写道:“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此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斗量,何重于你。”
这时候,关于他的生活困苦,臧已有所闻,为了补贴生活,他给别人刻图章,另外还给一个中学改国文卷子,但他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些。
关于他的学术以外,他写道:“近年来,我在'联大'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他在昆明领导文化运动,为*而战,他像一面大旗,引导着千千万万的青年。他呼喊的波浪,已波及全国。他已经不是孩子的父亲,学生的导师,而是四万万人民的闻一多先生了。但也由此引起官方的不满。
报纸上刊出了*解聘他的消息。许多朋友声援他,向他致敬。臧写了《擂鼓的诗人》,以示抗议。闻在回信中写道:“你在诗文里夸我的话,我只当是策励我的。从此我定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而闻竟死在了暗枪底下。这枪是无声的、卑鄙的;而他的呼声却是响亮的。他的血流在了他工作多年的昆明的土地上,他为*而斗争的精神却是伟大的、永恒的。
臧一直珍藏着老师为他写的“四十初度”的钟鼎文的条幅和那几封天真热情的长信。
“伯乐”的眼力:包天笑与周瘦鹃
包天笑,原名包公毅,字朗孙,曾用拈花、钏影等笔名。江苏苏州人。1901年因与杨紫麟合译《迦因小传》而步入文坛。1907年与冷血创办《小说时报》,后来又创办过《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时尚杂志。在办报刊的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他的小说多为政治、言情、武侠、教育等题材,以消遣和游戏为宗旨,因而被誉为中国第一代鸳鸯蝴蝶派作家。在鸳鸯蝴蝶派作家中,与徐枕亚、李涵秋、周瘦鹃、张恨水等作家被称作“五虎将”,包天笑则被列于首位。而包天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他曾对朋友说,他的小说是以上海报章新闻为素材,以揭露社会黑幕和世态炎凉为主,在选材上与卿卿我我的“鸳鸯蝴蝶派”不同。不过,他承认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是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周瘦鹃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时,英文成绩突出,毕业后留校教英文。无奈他不善于口头表达,对教书没有兴趣。他便翻译了一篇英文小说投给《小说时报》,主编包天笑读了他的译稿,十分赞赏,当即安排发表。在包天笑的鼓励和支持下,周瘦鹃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经常有译文见诸报端,很快就成为海上文坛的知名小说翻译家,因而周瘦鹃总是对包天笑以师长相称。
1916年,周瘦鹃应聘到中华书局担任翻译编辑,同时还被包天笑介绍加入南社,他为南社编写了剧本《爱之花》。此后,包天笑与周瘦鹃过从更为亲密,彼此间建立了忘年之谊。在周瘦鹃结婚时还特地请包天笑做证婚人。当时包天笑正主编《小说画报》,他鼓励周瘦鹃创作小说,更深入地投入到文学事业中来。周瘦鹃不负恩师的期望,很快就根据自己结婚的体会写了篇《芙蓉帐里》,请包天笑批评指导。这篇小说写的是在新婚之夜他与妻子恩爱的故事,写得细腻、生动,卿卿我我,很有新潮的派头。特别是小说中的“凤君啊”、“凤君啊”的几句,后来竟成为同仁们对他开玩笑的笑料。
1921年周瘦鹃接手《礼拜六》编辑工作,在编辑之余开始创作鸳鸯蝴蝶的哀情小说。其动机始于他结婚前的一段恋情。1914年周瘦鹃在一所中学观看学生文娱演出时,他对女主演周吟萍,一见钟情。但此时的周吟萍已经订婚,他只好将这种恋情藏在心底。1922年他创办杂志时,就取名《紫罗兰》,因为周吟萍的英文名字是“Violet”,即紫罗兰,用以纪念这段恋情。基于这种失败恋情的阴影,周瘦鹃创作的鸳鸯蝴蝶小说大多是哀情的,如《此恨绵绵无绝期》、《阿郎安在》等。后来周瘦鹃就成为与包天笑、李涵秋等作家齐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
“老夫子”为她取艺名:郑正秋与宣景琳
上海滩四大名旦之一的宣景琳在我国电影的“第一代导演”中成就最大的是郑正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妇女题材的《玉梨魂》等都是他导演的。
在1920年代初,郑正秋与张石川创办明星影片公司时,决定所拍影片的女主角,要由女性来饰演。招聘女演员的公告贴出后,他们还担心没有人来报名。可是大上海毕竟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大都市,年轻人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不久,就先后有四位年轻女郎被吸纳进电影界。她们就是我国电影史上最初的女明星“四大名旦”:王汉伦、杨耐梅、宣景琳和张织云。
1924年时,宣景琳才18岁,她的父亲是上海的报贩,家庭生活贫困。起初她在教会办的慕尔堂免费读书,却经常受到有钱同学的奚落和歧视。她不甘心忍受这种受歧视的日子,就退学转而学京剧。在她十四五岁时,父母和兄长都先后病倒,家里没有生活来源,只得卖身妓院,以便为家人治病。在明星公司招聘女演员时,宣景琳为了积蓄酬金为自己赎身,改变身份,就报了名。在试镜头时,郑正秋发现她有演戏才能,很适合饰演《最后之良心》中的阔家小姐秦春华,就与张石川商议选中了她。
宣景琳本名叫田金玲,郑正秋发现她很有潜质,能成为令人瞩目的演员,就同她商议,准备给她改一个能叫得响的名字。郑正秋对她说:“你的名字最好改为‘景琳’。‘景’与电影的‘影’古代是通假字;‘林’改为‘琳’,是美玉。你就是电影界的一块美玉。”宣景琳听了很高兴地说:“那就叫‘宣景琳’!我有个宣姐,去法国了,我一直很敬仰她,也很想念她。”就这样,这个初出茅庐的姑娘就成了宣景琳。她在《最后之良心》中的演出非常成功,获得的片酬也很多。后来郑正秋知道了她的身世,便由明星公司出资为她赎了身,成为明星公司的签约演员。
1925年7月,郑正秋编写了一部*生活的剧本《上海一妇人》,请宣景琳主演。目的是让她现身说法,调动她的亲身感受。在表演最初几场戏时,张石川导演还像讲故事那样启发宣景琳,可是演到后半部分,她联想起自己亲身体验过的这种痛苦生活,演起来十分深刻,十分逼真,演出非常成功。
宣景琳成为“电影明星”后,郑正秋编写了一个《早生贵子》的剧本,由洪深来导演。郑正秋建议洪深让宣景琳出演剧中的乡下老太婆。宣景琳心里没有底,不敢接受这个角色。郑正秋得知宣景琳的犹豫,就找到她说:“你很适合这个角色,相信自己,你会成功的!”郑正秋的鼓励,使宣景琳增加了勇气,结果在这部电影中她的演出非常出色,此后,宣景琳就以饰演老旦而闻名于影坛。后来郑正秋发现了胡蝶之后,仍然很关心宣景琳,在他的《姊妹花》中,请宣景琳和胡蝶分别出演姊妹的角色。宣景琳对郑正秋的知遇之恩,始终感铭于怀,她多次对人表示:“我进明星公司以后,郑老夫子不仅教我怎样演好戏,还让我懂得做演员应有的职业道德,以及做人应有的人格。我的成功,应该功劳归于我们的‘老夫子’!”
我国第一个“电影皇后”:郑正秋与胡蝶
被称为民国第一美女的胡蝶 被誉为“电影皇后”的胡蝶最初闯入影坛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艺人,可是在她结识了著名编导郑正秋之后,就成了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
胡蝶本名胡瑞华,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位“电影皇后”。她祖籍广东鹤山,1908年出生在上海。胡蝶从小喜欢戏剧艺术,16岁那年,全家返回上海时,正赶上上海中华电影学校招生,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