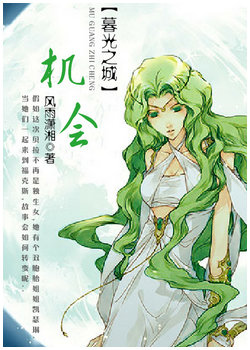回望的目光-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868年,瑞蚨祥的少东家孟雒川开始掌管店务。孟雒川当时只有18岁,人虽然很年轻,但颇有心计,这个年轻的天才商人不仅掌管了本房开设的瑞蚨祥绸布店,而且还兼管了孟家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四房共有的庆祥布店和瑞生祥钱庄,只是他更为〃关心〃瑞蚨祥的发展而已,孟雒川在瑞蚨祥中倾注了他所有的智慧,他在秘密的等待着机会,那个沾满母亲血迹的〃蚨〃像无法逃避的咒语,召唤着这个年轻人去干更大的事情。据说为了推动瑞蚨祥的发展,孟雒川经常利用职权之便,不断从庆祥、瑞生祥抽调资金,强行供给瑞蚨祥使用,于是,当他和孟氏家族的矛盾激化后,他手中的瑞蚨祥早已经羽翼丰满。1876年,25岁的孟雒川经过周密计划,投资8万两白银,成立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开始把生意向全国推进,并将业务扩展到皮货、丝绸、土布、洋布等不同档次几十个品种。1896年,孟雒川将周村泉祥总号和瑞蚨祥总号迁往济南估衣市街,周村瑞蚨祥成为分号。从周村走出去的瑞蚨祥迅速征服了京城的达官显贵,并扣开深宫重门,慈禧太后的寿服、袁世凯的〃中华帝国〃皇袍皆经此而做。清末民初,瑞蚨祥已成为北京名气最大的绸布店。
瑞蚨祥的东家孟雒川像〃蚨〃一样身负着传奇。据说他最喜欢茉莉花,所以他的书房窗外天井里就种着上百棵茉莉,花开时节,成片的白色花朵散发出诱人的清香,一直飘到村外。孟雒川一辈子都没有忘记买地,他最大的嗜好就是买地。每天晚上,这个疯狂的人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出许许多多的地契放在面前看,他把那些地契当成最好的艺术品和人间最好的享受。孟雒川,这位曾经叱诧商海的商业奇才,未曾留下过一张照片,以至于现在我们无缘认识他的真实。但是关于他的传说却一直没有中断,有人说他高大魁梧,有人说他瘦小精悍;有人说他有三个儿子,也有人说他只有两个女儿。这个孟子的后人曾数次到邹城孟子的故居认祖归宗,却都因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之门外。
但瑞蚨祥最终没落了。除了战争的因素外,最大的原因还是家族矛盾。孟雒川一家是一个兄弟子侄众多的大家族,自1924年全家迁天津后,其子侄们渐渐不愿受其管束,终日吃喝玩乐,1939年孟洛川病死后,子侄们更加肆无忌惮,竞相从瑞蚨祥支钱经营私产,严重影响了业务经营,使商号日渐衰落。青蚨最终没有让这个家族世代永享富贵荣华,忘记先人血缘的后辈们,像是没有涂抹母亲血液的〃蚨〃,再也飞不回来。
周村因丝绸而闻名,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与苏杭丝绸并美神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村的文明是依附于丝绸这种商品的生产、流通的,没有丝绸,就没有周村。1939年出版的《现代本国地图》记载:〃周村丝织业之盛,所织绢、绉、绸、绫之属,称山东第一。〃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以〃天上取样人间织〃来形容周村丝绸的精美,但这个十六岁时曾经写出〃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的天才诗人显然在美丽透明的丝绸面前笔力渐拙,只能发出那样无奈惊讶的感叹。
※BOOK。※虹※桥书※吧※
第9节:回望的目光(9)
三、博山古窑部落……午后的寂寞
丝绸之外的中国,尚有一样物品让世界侧目,那就是陶瓷。在外国,中国的名字就叫瓷器(china),许多的商人飘洋过海,纵然带去的只是被旅途打碎的瓷片,西方人也兴奋不已,他们在那些破碎的梦里面巩固着对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猜想。而在中国四大瓷都之一的淄博博山,就散落着许多被废弃的窑炉。
陶瓷的经营让齐国故地的商业文化更加辉煌。丝绸和陶瓷,在数十个世纪中几乎代表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从这些工序繁复、制作精良的艺术品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古老民族智慧而又神秘的想象力。在博山著名的陶瓷琉璃老街西冶街上,耐火砖的建筑铮亮又齐整,两面街铺老旧的门楣,门庭进深的曲幽,无不昭示出山城旧居的古朴雅致。这条老街在整个明、清两代,曾有数条向俄罗斯、满、蒙、高丽、缅甸、印度、南洋运送琉璃料器的商队。
现在,我们确知的是,清至民国,西冶街西圩早已是炉棚比邻、烟筒林立、碎熟药遍地,叮当之声不绝于耳,有大大小小的窑,如料条炉、圆炉、杖子嘴炉、轴子嘴炉、杂货炉、米珠炉等百十多个,形成如〃仁和成〃、〃福祥炉〃、〃新明炉〃多个经营陶瓷的老字号。1935年8月《中国实业》第1卷第八期写道:〃山东博山素为工业区域,玻璃出品尤为著名,大小工厂有三、四百家之多。贫苦劳工赖以生者,约在四、五万人以上。〃
我去博山的时候是一个五月的午后,阳光斜打下来,那些散落的窑炉就把影子拉的修长,倒映在古老狭长的巷子里。我在朋友的带领下在巷子里穿行,去看那些被废弃的博山窑。我时常落单。周围的墙壁或者是粗砾的石块搭建而成,或者就直接用烧窑的废胚砌成,这些墙壁的颜色斑黑或瓦红,线条和纹理之间,让人禁不住想到火焰的样子。而不时出现在脚下已沉睡多年的败瓮与残瓷,令我不得不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细细打量这空荡寂静的巷子,朋友们都走远了,巷子在目光能够企及的地方拐弯,一切都在那里消失。
在朋友的指引下,我们穿过杂草,进入了一口废弃的博山圆窑,里面漆黑一片,借着灯光可以看见窑炉的内壁泛着沙红的光,这口曾经烟火不熄了上百年的窑,火光在它的内部仍然以另外的形式燃烧。我抬起头,想要看清楚这黑暗,却发现窑顶有一束光芒从烟囱直射下来,光在半空中被黑暗湮没,于是只有光柱具体而明亮。烟囱的边缘,不规则的石块垒成圆锥的样子,石块的边缘已经被打磨的没有棱角,看上去,像一群鱼光滑的背部。
如果说陶是没穿新装的女人,是在旷野里仰望星空的女人,它周身散发着火最元初的形式,神秘、自然;瓷则是盛唐养在深闺,或是锁在皇宫的倾城女子,华丽、寂寞。在淄博的〃中国陶瓷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博山窑烧制的精美釉瓷……〃雨点釉〃。
〃雨点釉〃,史书上称作〃油滴〃,因在乌黑的釉面上呈现晶莹的银色斑点而得名。其斑点小如米粒,看上去,就象夜间空中闪闪发光的繁星,曾有〃尺瓶寸盂视为无上之品,茗瓯酒盏叹为不世之珍〃之说。〃雨点釉〃在日本称〃天目釉〃,这种瓷的茶具是日本茶道中的精品。作家刘焕鲁先生的长篇小说《国魅》就写了这种釉瓷的传奇故事,在小说中〃雨点釉〃是失传千年的碎钻瓷,宋代建窑称其谓〃中夜仰观天汉,三更满目星霰〃。当时,日本瓷祖加藤四郎曾在中国学习制造这种瓷质,他带回日本后,才号称〃天目釉〃。自御渥天皇起,为日本皇室所垄断,民间乃至得一瓷片,缀饰在帽子上面,亦堪夸富。
博山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在这里居住着平民世界的千年烧制者。我们敲开一户人家锈迹斑斑的大门,想进去看看,一位正在伺弄猫狗的老人抛下手中的活计,热情的张罗我们喝茶,他的杯子不够用,于是我们便见到许多样式的瓷杯被摆上了桌子,那只黑猫跳上窗台的时候,我看到一方落满灰尘的砚台摆在那里,猫的眼睛闪着一帘幽梦,让整个院子更加静谧。据老人介绍说,这院房子本来是博山一个有名的商人的祖业,后来商人在解放前逃到了烟台,这座院子也就衰败了,我看到门楼的飞檐已经部分坍塌,被雨水冲刷的部分留下黑色的痕迹,照壁上面的灰泥也已经脱落,里面的砖缝里长着衰草。只有正房的砖雕和瓦雕精致依然。那瓦的材质相当精细,雕刻的荷花图案花瓣层层叠叠,含苞待放的尚可看清楚叶片上的纹理。老人把我们领到正房西侧,推开一扇门,我们豁然发现,原来又是一个紧闭的四和院落,如此重叠下去,据说,这个大的院落总共有七个这样的小院落套在一起。遥想当年,这个家族该是多么的庞大和繁华。
◇。◇欢◇迎访◇问◇
第10节:回望的目光(10)
其实,在博山最多的建筑还是和窑与火有关。从材质到建筑风格,无一不让你置身在古窑的部落,随便穿行在某个巷子中,你都可以看见成片的民房是用烧窑之后的废胚加黄泥建筑而成,之前我以为它们多是被烧坏的半成品的陶瓷,后来经解释才知道,那些罐状的物品叫〃笼盆〃。在烧窑的时候,匣钵是烧窑时必不可少的容器,陶坯在经过浇制、水磨、上釉几道工序后,必须要要装进匣钵才能入窑烧制成真正的陶瓷,博山人通常叫成品为〃窑货〃,而匣钵则叫〃笼盆〃。〃笼盆〃使用过一到几次后就不能再用了,因为其材质结实,所以被拿来当建筑的材料。
这些用匣钵建造的屋子有一种不对称的美。墙体上的匣钵一般是环形的圆面,有的中间被时光镂空,露出一个黑色的孔,它们被砌在墙壁里,紧紧挨在一起,远远望去,像伤疤,像树木的年轮。当你行走张望时,会发现石头垒成的墙之间忽然有一段陶缸建筑的墙体,它们被竖着砌成墙,巨大的罐体凸出在平面之外,极其富有立体的空间感。有些院墙下半部分用石头、砖头,而墙头用陶罐做成,有的甚至全部用陶片垒砌,那些陶片没有经过任何修饰,扇面的形状一个接一个不规则的连成一大片;房屋的墙壁有些也全是废陶做成,看着很有沧桑感。烟筒、花盆、甚至村外的简易厕所,也都是陶罐、陶片、陶罐而就。这些烟火味道很浓的房子,大都老屋破败,门锁锈蚀。
在几乎每一个古窑的窑口,随处都可以看到满地瓷片和笼片,更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窑口散乱的排放着数层匣钵,圆环状的匣钵,有黑色的、灰白的、蜡黄的,有的已经破碎,用手摸上去,粗砾坚硬。当你走过这古风古韵的古窑,当你用双手触摸这古朴陈旧的老墙,当你把目光停留在这白墙黛瓦的古窑上的小四合院,你会不自禁要用心与古窑对话,与历史对话。这些匣钵建筑的博山民居,大片大片散落在街巷两边,它们和古窑上空陈旧的电线把天空分割的四分五裂。在巷子的一头,一个鼓状的匣钵躺在草丛中,我上去用拳头重重的敲击,里面发出沉闷的声音,像是古窑千年的叹息。
陶瓷之外的博山还有一样精美的艺术品,那就是琉璃。相传,远在西周时期,奴隶们在炼铜时,发现一种晶莹物体,冷却后脆而坚硬,因其外观光怪陆离,故人们称之〃琉璃〃。明朝万历年间,博山一带已是料炉遍地,盛况空前。到了清代,这里普遍设立专门机构,制作供应宫廷使用的琉璃料器。清朝康熙年间,在北京建造琉璃窑时,曾派人到博山选聘工匠,生产琉璃制品所需要的料条、壶坯,也都由博山供应。
博山的琉璃和一个人血脉相连,那就是孙廷铨。孙廷铨,字枚先,号沚亭、灌长氏,博山大街人,明崇祯庚辰进士,清顺治兵部、户部、吏部三部尚书,康熙内秘书院大学士。据记载他是乾隆皇帝的帝师,入参机务多年,曾经在天津卫办过漕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