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上卷)-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乎无望”这四个字,令张之洞心头一颤。
“卫大人,您说说山西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山西的弊病第一在穷困。”卫荣光慢慢地说,“历史上,山西原本是富强之地。战国七雄,有三个国家是从晋国分出去的。直到隋末,太原仍是全国重镇,故有李渊父子起兵反隋,造就了大唐王国。唐朝诗文繁荣,山西文人独领风骚,便是明证。到宋代之后,国家重心南移,明代以后都城定在北京,三晋便逐渐冷落下来。除开外部原因之外,山西的被冷落是因为自己的贫困,而贫困首先又是因为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缘故。百姓贫苦,各级衙门税收则少,税收一少,则捐摊就多。这捐摊便成了山西的第二个问题。”
阳曲县那个老太婆所诉的就是捐摊苦水,桑治平从晋北回来,也说老百姓最恨的就是官府的捐摊。张之洞皱着双眉说:“第一是贫困,第二是捐摊。贫困多半是老天爷造成的,这捐摊则完全是官府所定。我们为何不可以免去捐摊,以苏黎民?”
“贤弟啊,你有所不知。有的捐摊可免,有的捐摊则是难以免去的呀!”卫荣光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张之洞忙从火炉上提起瓦壶,亲手给卫荣光斟满。卫荣光喝了一口,接着说下去。
“山西有几个大的捐摊,就没有办法免去,因为这是朝廷造成的。比如说,朝廷每年要山西解平铁八万余斤、好铁二十万斤,这二十八万斤铁,包括脚费在内,朝廷只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短缺费用三万九千余两。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是乾隆初期定的价,到现在已百年出头了。百年里,哪样东西不是几倍的涨价,可朝廷给山西的铁银却一文未增。山西是穷省,藩库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不摊到各州县又怎么办呢?”
张之洞在心里沉吟着: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大事。每年三万九千两银子,对于山西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年来都是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了,让老百姓来承受这笔沉重的负担。户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呢?
体质仍然虚弱的卫荣光觉得身上有点冷,他将椅子向炉边靠拢。张之洞猛然想起,随身带来的简单行囊中有吴秋衣所送的四株灵芝,便从行囊里拿出来送给卫荣光。
卫荣光仔细欣赏这四株碗口大闪着黑红色光泽的灵芝,知道的确不是凡品。张之洞执意要把四株都送给他,他再三推托不成,最后只得接受两株。
“卫大人,您刚才说的铁捐,确实是一项大的捐摊。听说还有一项绢捐,也是民愤极大的。”有这两株灵芝草的效用,张之洞和卫荣光之间的谈话气氛变得更为融洽。
“是的。嘉庆时期开始,朝廷便每年向山西索贡绸绢一千二百匹。近十多年来,因为百姓生活苦,绸绢卖不起价,织造绸绢的作坊基本上都改了行,山西交不出这多绸绢,户部则规定少交一匹绢,用十两银子来抵,于是每年又多出这项费用。这一万多两银子,也只得向各州县摊去,这便是绢摊。”
卫荣光的精神比刚进门时强多了,他喝了一口茶后又说了起来:“还有一笔大费用,即每隔三年一次的文武乡试,乡试照例由阳曲县承办。办一届乡试至少要三万两银子,阳曲县如何负担得起,只得由巡抚衙门出面,向全省各州县摊派,平均每年要一万两以上。这是几项大的无法豁免的捐摊,还有其他形形色色、各州县自定的捐摊,加起来有二三十项之多,这些银钱往往都加在百姓头上,百姓怎能负担不重?又怎会不怨声载道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投石问路(5)
“地里收成这样差,老百姓的银钱从哪里来呢?”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发问。
“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不种庄稼而种罂粟。废掉粮食而种毒卉,他们不是不知道如此不好,但种罂粟获利是种庄稼的十倍,这叫做逼良为娼。”卫荣光气愤地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狠狠地一放。
张之洞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事理。那一天,踏进娘子关后所见到的罂粟苗,曾引起他极大的愤恨。他恨山西的农人,怎么如此昧良心,不道德;他恨山西的州县官吏,怎能如此公然容许小民犯禁违法!原来,“嗜利忘义”的背后有它一言难尽的苦衷!
接印还没有几天,他就准备下一道命令给各州县:限令三天内全部铲除罂粟苗。桑治平建议他暂缓下令,待把全省的情况摸清楚后再说。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看来,要铲除罂粟,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办得到的事,若官府的捐摊不大加削减的话,强行铲除罂粟也并非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张之洞非常感激卫荣光的剖析:“卫大人,看来这废庄稼而种毒卉,就是山西的第三大弊病了。”
“可以这样说。”卫荣光点点头,继续他的话题,“此弊病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一是种罂粟虽可赚较大的利益,但毕竟不能果腹充饥,平常年景可以用银钱去买粮食,到了饥荒年,都没有了粮食,拿着钱也是空的,这就是前两年山西干旱而饿殍遍野的原因。二是山西大量种罂粟,造成土药价大大低于洋药价,遂使得吸食鸦片在山西泛滥成灾。”
“我到太原这些日子以来,所接触的人大都脸色青黑,身体干瘦,可能都是吸多了鸦片烟的缘故。”
“香涛老弟啊,你还不知道,山西吸鸦片已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我的一个幕友这样估计过:乡间十人约有四人吸,城市十人约有七人吸,至于吏、役、兵三种人,几乎十人有十人吸。这个估计虽然有点夸大,但大致也差不多。鸦片烟一定要根除,不然的话,整个山西,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场到民间,很快都会烂掉。老弟,这个事要靠你来办了。”
瞬时间,张之洞真有点颓然气沮之感:早知道山西是这样一个污浊之地,真不该来,在京师做个侍郎,不仅事情少多了,而且还可以免去与这多鸦片鬼打交道,眼不见心不烦呀!但很快,他便从沮丧中挣脱出来。他是个禀赋刚烈、好强好胜的人,转念又想:当我张之洞把山西这个烂摊子整顿好后,太后、皇上、京师的友朋、天下官员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本事了。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卫大人,您放心南下,我非要把鸦片在山西彻底根除不可!”
“好。到底是年轻有为,我已近老朽,这种话就说不出来。”
“卫大人,据说山西的藩库有三十年没有清查了。许多人都说那是一笔糊涂账。我想在我手里办一下这件事,您给我指教指教吧!”
听了张之洞这句话,卫荣光晦涩的目光一下子明亮起来。他不是一个糊涂人,当了十个月的晋抚,已看出山西一切弊病中的最大弊病,就出在这个财政混乱上。一个省的藩库居然三十年不清,岂非咄咄怪事!账目糊涂,岂不人为地造成给管理账目人以贪污挪用的机会?刚上任时,卫荣光也想有所作为,也曾动过清理藩库的念头。但此念一出,便招致不少人的劝阻,第一个出来劝阻的人便是藩司葆庚。卫荣光心里明白,葆庚做了多年藩司,亲管藩库。一旦清理起来,第一个便要碰着他,也会牵连到许多现任的官吏。说不定,还会牵涉到曾国荃的身上。那个功勋盖世而又刚愎自用的曾老九,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以明哲保身为最高原则的卫荣光只在想过几天后,便脑子冷静下来,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卫荣光自身不是一个贪墨的人,眼见得一批国库蠹虫不得惩罚,他心里也不甘,只要不伤害自己,他还是希望这些蠹虫被抓出来。无论从律法道义上来说,还是从个人心志上来说,清除侵吞公款的贪官污吏,他总觉得快慰。那么,就鼓励眼前这位素以名节自律,不怕担风险,敢于任事的后任者来干吧!
“老弟,清理藩库这件事,你是不是真的做?”卫荣光两眼盯着张之洞。
“我真的要做!”张之洞的口气坚决,没有丝毫的犹豫。
卫荣光颇为满意地点点头:“若真的要做,就要一做到底。我比你痴长十多岁,在地方上混的时间也比你久,阅历教给我一个书上没有的知识。”
卫荣光说到这儿稍停了一下。张之洞趁机又把椅子向前移了一步,他知道这种阅历得到的知识远比书斋里读来的学问要可贵得多,一个字都不能漏掉!
“对于一个从政的官员来说,面对一件大事,在动手做之前,先要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到。能做的话,则一做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能做的话,则干脆不做。半途而废,比起不做来,后果要更严重得多!”
这的确是经验之言。张之洞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但冷眼旁观政坛,他也见过有人就栽倒在这点上。今夜,由这个浮沉官场三十年的老前辈口中说出,其分量自然更重。
张之洞十分诚恳地说:“卫大人,您这话真正是金玉良言,我将终生铭记于心。”
“山西藩库的账目,三十年未清,我刚来太原时也很觉奇怪,也有过清一清的想法,但后来终于未动手,就是鉴于刚才讲的这个原因。不怕老弟见笑,我身体不强健,耐不了繁剧,年岁大了,胆气也越来越薄弱,深恐引起更大的麻烦,故敷敷衍衍地这样过来了。老弟愿意来做这件事,我是非常赞同的,只是我再次提醒你,此事一旦动手,就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下去,今后会有很多预料不到的啰嗦事出来,你都先要有个准备。”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投石问路(6)
“卫大人,您放心。”张之洞离开椅子站起来,挺直在卫荣光的面前。“我张之洞才干或许不大,但从来胆量大,骨头硬,不怕妖风鬼火。为朝廷办事,为百姓办事,哪怕革职丢官也不在乎,即便把命垫在这里,我也在所不惜。”
这番话,使得禀赋懦弱的卫荣光大为激动,过去他多次读过张之洞那些风骨凛凛的奏疏,总想那不过是些豪言壮语而已,离实实在在的行动还差得远哩!现在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真名士,一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国家干臣。他不由得从心里生发出敬佩之情来,也跟着站起,拍着张之洞的肩膀说:“贤弟,你有这样的准备,那就什么都不用害怕了。站在你的面前,我自觉惭愧,我没有为山西做点有益的事,我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夜我愿意为贤弟竭诚帮一点忙。”
张之洞忙握着卫荣光的手说:“卫大人,请坐下,坐下说。”
两人一同坐下后,卫荣光颇为动情地说:“贤弟被擢升为晋抚,真正是太后、皇上的英明。自古说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贤弟欲干此大事业,没有人帮衬是不行的。山西官场尽管庸员多,能员少,但以我的十个月经历,也发现几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以至诚公心给你推荐几个,算是我这个前任对你所作的惟一帮助。”
张之洞听了这句话,心里太高兴了。山西弊病如此多,固然是他忧愁的事,而更忧愁的是初来乍到,他对山西官吏的贤庸智愚不清楚,县令以下的人几乎还没有见过面,且不去说,就是见过面的府道两司,也还谈不上有个什么评价。有的人面善心却不一定善,有的人能言并不一定能干,有的人又恰好相反。从来识人辨人是最棘手的事,也是最高深的学问。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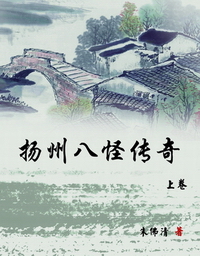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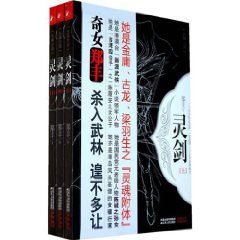

![醉玲珑[上卷]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6/1625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