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上卷)-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关于伊犁事件的处置,慈禧通过对张之洞的垂询,已在心里大致打定主意了。她听到不少人都称赞张之洞熟读经史,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学问渊懿,五月中旬甘肃地震,六月以来金星昼见,都说这是天象示异,读书不多的慈禧太后弄不清楚其间的深奥道理。何不叫张之洞来说说呢,他的学问究竟如何,也可借此测试一下呀!
“张之洞,近来地震在西北出现,金星白天可以见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慈禧突然间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张之洞所没有估计到的。张之洞通晓典籍,对经史书上所记载的诸如山崩地震、星象反常的现象,也曾给予极大的注意。他是一个严谨的儒家信徒,对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做法深为服膺。他不大相信那些谶纬家、占卜者神秘玄虚的推断,认为那多为附会之说。但经书史书为什么又都将它们记载呢?经过长期的钻研,结合十多年来的从政阅历,他确信那是先贤的一种神道说教,即借天象来劝诫君王迁恶从善,宽政恤民。他很钦佩先贤的这种智慧,现在是轮到自己来向君王履行这个神圣的职责了。
张之洞凛然奏道:“甘肃地震,金星昼现,此种地理天象在康熙十年也曾同时出现过,圣祖爷当即下诏修省,令臣工指陈阙失。上苍示儆,修身省己,此正圣祖爷仁心之所在。今两宫太后、皇上敬天爱民,忧勤图治,为天下臣民所共知,然天象地理如此,亦不能不慎之。臣以为宜效法圣祖爷,从以下数事来修省弭灾。”
张之洞略停片刻,定一定神,平素常常思考的大事,一件件迅速地浮出脑海:“一曰采纳直言。修德之实在修政,而修政必自纳言始。《 洪范·五行传 》谓居圣位者宜宽大包容,古语说君明则臣直,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故采纳直言乃修政之始。二曰整肃臣职。地震乃地道不修,地道者,臣工之道也。《 春秋 》于地震必书,意在责臣下不尽职。以臣看来,比年来臣职不修的事例极多,跪安之后,臣当向太后一一奏明。”
“你要照实禀报。”慈禧打断张之洞的话。
“是,臣一定如实禀报。”张之洞继续奏下去,“一曰厚恤民生。《 周易·大象 》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程子注曰:山而附着于地,圮剥之象,居人上者观剥之象,则安养民人以厚其本,所以安其居也。西北地震,正是上天启示下界有不安之民,故请厚恤民生。一曰谨视河防。史传所载,金星为变,抑或主水,故请朝廷加意提防黄河、淮河及京畿永定河等多灾河道,加固险工,防患于未然。臣以为地震及金星昼见虽不是好事,若见上苍之示儆,而修身省达,自可以消灾弭祸,国泰民安。”
慈禧见张之洞引经据典如顺手牵羊,不觉暗自佩服,心里想着:如此饱学而不迂腐的人才却屈居于司经局洗马,真是可惜了,应该破格提拔。转念又一想,张之洞是清流党的重要成员,朝廷口碑不一,宜慎重对待。她想听听张之洞本人对清流党的看法,遂问:“张之洞,都说京师有个清流党,专门弹劾中外大员,你以为如何?”
张之洞没有料到慈禧会提出这般尖锐的问题,他一时不知从何答起。他本能地意识到,太后对“清流党”三个字是不喜欢的,从来帝王都不喜欢臣工拉帮结派,即使是文人雅士的###结社,一旦被目为结党的话,也会为之不安。张之洞想到这里,头上冒出丝丝热汗,并一直热到颈根。他凝神片刻,调整下心绪,然后坦然奏道:“启奏太后,臣以为清流党一说不合事实。臣自从光绪二年从四川回京后,与李鸿藻、潘祖荫、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交往颇多。一则臣仰慕他们持身谨严的人品和忠于太后皇上关心国事的血性,二则臣与他们有喜爱学问诗文、金石考辨等癖好。尽管从来便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但臣仍凛于‘结党营私’之儆戒,不敢与人结社组盟,以贻口实。据臣所知,李鸿藻等人与臣此心相同。且臣以为专门弹劾大员一说亦不全合事实。就拿臣来说吧,这几年除代黄体芳起草过弹劾户部尚书董恂外,其余不论是为人代拟,还是自己署名的三十多道折子,全是言事陈策,并不以纠弹大员为主。比如这次伊犁事件,臣主张严惩崇厚,但亦非专门冲着崇厚而言。臣为此事草拟了七八道折子,还有几道未及上奏,所有这些奏章,都重在如何妥善处理伊犁归还一事,而不重在如何惩处崇厚一人。臣幼读先儒之书,粗明大义,既不敢结党以营私,又不愿以劾人而利己,侧身于翰詹之际,留心国事,乃臣之本分。臣一向认为,当以剖析事理寻求善策为重,而不应以严峻惩罚罢官削职为目的。”
慈禧默默地听着张之洞这番长篇陈述,心想:被人目为“清流党”的头面人物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张之洞确乎遭人攻诘不多,这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这个“清流党”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张佩纶、陈宝琛今天弹这个,明天纠那个,日后将积怨甚多,恐于己不利。隔着薄薄的黄丝幔帐,慈禧盯着张之洞良久,似乎看到这个司经局洗马的另一面。是明哲,抑或是乖巧?是练达,抑或是圆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清流砥柱(21)
出于对清流党本能的不喜欢,再加上那张不能令人悦目的长脸和上下不协调的短小身材,另一种想法渐渐地在慈禧的脑子里占了上风:他是一个诚恪务实、老成持重的干才吗?是一个能当大任、震慑群僚的社稷之臣吗?还得再看一看,等一等!暂缓破格,循例晋级吧。慈禧作出这个决定后,对着幔帐外跪着的张之洞挥挥手:“你跪安吧!”
走出养心殿,一阵凉风吹来,张之洞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此时,他才发现,贴身的内衣早已湿透了。
六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
回到家里,张之洞关起书房门,独自默默地坐了大半天。就像孩童时代回味好看的戏一样,养心殿召见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脑子里慢慢地重新出现一遍,尤其是将太后的每一句垂询和自己的每一句对话,再细细地咀嚼着,仔细体会太后每句问话的意思和有可能蕴含的其他内涵,以及自己的应对是否得体,是否达意。他揣摸着慈禧太后对伊犁事件的心态:恼怒崇厚所签署的这个条约,使她和大清朝廷在洋人面前失了脸面。倘若有足够的力量的话,这个强硬的中年妇人决不会谈判,她会下令左宗棠带兵赶走伊犁城里的俄国人,将这座本是自己的城池强行收回来。只是现在国力衰弱,她有所顾虑。张之洞相信自己废约杀崇厚、积极备战迎敌的主张,与慈禧的心思是吻合的。在整个召对的半个时辰里,自己的各种表现也没有失仪之处。
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兴奋起来。他将已经草拟的几份奏稿再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着,力求考虑得更周到,更全面,更细致,更易于被采纳。司经局洗马不仅要为太后和朝廷在处理伊犁事件中提供一份完整的方略,同时,也要为国史馆保留一份完备的文书,以供后人阅览,日后遇到棘手的国事,张某人所上的这一系列奏章便是一个极好的借鉴。
他还想到,久困下僚、屈抑不伸的年月就要从此过去了。通籍快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从五品的小京官,张之洞为此不知多少次地苦恼过、困惑过、愤怒过。论出身,论才学,论政绩,论操守,哪样都比别人强,偏偏就升不上去。是缺少溜须拍马的钻营功夫呢,还是时运未到?想起父、祖两辈都官不过守令的家世,他有时会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难道是张家的祖坟没葬好,压根儿就发不出大官来?
看来,时至运转,这一切都要改变了!
然而,现实并没有这个富于幻想的从五品小京官所设想的那么美妙。
首先,是恭亲王奕䜣和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多次向慈禧郑重指出,作为与俄国谈判的特使,崇厚是不能杀的,杀崇厚无异于侮辱俄国。俄国是侵略成性的军事强国,与之开战,中国必定损失更大。用武力收复伊犁之议,貌似爱国,实乃误国。这是不负责任的轻举妄动。自古以来清议皆误国,今日张之洞、张佩纶等人正是这样的人。
接着,各方推举认同的崇厚替代者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从伦敦上疏,说筹办伊犁一案不外三种方式:战、守、和。曾纪泽详细分析敌我双方形势:伊犁地势险要,俄人坚甲利兵,战未必能操胜券;且伊犁乃中国领土,开战后俄人无损,受害者实为中国,何况俄人对中国觊觎已久,此次不过借伊犁以启衅端,开战正合其意。中国大难初平,疮痍未复,不宜再启战事。故战不可取。言守者,谓伊犁乃边隅之地,不如弃之,以专守内地。持此论者不知伊犁乃新疆一大炮台,若弃伊犁则弃新疆;新疆一弃,西部失去屏障,故守亦不可取。当此之时,只可与俄国言和,修改条约,能允者允之,不允者坚决不允,领土及边界事决不迁就,其余不妨略作通融。至于崇厚,可以严惩,但以不杀为好。
曾纪泽这个处理伊犁一案的方略,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护,慈禧本人也同意。既然按照曾纪泽的稳健方案来办事,过于强硬的张之洞便不宜破格提拔。慈禧又为循例晋级找到一层理由。于是,张之洞便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官职则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仅升一级,张之洞虽然感到失望,但毕竟官位提升了,也是好事。尤其令他欣慰的是,朝廷没有接受崇厚所签署的丧权卖国条约,将崇厚拘捕,定为斩监候,并改派曾纪泽为全权特使与俄国继续谈判。张之洞认为朝廷还是接受了他处理此案的大计方针,这足以值得快慰。相对于国家主权来说,没有破格超擢,毕竟还是小事。他仍然以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凡关于此案的一些新想法,他总是不断地缮折递上去,供太后参考,以尽自己对国家应尽的职责。
这一天,他在书房阅读邸抄,得知曾纪泽已抵达俄国,正在与驻俄国的英国大使德佛楞及法国大使商西接触,探询英、法两国对伊犁一案的看法。张之洞对曾纪泽办事的稳重很满意。这时,王夫人进来说:“尊经书院的学子杨锐来看你了。”
“杨锐来了?”张之洞放下手中的邸报,惊喜地说,“快叫他进来!”
“学生已经进来了。”
说话间从王夫人身后走出一个二十岁出头、五官清秀的青年,他就是杨锐。“香师,三年多没有见到您了,这几年来都好吗?”
“好,好!”张之洞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身边的椅子说,“坐,坐下说话。”
第一章 清流砥柱(22)
杨锐在张之洞的对面坐下来,张之洞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笑着说:“三年不见,你长大许多了,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了。”
说得杨锐不好意思起来,咧开嘴笑着。王夫人亲自端一碟盖碗茶上来,对杨锐说:“这还是那年在成都,你陪着老师在黄瓦街买的青花茶杯,用了几年,还跟新的一样。”
师母这般亲热,这般慈祥,使杨锐备感温暖。他起身接过茶碗,如同小孩在长辈面前表功似的说:“黄瓦街是满城。我那年对香师说,满城里卖的瓷器是宫廷用瓷的余货,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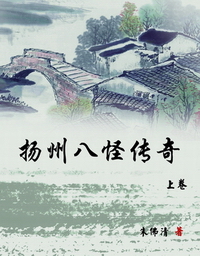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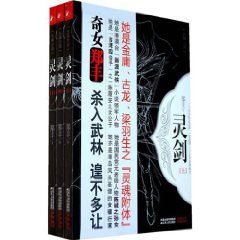

![醉玲珑[上卷]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6/1625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