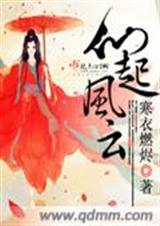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界就“董浩云与包 玉刚,谁是真正的世界船王”闹得沸沸扬扬。 有关详情,本书将在第三十章涉及。
… 页面 11…
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 香港的五大船王,有两位鲜为内地人所知,他们是华光航运的赵从衍、 万邦航运的曹文锦。赵氏曹氏均是上海人,他们在香港从事航运业的目的, 都是看好“会流动的资金”——船。他们的势头压过老船王许爱周,并且 先于包玉刚下海。他们两家的船合起来,相信不比航运较发达的大国少。 他们为何不同航? 上海的淡出与香港的进取 香港第22任总督葛量洪 (1917年至1958年)在回忆录中说:香港“复苏较快的因 素是由于中国回流香港的大量劳工”,“香港经济的重建主要是得力于上海人带来的 资本和工业技术”。 香港沦于日治较上海晚几年。30年代后期,上海有一大批工厂迁往香港。抗战胜 利后,有少量工厂迁回上海,但马上内地内战烽烟四起,大部分工厂就暂时留在香港。 解放战争中,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愈来意多的移民和资金流入香港。高岭期以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为起点,在9个月里。有75万人从水陆两路涌入香港,1950 年,香港人口激增到250万。之后,仍有移民越境入港。 移民中,以上海人文化素质和商业素质最高,他们多是银行家、工商资本家、公 司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随老板而来的),另有少量的官僚譬吏及文 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据 《广州百年大事记》,1949年8月11日流入港澳的黄金估计达2 万两,一周内已达五六万两之多。这之中,流入香港的黄金肯定较澳门多。这一时期 为广州解放前夕 (10月),流入的黄金以广州人的居多。上海解放为该年5月,上海资 金流入香港的高峰期为2至7月。上海为远东最大工商业城市,流失的资金肯定比广州 多。资金形式有黄金、白银、珠宝、外币等。流入形式为自带,极少通过银行,因此 无法估量。 另外,原来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商行,均卷资入港发展。 百余年来,香港虽名为世界自由贸易港,但上海在这方面的功能并不亚于香港。 上海扼守长江流域,处中国东部中心,又以辽阔的中原为腹地,城市规模、经济发达 程度,以及在国际金融贸易的地位,均胜于香港。由于政治与战争局势的变化,这似 乎成了一条规律:沪盛港衰,港起沪落。 1949年后,上海的半殖民化的自由经济渐纳入计划经济轨道。一方面帝国主义对 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中国奉行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的国策。这样,上海“准 世界自由贸易港”的功能日渐消失。上海的对外贸易,基本限于社会主义阵营或友好 国家间的易货贸易,以及援助亚非拉。 战后经济复苏的东京,有可能成为“准世界自由贸易港”,但日本的贸易壁垒和 高税制,使各国商人望而却步。这样,香港就是远东唯一的世界自由贸易港。香港基 本成了中国内地转口贸易的唯一通道。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功能辐射全世界,它在许多 方面远远走在上海前面。 在香港的五大船王中,相信还有两位船王,内地人一定相当陌生:华 光航运的赵从衍、万邦航运的曹文锦。不过,赵氏、曹氏两大航运世家, 在香港却是相当有名。 赵氏、曹氏都是来自上海航运界的家族。两家高沪来港的时间前后不 超出半年。他们来港重执航运业的目的一样:都是看好“会流动的资金”
… 页面 12…
——船。 避风落根 1948年隆冬,刺骨的寒风在黄浦江掀起浑浊的浪花。国星号的汽笛如 位声在外滩的洋行大厦间回荡,国星号缓缓偏离码头,将驶往南中国海的 香港。 这大概是国星轮第一次装载这么多乘客,它纯粹是一艘散装货轮。不 过眼下这情景,已见怪不怪,离沪的“难民”如潮水四溢。国星轮上,就 有该轮的老板——赵从衍及他的四位公船上的上海人问赵老板还回不回上 海。赵从衍道:“我是去避避风头的,当然还要回来。” 熟悉上海航运界的人们,谁不知道赵从衍的大名。赵从衍跟人们通常 所见的船东不同,他们多是从风口浪尖中摔打起家的,而赵从衍是律师出 身,纯粹一介书生。 赵从衍是江苏无锡人氏,父亲是官僚,家境富裕。赵从衍就读于上海 东吴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与同学倪亚震结为伉俪。赵从衍毕业后,在 上海做律师。 1940年,日伪政府对律师重新注册登记,赵从衍为示“抗议”,放弃律 师业,投入商界。最初与一位英商从事进口香烟业务。日军偷袭珍珠港, 英美与日本成为敌国。英商离沪流亡,香烟进口业务嘎然而断。 赵从衍与友侪开办船务行。他们没有船,仅是代理——为货主联系船 只,又为船主招揽货源,从中赚取佣金。这便是赵从衍的航运启蒙学校。 上海收复,中原大地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物资极为匾乏。 日伪期间,上海留下大批物资,远东各处,亦有战争剩余物资运来上 海。 赵从衍见这是一宗好买卖,便倾其多年积蓄,购买一艘二手洋轮,取 名国星号。赵从衍既是船主,又是货主,一石二鸟,财源广进,到1947年, 已跻身千万富豪。 当年百万富翁已是非常了不起,赵从衍30出头就有千万身家,在富翁 云集的上海滩亦不多见,以市值论,相当今天的数亿。赵从衍马上大举进 军房地产,购下的物业竟有数条街之多。好像赵氏是开国家银行的——他 那艘国星轮就是“银行”。 1948年冬,解放军气吞山河,锐不可挡。赵从衍安排太太带幼女乘飞 机去香港,然后带四个儿子乘自己的船去香港。 赵从衍选择了中立的香港为避风港。 赵从衍的儿子赵世光回忆当年的情景: “当时父亲告诉我们要到香港度假去,谁知一去便是几十年,而且是 在香港落地生根。当年,我们乘搭的那艘轮船体积庞大,大约有3千到4千 吨,俨如巨无霸一样,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 曹文锦约比赵从衍小10岁,曹氏家族是真正的航运世家。曹文锦祖父 曹华章开设一间曹宝记船业公司,从事长江流域的内河运输业。但曹文锦 父亲曹隐云没有继承父业,主要是太古、怡和的洋船队势力太大,民族航 运业步履维艰。曹隐云在父亲的资助下开办银号,后发展成中国劝业银行。 曹文锦1925年生于上海浦东老家,从小在教会学校求学,中学毕业后,
… 页面 13…
进入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读书。此时,父亲是 上海有名的银行家,母亲吴娱萱开设天宝成珠宝金饰行,是上海滩自力谋 生的阔太。 在曹文锦读至大二时,父母就迫不及待讨论儿子该继承谁的事业。大 学甫毕业,21岁的曹文锦便按照家族列具的“训练项目”投入紧张的训练。 他白天去祖父的进出口行实习,晚上便随父亲学习金融课目,曹文锦回忆 道:“祖父、父母望子成龙,我都要累得趴下来。” 曹文锦唯独没有学习航运业。那时执航运业的人士,多是走船出身的 “粗人”,家族不屑让名校毕业的文锦学走船揽货。同时,家族的航运业规 模日微,不可与其他事业同日而语。 如果一切都未发生变化,曹文锦将会顺利地继承庞大的家业。不过, 没有受过大起大落磨难的曹氏,是否能将家族事业光大而成为一名出色的 企业家,尚需打个问号。 人算不如天算,曹家苦心孤诣让曹文锦继承家业,可家业将来是否姓 曹都成问题。 1949年新年伊始,偌大的淮海平原落入解放军之手,杜聿明、黄百韬、 黄维兵团全军覆灭。上海的有钱人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屋丢舍,逃港逃台。 香港《资本家》杂志(1992年8期)称:“1949年,中共兵临上海前夕, 曹家仓皇出走,只带了10万美元南下香港,大致只有当时曹家财产的5%至 10%。当时曹文锦还不到24岁。” 另有不少香港报章杂志认为,曹家带出的资金,只有家产的1%。无论 哪种说法更准确,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曹家是上海的巨富;二、曹家出 走损失不菲。 当时曹家还不认为就蒙受了什么损失,他们只是避避战 乱。以前也曾有过北伐、日侵等战事,曹氏家产仍姓曹,仅破损了一 些坛坛罐罐而已。 曹文锦回忆道: “当初,我们只想着来港避风,为了使属下职员安心,我们(在上海) 的公司如常营业,房地产、珠主以及股票都没有出售或带走,只随身带了10 万美元现金和一些珠宝,希望局势稳定后再回上海。” 靠水生水 无独有偶,赵家来香港的初衷与曹家相同,数十年后,赵从衍回忆南 逃的情形: “当时形势十分混乱,我最初只把香港当作庇护所,逗留半年便会返 回内地,但内战结束后,反观香港却有作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 赵从衍带出的唯一家当是国星轮。国星轮3500吨级,是当时比较大的 海轮。赵从衍便把国星轮当主,作为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财源。 逃港的上海人,都说赵从衍是个聪明人,带来一笔“会走动的资产”, 来到香港便衣食无优。 和所有来港的上海人一样,赵从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为了揽货, 赵从衍把运费压低,却又遭到同业的谴责。赵从衍见逃港的上海人愈来愈 多,估计一时难回上海,便在港庄册一间华光船务公司,雇用一名粤籍的
… 页面 14…
香港人帮他揽货。 真正使华光船务突飞猛进的,是朝鲜战争爆发、海上禁运。由于战争, 各方急需各种物资,而禁运,把运费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至内地及 朝鲜的每吨货物运价竟达150美元!在90年代的今天,同等航程每吨货物运 价只有10—20美元(视货物类别而异)。当年的150美元,相当于今日的1500 美元,两者运价悬殊100倍! “有船就是印钞机”——当年为朝鲜战争运载货物的船主、货主均这 么说。 然而,利润大,意味着风险大。港府执行联合国决议,对内地及北朝 鲜实行禁运,要闯过香港海关这一关,已是不易。过台湾侮峡,国民党军 队为防解放军攻打台湾,在海峡布水雷。愈接近辽东半岛和朝鲜,危险愈 大,若遇到美国巡洋舰,不是被扣留,就是被击沉。 船毁人亡、为之破产的船东大有人在。 国星轮跑过短暂的险程,盘满钵满的赵从衍便适可而止,开辟至日本 横滨的航线。朝鲜战争使日本经济绝处逢生,由于地理的原因,日本成为 美军的后方基地,日本产业界获得大量的战时特需订单。日本工业化路子 与香港一样,都必须依赖海外的原料市场。远东大闹船荒,国星轮不愁货 源,运费虽比跑“险程”低,盈利仍十分丰厚。 赵从衍把盈利投入购买二手船,渐渐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到50年代 未,华光船务到日本订造新船,遂步把老船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