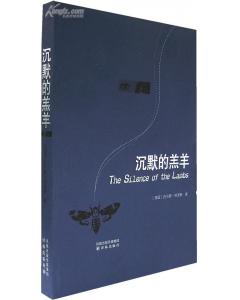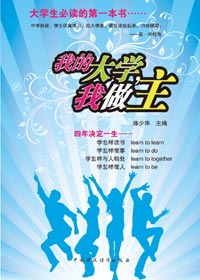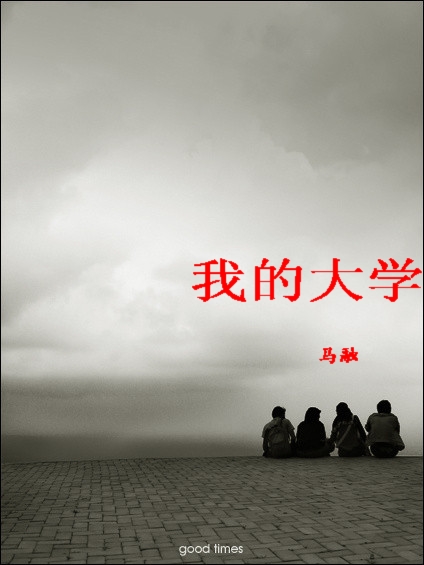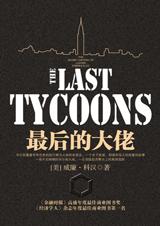��Ĭ�Ĵ����-��2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IJŶԡ���һֱ������ͬ����ð��ȥ�ؾ���Щ�ˡ���ֻ��ϧ����άŵ���ˡ��������������߷����۸��ֵ͵�ë����������Ҳ�е�ô����������������ְġ�һ���˵�ս������������
����*��*��*������
������ƪ���������1996��2��28�ա��л����鱨����������������������
�����Ż���������
��75�ڣ���������Բ���������������������
������������Բ���������
����������ʱ�����ӣ���Щ����������Щ�����ֹ�����������ӻ����������е��˶��ڳ��裬��һ����ʥ���ڡ����е��˶��ڳ���������ҹ����ʥ��ҹ�����е�Ƶ�����������֣����ż������е�Ƶ��������ͨͨ��һ���ˣ�Χ��¯�߳������е�Ƶ���������������ٱ��ˣ���һ����������һȺ��ʫ���ͯ��һ���������и�����һ�쳪�ĸ趼��������ꡭ����һ����ӾͿ������е��ڽ̸��������ᡣ��һ����Ү�ջ����ĵ����ա��������Ǹ������̹��ң����������ûʲô��˵�ģ����������������Լ���˵�����궼����һ�ף����Ƿ����ˡ�������ϲ�����ڽ̿�Щ��Ц��������Ϊ���Dz��ϣ���Ҫ����Ϊ������һ�ף����Ǿ����е㷳��������һ�������һ�Ρ����������������������е����Ӵ��ӣ�����Ļ���ǹ�����Щ�����Ĺ��ִӷ�����������������ڽ������ţ��·��������綼���̵ġ�����Ȼ����һ������ʥ�ڡ�����һ���ϰ�����ͷ����ˣ�����������д�ų������̨�������Ǿ��Dz��ϸġ�����ʱ��Ļ��һƬ�ʺ죬�и���Ŀ�����ļһ���ִ�������е�Ƶ���Ͽ��ˣ�ֱ������ͷ������Ѫ���ɺӡ���ʱ����ôҲ�벻����һ����ͷ�ڡ������������˲�֪������һ����ʮ���������壬Ҳ���Ǻ�ɫ�����塣���ڿ���ͷ�ĵ���Ƭ�����������˺�Ҫ����������̨ƫҪ�š����ǵ����ӱ�������ס�ˡ���Ҷ�֪������Щ��������������շ����ģ�������һ�־ͽ�������ɫ�����塨����һ�����Dz��ң������ֲ���������Ҳ�ֲ������������Լ�Ҳ����ô˵�ģ������ر�����ӣ������뿴�������ĵ��ӽ�Ŀ��������
�����Դ��һ����й������������Dz��֡���ɫ�����塨�ˡ���������һ��һ��ģ����в����ĵ������е����й�����̨�ıർ������Ҳ�б���������Щ�������е�Ƶ���������ձ����ӡ�����Ȼ����Щ���Ӻͺ���������վ��������ˣ����ⲻ�ֳܵ��ҿ�������ʱ���еķ����и��������ڵ�����Ļ��˵��̫�������������Ҵ��������ˡ������˶������������ʲô�ˣ�����ʮ���꿪ʼ����һֱ˵�������ڣ�����Щ�������е�Ƶ���������Ը߸裬���ҳ��ö���û��ûζ�ġ����������Ȼ�йأ���Щ�����ǽ�ʦ�ڣ���Щ���������˽ڡ���ͯ�ڡ����ڵĽ������࣬���������ݱ���һ�����ա�����Ѽ��������ϣ�����ÿ�춼�е�˵ͷ���и�˵ͷ����̨�͵�������ʾ����ʾ�Ľ�����������˷��ꣿ��������
����ijһ���Ϊ���ջ������ն�����ԭ��ģ��Һͱ���һ�����Դ˲����зֺ��IJ���������һ����С���ѵĽ��ա�������һ�����̨�Ͳ�����İ��Ž�Ŀ��ֻ�ܰ�ƽ��û�˿��Ķ�ͯ���ӰƬŪ��ȥ�ݡ���ЩӰƬ�����ܴΣ���Щ���ǹ�ʱ�ĺڰ�Ƭ�����˿��˲����⣬�ർ����˵�������Ƕ�ͯ�ڣ�Ϊ�˺��ӣ��������ŵ�ɡ�С�������⣬�����˵�����尢�����صظ��㰲���˽�Ŀ���װ���С���ѣ��㲻Ҫ������Ҫ���ġ��ܶ���֮�������涼�����ù�ȥ����ʡ����ý�Ŀ��Ǯ�����������Ķ�ͯ��Ŀ��ָ��С���ѻᰮ������ʵ����ͯ�ڵ��������õģ��������ǵĽ��ո��㡣���˽�ʦ�ڣ��ͳ�Щ�����質�����ʦ���ҵ����ܶ����ʦ�������Dz�������Щ�衭�����ʴ���ȫ�����㡣��������дӦ������Ʒ����Ȼ��������dz�����Ӧ���ĸ�Ҳ���ܵ��������ҿ�������̨ǰ������û�����������ǶԵģ�����������ĸ����ҧ����ͷ�������ʦ������ֵ����������ָ�Ҫ�ޣ���ô�̳�������ѧ�����ˣ���ǰ�ҵ���ʦ���������ָ����һ����Ƥ�������ڲ����ˣ���Ƥ������õ����ˣ������˴��ھ�Ҫ������������Խ��Խ������������Щ��ƶ��СƷ����ƽ�������ӻ����Բ����������������
�����Ե��ӹ�����˵�����˵��ǣ�����ÿ�춼�ǽ��պʹ�ļ����գ�����Щ���������ָ������ý�Ŀ���Ե���̨�ıർ��˵�����ҵ�Ҳ�ǣ�����ÿ�춼�ǽ��պͼ����գ���һ�����DZ���������ҵ��Ŀ��������վ�ڱർһ����˵����������Ӧ�����µ���̨���Ѵ�������Ϊ���������ӽ��պͼ����յ���Ŀ��������˵�������ж�ͯ�ڡ�����ڡ����˽ڣ���ôû��������أ�Ҫ֪���������˼縺��������ص����ٱ���˵�������и�Ů�ڣ�Ϊʲôû�����˽��أ�Ҫ֪�������˸���Ҫ�ػ����˵�������Ҳ���صȵ���սʤ����ʮ���꣬ÿ��ġ����ߡ��͡��ˡ�һ�塨�����Դ����ǡ��������������Ժ�������ÿ�춼��һ����Ŀ��ֻҪ�������Ŀ֮�£����ܽ�Ŀ�û��������ݡ���������ڣ����ˡ��˵����꡷���ƺ�ûʲô���ݵ��ˣ����ʡ������������궼�������������벻����ʲôר������Ϊ��ĵ�ӰƬ���Ǿ��á��ɴ�ʲô�����ݣ�����̨�ż٣�����Ļ�Ϸ�һ����Ļ����̨ȫ����Ա��ȫ�����е���ͬ־�¾�����Щ���������������������������Ļ��ð��һ���������ͺ����˲����ˣ���������
������Щ���Կ��ܻ�Ⱦ��ij�����շ����IJ��������硨��ɫ�����塨�����������ޡ������ֲ���Ҫ�ü���ŷ���һ�Σ�һ̨����Ҳ����Ⱦ��һ���ֲ��������Բ���������ʱ����������������ÿ�춼�����������ɺܼ������������õģ�ÿ����һ�Σ�������������Ҫ���к��ô������֮�£��ҷ��ִ�ҶԵ��ӱȵ��Կ��ݵöࡣ������
����*��*��*������
������ƪ���������1996��11��8�ա�Ϸ���Ӱ����������ʱ��ĿΪ��������������������������������������
������š�����ɡ�������
��76�ڣ����������ɼ����͡�����������������
�������������ɼ����͡�����
�����ϴ���ݻ������������ң����Ұ���˭�ĸ衣��ʵ���벻����ֵ����֣���˳��˵�˸���ͷʿ����ʵ��ֻ����ʱ����ͷʿ�ĸ����������䡣���������������ĸ�Ӣ���еļ��д��̣�CD��һ�Ŷ�û�У���������Ӵ��Ҳ���������ǵĸ��ԡ�ֻ��һ������Щ��ͻ��뵽���̵����£��ö�����ǰ���ҳ�����������ҹ�ﵽ������һλ���ɼ������ͣ���ʱ���������¼������������ͷʿ�ĸ衣˵����������˼�����Ǹ�������ʶ�˼ң�ֻ�����ѵ����Ѹ��������������ַ��ҹ��һ������һͷײ�˽�ȥ������һȥ�����ĸ��ˡ�̹��˵����������Ƿ��ѣ�����Ҫʡס�ùݵ�Ǯ������ŦԼס���úܡ����粻�����ɣ������Ͳ��������ǽ�ȥ���������绰�о�����ץ���ǡ������˼�������ȴ�ܸ��ˣ�����������һҹ���ĵ����С�������������Ļ������к�Ȼ�ġ������������λ���������б�Ӣ�ĵġ�����������й����棬�����ѵ����ѷ���ġ��ҷ��˷���������ò����á���λ����̸�������Ƿ��ڵ�����ʮ�������ս�˶���¶�켯�ᡢ��ʾ���������У���������С�����ϳ��ο������췴������ʱ��������顣����ʱ���۾��ﶼð��⡣����Ҳ��Щ���Ƶľ�����������ϲ��̸��������������̸̸�й��ĺ�����������Ҳ����̸���ܵ���˵�������ҵ�ӡ�����ijλ���ѣ�������ͬ���㣬����ȴ����Ͷ���������ܾ��������뷨�е㼫�����ζ��Ҫ�ǰ�����˵�����Ҳ���������ѧʲô��Ӧ�û�ȥ�����췴���Ҳ��������Ǹ������⡣��������ô˵��������������Ʒ���dz�֮�ã���һ��������Ҳ���ò����ϡ�������
�����Ҽǵ���λ������������һͷ������������ˮ����ţ�п㣬����һ�����ӣ������в��ٰ�˿�������Ǽ�խС������Ĺ�Ԣ���һλ���긾Ů�������������š�����һ��ɵ�ǺǵĽ�Ů����Ҳ��������Ů�����ܵ���˵����������ɹ���ʿ������ʷ������������˼���һ�ʣ���Ϊ��������ͦ����������Խս�����������ӣ�����һ�в��������賿ʱ�֣����Ƕ����ˣ�����̸����Ũ�������������ڰ�ҹ����ս��������ʮ��������Ǿ����ڹ���ҰӪ���ڻ�ѱ���̸�ż�������һҹ�������Ŵ����̡�����������Ҳ�й���ֻ�������ڹ������ɽ���ϡ���������ɽ�ߴ�ӣ�Ҳ��������ɽ��ľͷ��һ��֪����Ұ�����ѻ����س���һҹ�����ڴ��飬��û�г����ֻ����һ���̳����ˣ��������ϳ��Ĵ�Ҷ�����Լ�����һ֧���м��ȴ�ϸ���û��һ�㣬һ�Ż�ð�����������ҵĽ�ë���˸����⡣��Ҷ��û����Ŷ������в��ٿ������ҳ���һ�ڣ��о�����̫��Ѩ�ϰ�����ǹ��һͷ�Ե��ڵء�ֻ��ϧ���ǹ�����������û��ʲô���壬ֻ���Լ�����Щ����ѡ��Դ���ûʲô�ɱ�Թ�ģ�ֻ�Ǿ����Ѿ����ˣ�����Ҫ�ɵ��ġ��������Һ������������IJ�֮ͬ������������ô˵���������ĸ������У�����ϲ���Ļ������ɡ�������������������
�����š����ɡ�BOOK������
��77�ڣ����������ǣ�1��������������������
�������������ǡ�����
������һ�Σ��������ϰ˵�����߹���������������֣����ʱ���̵궼û�п��ţ��������е��Ͽտյ�����ֻ�����ַ���ı���ֽ��������ä�ˡ������ð뵼��¼�������࣬������衣�ҵ���ŷ���ܶ�ط������������ֲм������ֻ����������������ѹ������ǿ�����ä��������������Ϊä������ֵ��ͬ��IJм��ˣ������������������߳ܡ���˵�����ڱ�����������Щä�����϶����࣬�質��Ҳ���ڱ��ҡ��������dz����ĸ裬�Ҷ���Ҳ������������ʱ���ֶ���������ä�ˣ�����һ�������ˣ��Ҿ������־����е���֡��Ҽ������ָ����������ߣ������������Ͽ��������������ġ����룬����и�ä��֮�ң��������չ�����������ϴϴ�裬�����·�����������������������ǵ�������������ö�������������֡���������ñ��������ܶ�ä���������츳�����Ժú�ѧһѧ����ְҵ�����ҡ��������в���ä�����ּң������м�������������������
�������ĵ���ּ����̸��ιػ�ä�ˣ�����̸������������Ȼ������˵�������ǹ���ģ���������Ҳ���ڡ��Ҽ������������ߣ�����������һ�������������Ͽ����ġ���һ�����ʮ�����ң���׳��ţ��ͷ��һ����ñ�����������ʵ�����ë����������ͷ���е����ͯ�����ë�����ϴ���һ����Ƥ�ѿˣ��������գ�������������Щä�˸ɾ�������Щ������û�����գ����������������ġ������ﵯ�ŵ缪����������������֧��һֻ���٣��Ų���һ��̤��ģ�ϥ��˩�������࣬ѥ�Ӹ��ϡ�����˩�����壬�����ط�����Ҳ����һЩ���飬��Ϊ��������������ֹ��˵������Щ����������ʱ����������˵��������һ֧���ֶӣ���������˵����һ�������ڰ����Ĺ�����������һЩ�ײ����͵�����������ʱ�����ᣬ����һ���ӣ��͵ö��µ���Ǯ���ߣ�����ͻ�ͷ�Σ���Ϊ��̫���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