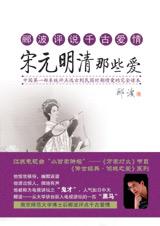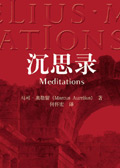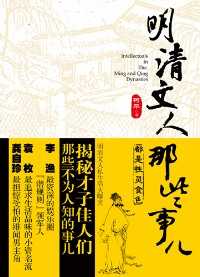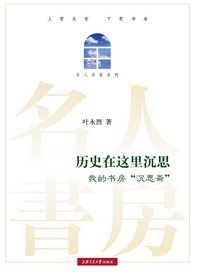明清史事沉思录-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虹←桥←书←吧←。←
第37节:“拟桃源”解(5)
在封建社会内,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对抗,其社会基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仅包含了地主、贵族及其最大的代表者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不得不去租佃地主的土地,把收获的大部分作为地租交纳给地主;而且还包含了中国封建社会两三千年来,始终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作为“四权”之一的政权这根绳索,既是这种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也是为巩固这个社会经济基础而服务的上层建筑。喘息、挣扎在地主阶级铁蹄下的农民,被逼上梁山,奋起造反后,必然把矛头指向地主阶级政权这根绳索,不断地打击它、松动它,并在斗争中建立起与地主阶级政权相对抗的革命政权。但是,从陈胜、吴广大起义直到近代洪秀全等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所有的农民没有也无法认识到产生封建关系的另一个根源,不是别的,正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两三千年来,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对于这个封建剥削与封建压迫的社会基础,在我国古代前仆后继的农民战争中,没有一次农民战争曾经予以触动。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个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不仅不断孳生出新的封建剥削关系,而且革命农民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政权,无法摆脱与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以家长制为其重要内容的封建等级制的制约。下面,我们从明末农民军所建政权的礼仪这一侧面,来看一看大顺政权发展的必然趋势究竟通向何方。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在农民军内部,曾发生过这样的事:“闯贼日置酒宫中,召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刘宗敏、李过等欢饮。牛、李执礼恭,闻呼辄避席而答。余贼杂坐觥倾酒,手攫食。宗敏时呼大哥,闯贼无如之何。贼党久称公侯将相,而贼态自在。坐则相压,行则相谗,谑以诟詈,戏则推蹴,目不能识丁,手不能握管。……时加以规讽,不能改也。”[4]又,农民军的重要将领“顾君恩往往科头坐吏部堂,举足置案上,乘醉携蛮童,唱边关调为乐。伪尚书企郊规之曰:‘衙门自有体,不比营中可以自放。’君恩咻之曰:‘老宋犹作旧时气象耶?’”[5]此事颇为发人深思,它尖锐地表明了革命农民与封建礼仪之间的矛盾。牛金星出身举人,对封建礼节当然是娴熟的,李过是李自成的养子,而且常常身不离自成左右,对日益发展起来的封建礼节耳濡目染,自然也早已适应,所以才那样“执礼恭”。而像刘宗敏、顾君恩那样的重要将领,特别是战功赫赫、握有兵权的刘宗敏,来自农村,出身寒微,对封建礼节还很不习惯。“老宋犹作旧时气象耶?”顾君恩可谓一语道破了革命农民与“旧时气象”,亦即附着在旧的地主阶级政权机体上那套封建礼仪之间的矛盾。这时,李自成毕竟还没有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东有满兵及吴三桂,南有南明,西南有张献忠,一言以蔽之,大顺政权还没有一统天下,而且根本还谈不上巩固二字,因此李自成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威还没有完全确立,他对于老部下的失礼行为,暂时也就只能“无如之何”。当然,不管是刘宗敏也好,还是顾君恩也好,他们对李自成的失礼,毕竟是那个历史时期暂时的现象。如果李自成的帝位坐稳了,无论是刘宗敏、顾君恩或是其他任何人,如果他们不存心想身首异处的话,就必须得惶惶然地向李自成叩首称臣,严格遵从一切有关的封建礼节。追溯历史,这个问题便更为了然。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后,起初还是“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高祖朝,太公拥彗,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6]就刘邦父子而论,当了皇帝后,父子关系必须服从于主臣关系,当年他们在泗水之滨耕作之际,恐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必须看到,李自成与牛金星、顾君恩等将领之间,以及顾君恩与旧营垒中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宋企郊之间的礼仪上的矛盾,绝不是彼此间个人品质的不同而造成的,归根到底,还是那个封建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
※BOOK。※虫 工 木 桥 虹※桥书※吧※
第38节:“拟桃源”解(6)
礼是什么?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它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关系的规定;而在封建社会中,则是封建等级制下尊卑贵贱秩序的规范。让我们来看一看,李自成在北京登基时,究竟采用了什么礼仪。
需要指出的是,李自成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固然是在北京。但实际上,在西安名曰称王,实已称帝。从李自成在西安以及在北京坐上金銮宝殿之前的一系列礼仪上,我们不难窥知这一点。例如,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后,“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7]这就不是行的王礼,而是行的帝礼;自成“每三日,即亲至大教场校射,身御蓝布袍,张小黄盖乘马,百姓望见黄龙旗皆辟易”。[8]自成穿蓝布袍并不像某些史学工作者所解释那样,是什么艰苦朴素,保持农民本色,而是由于李自成等在五德始终说的影响下,认为明朝既是火德,他们便“以水德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9]值得注意的是,所张“黄盖”,亦即华盖,也是用天子之礼。又如:自成早已称朕。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在攻克潞安,分骑趋怀庆、彰德时所发布的檄文中有谓“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10]云云,是其一例;进京后,三月二十三日,自成在文华殿召见明朝降官时,谓“朕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11]是另一例。人所周知,朕,我也;在先秦时代,不论尊卑贵贱,都可以称朕。但至秦始皇时,在李斯的建议下,朕变成了皇帝的代名词、专用品,后世一直沿袭下来。不仅如此,李自成在部属、降官甚至百姓的口语中,也早已被称之为圣上、天子、皇帝、万岁。请看事实:李自成克昌平后,“我兵(按:指明朝军队)至三里坡,已有老人、生员在前迎接,刘老爷(指刘宗敏)先至,吾辈跪云:昌平守兵降。刘老爷云:圣驾在后。须臾皇帝(自成)至,跪降之”。[12]进京后,宋企郊对前来攀附的秀才说:“贺朝大典,安用若辈,速回读,候新天子考试。”[13]而普通百姓,在李自成军刚刚攻破北京之际,“设香烟,粘黄纸一条,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14]凡此都充分表明,实际上李自成早已称帝,那套散发着封建君主腐朽气息的礼仪,犹如蛇菌、毒蕈,把李自成装点得面目全非了。而李自成在北京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的礼仪,因为事先就经过精心的安排、演习,虽然是在山海关战败之后匆匆举行的,但仍然颇为隆重。史载:“二十九日丙戌,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礼。”[15]而在此前,大顺政权的礼部已“示闯贼先世祖讳,如自、印、务、明、光、安、定、成等字悉避”。[16]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这里,我们不妨将李自成的登极仪,跟被李自成推翻的明王朝的老祖宗朱元璋称帝时的登极仪,略予比较。史载:“明兴,太祖以吴元年十二月将即位,命左相国李善长等具仪。善长率礼官奏。即位日,先告祀天地。礼成,即帝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及都民耆老,拜贺舞蹈,呼万岁者三。具卤簿导从,诣太庙,上追尊四世册宝,告祀社稷。还,具衮冕,[17]御奉天殿,百官上表贺。”[18]对比一下李自成和由靠农民起义起家,最后当上封建皇帝的朱元璋的登极仪,我们不难发现,何其相似乃尔!
过去,史学界某些同志在论述李自成政权时,强调李自成的称帝及其封建礼仪,只不过是沿袭了封建政权的形式,并不影响大顺政权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恩格斯说过:“直到现在社会是在阶级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甚至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立已被遗忘了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之上的、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19]恩格斯分析的道德,也适用于礼仪。在阶级社会里,礼仪总是阶级的礼仪,超阶级的礼仪是没有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封建社会的礼仪,是封建等级的产物,是对地主阶级确立的尊卑贵贱秩序的规范。李自成及其大顺政权既然被这种规范所制约,就不能不在实际上被这种规范所筑起的一堵高墙,与革命农民相隔绝,沿着封建化的道路迅速滑下去。更何况问题还在于另一个方面,即植根于一家一户个体生产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家长制,本身就是历代封建帝王统治的支柱;而作为不断分化的小生产者的代表人物李自成,随着起义后地位的改变,手中的权力愈来愈大,是很容易沿着家长制的道路,由一家一户的家长,变成全国最大的家长——封建皇帝的。这是历代农民革命变质的内因,李自成及其大顺政权,丝毫也不会例外。仅仅从大顺政权的封建礼仪这一侧面,难道我们还不足以看出,这个政权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不正是通向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吗?必须看到,包括封建礼仪在内的地主阶级的政权形式,本身就是农民不可能斩断的绞索。把这根绞索抽象化,抹杀其阶级实质,起码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解。
。▲虹桥▲书吧▲
第39节:“拟桃源”解(7)
二
如前所述,家长制是封建等级制的基础。两三千年来的封建社会,贯穿着这根宗法纽带。封建的家长制,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产物,又是巩固这个基础的利器。地主阶级及其政权通过封建家长来实现它对农民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要求。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陈词滥调,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金科玉律,大肆宣扬,以确立家长在家庭内的绝对统治。封建的政治体系与家族宗法的伦理体系密切配合,巩固封建家庭秩序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紧紧相连。因此,封建家长的权力,实际上代行着一部分封建国家的职能。明中叶尹畊有谓:“国制,族有望,甲有长,里有总,其乡秩然也。”[20]这就清楚地表明,明代的封建统治者,把封建家族关系与基层政权的保甲制糅合在一起,使族权这根绳索,更紧地捆绑在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身上。
与历次农民起义一样,明末农民大起义从酝酿发动到燃起燎原烈火的过程,就是冲破封建宗法关系束缚,不断对族权予以打击的过程。就张献忠来说,史载:“开科取士,状元姓易,本姓杨,因献忠极恨朱、杨、左三姓,见无不杀,故去木旁以避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