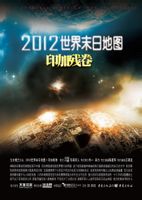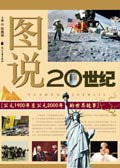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都有幽默感,无论他们的谈话或是书信往来,总是庄谐杂出,令人捧腹。刘半农与钱玄同一说话就要抬杠,他说他和钱玄同“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并以半农体作“抬杠诗”一首:“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每当二人抬杠时,周作人总是在旁静静地倾听,脸上挂着理解与欣赏的微笑。当然,有时玩笑也会开到周作人的身上。有一次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和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的回信却令周作人吃了一惊:信无笺牍,但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昭代名伶院本残卷”,信文竟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按: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了他。拜一拜,手儿呵,你就借去了罢。”这就是活泼、幽默、才气横溢的江南才子刘半农。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曾说那时办《新青年》的人很寂寞,“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是“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在同一文中,鲁迅先生还以切身体验写道:“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到了1918年3月,新文化运动的几位先驱者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就像奔腾于沙场找不到敌人的战马,独自昂首刨蹄,仰天长啸。因为敌手畏葸不前或曰不屑与之对阵,钱玄同和刘半农设计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上演一出“双簧”,以诱敌应战,然后好展开围歼。先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诸君子”一封反对白话文的长信。在这封信中,钱玄同以旧派的口吻,收集了复古守旧派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无知的攻击和引人发笑的责难,行文之乎者也,通篇浓圈密点,洋洋洒洒三千四百余言,黑乎乎一大片,酸腐之气冲天。而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写了一封更长的《答王敬轩》的信,对“王敬轩的信”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逐段驳斥,全篇行文用白话,新式标点,有理有据,诙谐活泼,把当时国故家们的丑态描写得活灵活现。比如对反对白话文最烈而极为卫道士们推崇的林纾,钱玄同以“追星”口吻对其盛赞一番:“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刘半农则把这一段批得体无完肤,他指出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何以如此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的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未尝或者是没有加以过问。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第三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刘半农还嘲讽了旧派对新文学无知而又不懂装懂的可笑。他针对来信写道:“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耶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指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耶夫,表字斯奇。照译名的通例,应该把这‘陀思妥耶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像先生这种横路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赞成。” 。。
3。演“双簧”的钱玄同和刘半农(4)
“双簧信”在《新青年》上一发表,当即引起社会的关注,同时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轰动,在旧派文人中也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竟然真有人相信“王敬轩”是个真人,并写信给《新青年》向他表示敬意,而对刘半农的回信表示不满,并向《新青年》要求“讨论学理之自由权”。
通过主动挑战,革新猛士们终于达到了造成声势、以开风气的目的,而封建守旧派分子也开始集结反攻,一场新旧势力大决战终于打响。萌芽在风雨中才能茁壮成长,真理在辩论中才能愈辩愈明。经过一个又一个回合的激烈搏战,新文化最终可谓大获全胜。
大战前的寂寞是难耐的,胜利后的寂寞有时会更难耐。后来的刘半农一心学术,少问世事了,原来那股锐气,大家以为都没了,还因此没少挨最爱骂人的那个周树人的骂。不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次办《世界日报》的成舍我找到蛰伏了多年的刘半农说:“怎么老不给我们写文章?”刘半农说:“我写文章就骂人,你敢登吗?”成舍我说:“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真的就写了一篇,名为《阿弥陀佛戴传贤》,讽刺当时的考试院长戴传贤只念佛不干事。《世界日报》也不食言,即在第一版发表了此文。戴传贤看了七窍生烟,以查封数日处罚《世界日报》,但对刘半农,却丝毫奈何不得。北大刺儿头多,弄不好扎得满手是血,倒不如放他一马,落得个大人大量,新鞋不踹臭狗屎的美名。
中国人向来迷信又多忌讳,尤其对“死”常常三缄其口,万一不慎出口,也要“呸呸呸”唾地三口以出晦气。钱玄同年轻气盛,又过于偏激,向不讳言死字,甚而至于愤言:“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年届不惑,竟要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并为此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一些稿子,都是些搞笑的东西。因为正赶上张作霖大帅进北京,为避免引起麻烦,该期专刊并没有印行,但其要目却流传出去了。不明内情的人见了,误信为真,相互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吊唁。1928年9月12日,钱玄同41周岁寿辰,胡适针对其“40岁就该枪毙”论,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周年纪念歌》为钱玄同贺寿。歌云:“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不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9月12日,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9月12日,到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钱玄同读后哭笑不得。1938年夏,北平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楚报》发消息误为钱玄同,当然又有不少人发唁电寄挽联。
惜乎天不佑奇才!刘半农、钱玄同二人后来都不幸英年早逝。刘半农1934年去世,主办《论语》月刊的林语堂送其一副挽联,下半联说的就是逝者撰文批戴之事:“此后谁赞阿弥陀佛,而今你逃狄克推多(专制、独裁)。”事隔5年之后,1939年1月17日傍晚,钱玄同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这之前,他还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并四处奔走联系变卖李大钊藏书,为其子女筹措逃赴延安的路费。这是后话,此处打住不提。
。 想看书来
4。李大钊为国人敲响晨钟(1)
有人曾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健将:在《新青年》的同仁中,没有人比李大钊更宽厚深沉了,他以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独立开创了属于他也属于现代中国的一片新天地。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此生还真是多灾多难。就在出生不久,父母就结伴赶赴黄泉报到,而他自己年仅38岁就被张作霖大帅送上了绞刑架。
李大钊早年就读于袁世凯创办的北洋法政学堂。1913年冬,他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多后回国,正赶上梁启超、汤化龙筹办《晨钟报》(1918年9月改名《晨报》),当即决定应邀担任该报总编辑。李大钊经营此报抱负远大,决心承担振兴民族、再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在该报创刊号上,即刊出了他亲笔撰写的《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等文,“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应发之曙光,由是一叩发一声,一声觉一梦,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盖青年者,国家灵魂,《晨钟》者,青年之友。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
该报在编辑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办得真是有声有色,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例如,为激励读者振作起来,为创造新中华而奋斗,他在报纸显著位置特意设计了一个古钟图案,在古钟上面每天选登一条警语,希望读者能“一叩发一声,一声觉一梦”。像“少年人望前,老年人望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铁肩担道义”等,都是李大钊亲自编选的。尤其对“铁肩担道义”,李大钊更是心有灵犀、感慨有加。此语出自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之口。杨继盛跟李大钊相隔几百年,惺惺相惜,同病相怜。杨继盛父母早亡,幼年饱尝孤苦,白天放牛割草,深夜秉烛读书。皇天不负有志人,杨继盛竟如愿以偿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因得罪大奸严嵩而被诬陷下狱处死,年仅40岁。临刑前杨继盛还放声高歌:“浩气远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这情节跟李大钊走向绞架时的慷慨陈词、从容就义又何其相似。“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杨继盛在狱中墙上题写的两句述志诗。除在《晨钟》报上刊出“铁肩担道义”之外,李大钊又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赠杨子惠。
1917年底,李大钊接受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新青年》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