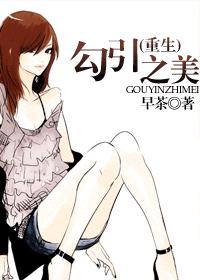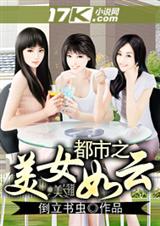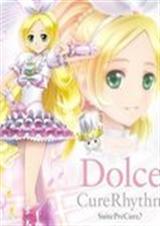汉字书法之美-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欧洲的建筑长时间追求向上垂直线的上升,中世纪歌德式大教堂用尖拱(pointed arch)、交叉肋拱(ribbed vault)、飞扶拱(flying buttresses)交互作用,使得建筑本体不断拉高,使观赏者的视觉震撼于垂直线的陡峻上升,挑战地心引力的伟大。
汉代水平美学影响下的建筑,在两千年间没有发展垂直上升的野心,却用屋檐下一座一座斗拱,把水平屋檐拉长、拉远,在尾端微微拉高起翘,如同汉代隶书的书写者,手中的毛笔缓和地通过一丝一丝竹木纤维的障碍,完成流动飞扬漂亮的一条水平“波磔”。
东方美学上对水平线移动的传统,在隶书“波磔”、建筑“飞檐”、戏剧“云手”和“跑圆场”都能找到共同的印证。
书法美学不一定只与绘画有关,也许从建筑或戏剧上更能相互理解。
“波磔”的书写还有一种形容是“蚕头雁尾”。“蚕头”指的是水平线条的起点。写隶书的人都熟悉,水平起笔应该从左往右画线,但是隶书一起笔却是从右往左的逆势,笔锋往上再下压,转一个圈,形成一个像“蚕头”的顿捺,然后毛笔才继续往右移动。
写隶书的人都知道,水平“波磔”不是一根平板无变化、像用尺画出来的横线。隶书“波磔”运动时必须转笔使笔锋聚集,到达水平线中段,慢慢拱起,像极了建筑飞檐中央的拱起部分。然后笔锋下捺,越来越重,再慢慢挑起,仍然用转笔的方式使笔锋向右出锋,形成一个逐渐上扬的“雁尾”,也就是建筑飞檐尾端的檐牙高啄的“出锋”形式。
之二 书法美学(2)
隶书的美,建立在“波磔”一根线条的悠扬流动,如同汉民族建筑以飞檐架构视觉最主要的美感印象。
《诗经》里有“作庙翼翼”的形容,巨大建筑有飞张的屋宇,如同鸟翼飞扬,美学的印象在文学描述里已经存在。
如今走进奈良法隆寺古建筑群,或走进北京紫禁城建筑群,一重一重横向飞扬律动的飞檐,如波涛起伏,如鸟展翼,平行于地平线,对天有些微向往,这一条飞檐的线,常常就使人想起了汉简上一条一条的美丽“波磔”。
在西安的碑林看“曹全碑”,水平“波磔”连成字与字之间的横向呼应,也让人想起古建筑的飞檐。
石刻隶书“石门颂”, 开阔雄健的气势
“曹全”、“礼器”、“乙瑛”、“史晨”这些隶书的典型范本,因为都是官方有教化目的设立的石碑,隶书字体虽然“波磔”明显,但比起汉简上墨迹的书写,线条的自由奔放,律动感的个人表现,已大受限制。
石刻隶书到了“熹平石经”,因为等于是官方制定的教科书版本,字体就更规矩森严,完全失去了汉简手写隶书的活泼开阔。
石刻隶书除了少数像“交趾都尉沈君墓神道碑”,还保留了手书“波磔”飞扬的艺术性,一般来说,多只能在拓片上学习间架结构,看不出笔势转锋的细节,因此也不容易体会汉代隶书美学的精髓。
近代大量汉简的出土,正可以弥补这一缺点。
汉代石刻隶书中也有一些摆脱官方制式字体的特例,例如极为许多书家称赞的“石门颂”。
近代提倡北碑书法的康有为,曾盛赞“石门颂”,认为“胆怯者不能写,力弱者不能写”,可以想见“石门颂”开阔雄健的气势。台湾近代书法家台静农先生的书法也多得力于“石门颂”。
“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开通褒斜石道之后,汉中太守王升书写刻在摩崖上的字迹。“摩崖”与一般石碑不同,“摩崖”是利用一块自然的山石岩壁,略微处理之后直接刻字,在凹凸不平的山壁上,没有太多人工修饰,字迹与岩石纹理交错,笔画线条也随岩壁凹凸变化起伏,形成人工与天然之间鬼斧神工般的牵制。许多“摩崖”又刻在陡峻险绝的峭壁悬崖上,下临深谷巨壑,或飞瀑急湍,激流险滩,文字书法也似乎被山水逼出雄健崛傲的顽强气势。
在汉隶刻石书法中,“石门颂”特别笔势恢宏开张,线条的紧劲连绵,波动跌宕,都与“乙瑛”、“曹全”大不相同。甚至在“石门颂”中有许多字不按规矩,可以夸张地拉长笔画,特意铺张线条的气势。
一九六七年因为修水坝,原来在山壁上的“石门颂”被凿下,保存到汉中博物馆。“摩崖”原来在自然山水间的特殊视觉美感,当然一定程度受到了改变。
汉代书法也许要从简牍、石碑、摩崖、帛书几个方面一起来看,才能还原隶书在三百年间发展的全貌。
隶书“波磔”的水平线条在唐楷里消失了,但是一个时代总结的美丽符号却留在建筑物上。看到日本的寺庙,看到王大闳在国父纪念馆设计的飞檐起翘的张扬,还是会连接到久远的汉字隶书“波磔”之美。
即兴与自在 王羲之“兰亭序”
“兰亭”是一篇还没有誊写恭正的“草稿”,
保留了最初书写的随兴、自在、心情的自由节奏,连思维过程的“涂”“改”墨渍笔痕,
也一并成为书写节奏的跌宕变化……。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之二 书法美学(3)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或文化史上都像一则神话。
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和辽宁博物馆各有一卷“萧翼赚兰亭图”,传说是唐太宗时代首席御用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但是大部分学者并不相信这幅画是阎立本的原作。
然而萧翼这个人替唐太宗“赚取”“兰亭序”书法名作的故事,的确在民间流传很久了。
唐代何延之写过《兰亭记》,叙述唐太宗喜爱王羲之书法,四处搜求墨宝真迹,却始终找不到王羲之一生最著名的作品——“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三月三日,那一天
“兰亭”在绍兴城南,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五三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友人—战乱南渡江左的一代名士谢安、孙绰,还有自己的儿子徽之、凝之,一起为春天的来临“修禊”。“修禊”是拔除不祥邪秽的风俗,也是文人聚会吟咏赋诗的“雅集”。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初春,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山水佳境,包括王羲之在内的四十一个文人,饮酒咏唱,最后决定把这一天即兴的作品收录成《兰亭集》,要求王羲之写一篇叙述当天情景的“序”。据说,王羲之已经有点酒醉了,提起笔来写了这篇有涂改、有修正的“草稿”,成为书法史上“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是收录在《古文观止》中的一篇名作,一向被认为是古文典范。
这篇有涂改、有修正的“草稿”,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书法史上的“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死后,据何延之的说法,“兰亭集序”这篇名作原稿收存在羲之第七世孙智永手中。智永是书法名家,也有许多墨迹传世。他与同为王氏后裔的慧欣在会稽出家,梁武帝尊敬他们,建了寺庙称“永欣寺”。
唐太宗时,智永百岁圆寂,据说还藏在寺中的“兰亭集序”就交由弟子辩才保管。
唐太宗如此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已经收藏了许多传世名帖,自然不会放过“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何延之《兰亭记》中说到,唐太宗曾数次召见已经八十高龄的辩才,探询“兰亭”下落,辩才都推诿说:不知去向!
萧翼赚兰亭
唐太宗没有办法,常以不能得到“兰亭”觉得遗憾。大臣房玄龄就推荐了当时做监察御史的萧翼给太宗,认为此人才智足以取得“兰亭”。
萧翼是梁元帝的孙子,也是南朝世家皇族之后,雅好诗文,精通书法。他知道辩才不会向权贵屈服,取得“兰亭”只能用智,不能胁迫。
萧翼伪装成落魄名士书生,带着宫里收藏的几件王羲之书法杂帖游山玩水,路过永欣寺,拜见辩才,论文咏诗,言谈甚欢。盘桓十数日之后,萧翼出示王羲之书法真迹数帖,辩才看了,以为都不如“兰亭”精妙。
萧翼巧妙使用激将法,告知辩才“兰亭”真迹早已不在人间,辩才不疑有诈,因此从梁柱间取出“兰亭”。萧翼看了,知道是真本“兰亭”,却仍然故意说是摹本。
辩才把真本“兰亭”与一些杂帖放在案上,不久被萧翼取走,交永安驿送至京师,并以太宗诏书,赐辩才布帛、白米数千石,为永欣寺增建宝塔三级。
何延之的《兰亭记》记述辩才和尚因此“惊悸患重”,“岁余乃卒”。辩才被萧翼骗去“兰亭”,不多久便惊吓遗憾而死。
何延之的《兰亭记》故事离奇,却写得平实合理,连萧翼与辩才彼此唱和的诗句都有内容记录,像一篇翔实的报导文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之二 书法美学(4)
许多人都认为,绘画史上的“萧翼赚兰亭图”便是依据何延之的《兰亭记》为底本。
五代南唐顾德谦画过“萧翼赚兰亭图”,许多学者认为目前辽宁的一件和台北的一件都是依据顾德谦的原作,辽宁的一件是北宋摹本,台北的一件是南宋摹本。
唐太宗取得“兰亭”之后,命令当代大书法家欧阳询、褚遂良临写,也让冯承素以双勾填墨法制作摹本。欧、褚的临本多有书家自己的风格,冯承素的摹本忠实原作之轮廓,却因为是“填墨”,流失原作线条流动的美感。
何延之的《兰亭记》写到,贞观二十三年(*九年)太宗病笃,曾遗命“兰亭”原作以玉匣陪葬昭陵。
何延之的说法如果属实,太宗死后,人间就看不见“兰亭”真迹。历代尊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只是欧阳询、褚遂良的“临本”,或冯承素的“摹本”,都只是“复制”。“兰亭”之美只能是一种想象,“兰亭”之美也只能是一种向往吧!
行草, 行书与草稿的美学
“兰亭”原作真迹看不见了,一千四百年来,“复制”代替了真迹,难以想象真迹有多美,美到使一代君王唐太宗迷恋至此。
汉字书法有许多工整规矩的作品,汉代被推崇为隶书典范的“礼器”、“曹全”、“乙瑛”、“史晨”,也都是间架结构严谨的碑刻书法。然而东晋王羲之开创的“帖学”,却是以毛笔行走于绢帛上的行草。
“行草”像在“立正”的紧张书法之中,找到了一种可以放松的“稍息”。
“兰亭”是一篇还没有誊写恭正的“草稿”,因为是草稿,保留了最初书写的随兴、自在、心情的自由节奏,连思维过程的“涂”“改”墨渍笔痕,也一并成为书写节奏的跌宕变化,可以阅读原创者当下不经修饰的一种即兴美学。
把冯承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几个不同书家“摹”或“临”的版本放在一起比较,不难看出原作涂改的最初面貌。
第四行漏写“崇山”二字,第十三行改写了“因”,第十七行“向之”二字也是重写,第二十一行“痛”明显补写过,第二十五行“悲夫”上端有涂抹的墨迹,最后一个字“文”也留有重写的叠墨。
这些保留下来的“涂”“改”部分,如果重新誊写,一定消失不见,也就不会是原始草稿的面目,也当然失去了“行草”书法真正的美学意义。
“兰亭”真迹不在人世了,但是“兰亭”确立了汉字书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