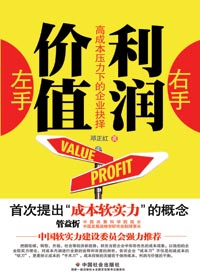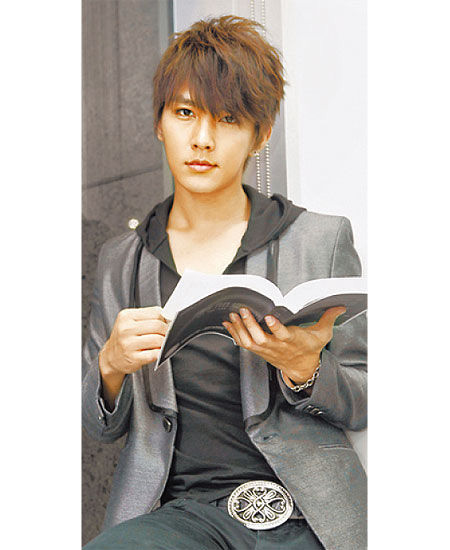���ֵ�Ӱ,�����껪-��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ˡ����ں��濴�����ı�Ӱ�����ĺ�ɫ����ͻȻ�����˶��캮��ķ磬��֪��Ϊʲô����ͻȻ���ú��ѹ���������û�и�������������Ц������ȥ��
2001���Ҷ��ĵ���־�����������мҡ��͡�������ء�����Խ��Խ���ܵ�Զ������һ��Ī�����ٻ����������Լ�����֪�������е�Զ������Ӧ���ж�Զ��ͻȻ�뵽һ����Ӱ���Ƭ�Σ�һ�����˶��మ�ܾõ�Ů��˵���Ҳ������ˣ����������Զ�㡣Ȼ���Ǹ�Ů��Ц�ˣ�Ȼ���������������˵��Զ����Զ����Զ����ǰ����ŦԼ��绰��������������ڳԱ��ɣ���һ���Ҿ������Ǻý��������ڣ���վ������ǰ�����Ҿ�������վ����ߡ�
�����ּ������ϣ���3��
��������������������Щ������������ͼƬ������һƬ�������ң�Ȼ��������Ȼ��Į���ҷ�����Įһ��һ���������Ͽ��ºۼ����������ǰѿ̵�����ɫ��������Դ��С��ҵ��ֱ�һ�����һ�����ʲ裬Ȼ���ڷ�ҳ�ļ�϶���һ�̧ͷ����ͷ�������ļ�į�ĸ��ӣ�ż���л�ɫ����ëƮ���������������Һ�ɫ��ͫ���ϡ����������ʱ��Զ����һ��ɽ�ϻᴫ��������Զ��������ĺɫ��������������ؽ��������������������������У�ҹɫ��ɺ���ƻ���ϣ��Һ�����־������Է���
2001�����ĩ���ڿ������ǻ�����ͦ��ҵ��һ�������硣������ͻȻ������һ����ӡ��ܺã������ࡣ������ô������ƽ�ͣ�����������һ���ˣ���ͬһƬ�����ĺ��������Ҽǵ����ڿ�������ѣĿ���̻��ʱ����˵��Сʱ����һ�����Ѹ����ң��������ʱ����ʹ�ͻ�һ�����������������ʱ������������������ǣ�����Ը��Ҳ���ر�����ʵ�֡�������������ɫ�տ�����գ���ʱ�������һЩ����������ʱ��û�С��Ҵ���û�ж����������¹�Ը������Ϊ��û�п��������ǡ�2001������ĩ��ʱ�����кö�����ǣ�������ȫ��û������ʨ������û���������������Լ���˫������Ҳû������
������һ���ط�����̨�������������������������������Ҹ���վ����̨�ϡ��ҹ����Ŷ������ҵƻ���ǰ��2001�곤����ʱ��Ƭ�ν����߹�����ͬ��Ӱ�Ļطţ�û����������ɫ�ķ��ƿն����������Ҹոճ�����ͷ�������������������˵��������ҵ�ͷ������������
2001������һ�̣�������¥�¶�����̨�ϣ��ں�Х�ĺ�ɫ���У���������ŵ�����У������µ�����������У���ʱ��ͲѮǰ���Ĺ켣�����ӯ����
������������£�
2002�����β�������Ϻ����½���������Ȼ��ʧ���Ҵ��ź�ɫ�ij��������ڵƻ�ͨ����ʯͷɭ�ֵ��ѷ����棬����ʱ���㳡ƻ������ʱ��ӿ�ĺ�ɫ��Ⱥ�У�����ʱ����ʱ��Ķ��Ѵ�����������������ͨң����ҡͷ���Եض������������е���Ц����ͬһ��С��졣��һ���е���һ���Σ�һ���߳����߲����ҵ��Ρ�һ��ǰ�����ʱ���һ�վ���Ĵ��ļҵ���̨�ϣ����ź�ɫ����պͰ������������ӯ������һ���Ľ��죬�Ҽ���վ��������ϲ���ij��е������ϣ�վ�ڳ䡤���������յ�ʮ����
2002���ҹ���19������ա��Ǹ����չ��ø���ֻʣ���Ϊ�Ǹ�ʱ���һ��ڸ�����ÿ�챧��һ����鲻�ϵ�����¥������¥�ݡ������������Ҽǵû���һ�����ԣ��������硣�����Ͽε�ʱ�����ǾͰ����ﴫ�����ˣ�����ֽ��һ�������С�������Һܾ��ȡ�����Ϊ���������ˣ��������Ƕ��ǵá������ʱ�������ڴ��ϲ������װֽ���������Ρ��ҵ������г�ˮӿ����������������ֻ���Ҷ���֪�����DZ��˻��ǡ����֡��Ҵ���û������Լ�����ô��վ��19�꣬վ�ڳ��˵��ſڵȴ��Ƽ��˺�ѵ�ʹ��һֱ��Ϊ�Լ���һֱ���Ǹ�������ë���������ϻӺ�����ĺ��ӣ���һֱ���Ǹ�������������Ů����������ѧУ����ֱײ�ĺ��ӣ���һֱ����ʮ���꣬һֱ���ڵ����ϵ��ഺ�������ȥ��
�ٰ�ʱ��ˣ���ͬ���ǿ�Ӱ��ʱ�����ְ���back����Ȼ��һ�оͿ������³����������ǰ�����ǻ�����ô���ᣬ���ǻ�����ô���ԣ�����ʱ�����û����ʧ�����������Ӵ���û�д��ҹ���һ��������ͬ�����µ�Ϫ�������Ǽ��������ѣ�վ���ഺ�ĺӰ��ߣ������ڣ��»������ú������֣�����ʱ�⣬�������ر��ܣ��������ǹ�����Ц���������ˣ���������ֱ�ˣ��˵�������ǰ��������֮ǰ��վ���Ĵ���ɫ��ص����룬������ʮ����ȵ������ºȿ��֣�����Χ��֪�˱˴˳����˸߲��ң�������ͬ�����������������ݳޡ�������������Խ����Ȼ����������۶�ȥ�������տ�����Զ���ҵ�ѧУ�����������������Һ�������������Щ�Դ����ͬ����ĺ�ˮһ�����������档�Һ��Ѿ���ʶ��һ���ˡ�һ�����棬�˴˵�����ͻ�Ц��һ��һ�εؿ̽��˴˵���խ�����֣��������Ǹ�ɬ���߽��һ�꣬��һ�꣬���Ǹ�������������֮����վ���Ϻ�������ȵ��峿��ȥ���г����Ͻ�ı�����һ���˪ȥ�ϿΣ���Χ���������ƶ���ͬ������MV��������ģ���Ĺ��ߡ����������У������ú����ϡ��֡���ѧ����Ӱ��������������֪����ô��������ͺ��ڼ�������������Ч����ֻ���Ҳ����ף������ľ���Ԥʾ��ʲô��
2002�꣬�Ҵ��Ĵ��뿪�������Ϻ����Ҷ��Ա��ų��ص������߳��Ǹ���������19�����أ��Ǹ���ɫ����ů����أ������죬�ǻ������գ������ʹ�࣬��ͬ������˺����һ��Ƥ�����ڷɻ��ϣ��ҿ��Ų�����������˯ȥ�����ﲻ�ϻؼ���������Ƭ��������Խ��Ц�ݣ�������/JYA������ѩ�����ӣ����������������Ĵ���18�ꡣ��������һ������˵���Ļ������ҵ�������Ǵ�Ǯ����ܶ��Ǯ���浽��һ�����ǿ�����ܴ�İ���װ���������е������е�CD�����е����룬����������һ�����ϻ��������������Ժ�����������Ⱥ�³���Ȼ�����������ϲ�����˵ij��У�����ô�������Լ�������˵���ǰ����������������ӯ������
������������£�����2��
2002����û��ϲ�������������˵�У�Ҳ�Ǵ��������������������ϴ��ڿտ�����į�IJݵ��ϴ��С�ÿ�����ڶ������ϣ������ų��ӽ��һ����ң�һ���˴�Խҹ����ɫ�ķ磬��ʱ��Ͱ�����һ�����ʱ���һ����������������������������ѧУ�Ĺ㲥���գ��Ҳ�֪��ѡ��Щ��������˭��ֻ�����������룬����������Ҳ���Ǹ�������ŵ�Ц�ݵĺ��ӣ�һ��վ���������β���ϵ���ͯ���ҵ����Ҷ����и�����ѧ�����ٵģ�����һ�����������������ٴ�¥�°���ȥ���ܶ��ҹ���Ҿ�������20�ߵ�̨����ǰ��д���£���С˵�����Ǹ�����ɬ���������ڷ�����ҳ��˲�䣬�������������㴩�����������졣
���µ���ͯ���������������ס����һ��һ��Ʈ������
2002���Ҽ�ƽû����CD���ҵ�CD���������Ĵ��ļ�����������Ϻ�����һ�����������ӡ�����ij����Ѫ��������ȥ���˸����£�Ȼ�����ܵ��������ſڵ���·�������������CD������������ʮ��Ǯ����һ�Ź������ġ��ʺľ�ѡ�����ұ���һ��ѵ�CD����¥ȥ��Ȼ��ͷ��˯�����������¡¡���죬������һ���������Ժ��Һ�������CD����Ҳ��֪������ʮôԭ���Ǹ�CD�����ҷ���д��̨�����棬��������һ�㱡���ij�������ͻȻ�����Լ��߶�������ʱ��û��ûҹ�س����ڽ�ƽ���ѵ��ź������棬������Щ���ӣ����ľͻ̻�Ȼ����ң���ѩ���ñ�ꡣ
2002�꣬�ƺ�����һ��ʱ��Ķϲ㣬�Ҷ��Լ��Ĺ�ȥ��ʼһ�־����ĸ��ѣ���ͬһ�ֱ��ѣ��ҽ��Ǹ����˵ļ�į�ĺ��ӹ¶�����������18�꣬���Ǹ��º����˶�ȴ���¹µ��ĺ��ӹ¶���������Ƭ��ɫ�Ĵ���ϣ�Ȼ��һ������ͬ�丸һ�����ųɳ������˵ر���ȥ��������λʫ��˵������Ȼ�����ˣ���ײ�ϣ����Ѿ�û��ʲô����ǰ���������־���������ߡ��͡�ͨ�������Լ����Ұ�ҡ����MԼ�ˡ�����������������ɽ��ˮ�ļ��������������������ҡ���������������������������������������������������������ӣ��������������Լ������Ǹ���ô�Ը��ĺ��ӣ����������ڱ����۾����ǰ��ֻ����Ϊ���ҿ�������ǣ�ҵ��ߣ�����������
����������ǰд�Ļ���˵����������ʲôʱ��Ҫ��ǿ���µ�����������Dzſ�����������ת��ʱ��զɤ��м�������ͳɳ�ʱ������ͬ�������νڵ����졣��į�ѹ�������һЦ��⺮��
����ǰ�ĵ��Ӿ������dz����������쳾�����������ϵر�����������
2002��ĺ��٣��Ҵ��Ϻ����Ĵ�������ǰ�����ѣ�����ǰ��·��������������ĸ��з����Լ�����Ƭ����ɵ�����ڳ������档�Ǹ�ʱ����Լ���ͷ���̶̵ģ�һ�������������ڣ����Ҵ��ź�ɫ�ķ���ͷ��������������������߹���ѧУ���ʱ������ľ����Լ��Ǹ��µ��Ĺ��͡���Щ���ӵ��ഺ�������������ܣ��ҿ��������뵽�ҵ��������뵽�ҵ�9��̨�ƣ���Щ��Ƶĵƹ⣬��Щ�˸е��Ρ�
2002�����ĩ�Ѿ���ȥ��2003������Ӻ�����ҵ����������д����ƪ���µ�ʱ�������뿪�Ĵ�ȥ�Ϻ���������ˣ�������ٴ�æ�ؾ�ȥ�ˣ������Ҿ�������Żص��ң�Ȼ��˯��һ���߳��ľ����ڶ����������������̡�
2002�꼺����ȥ��������Ȼ�ϸ���ʱ���У��ȴ�����һֱ�ȴ��Ķ���������������û�г��ֹ���Ҳ����Ҫ���ܾ�֮����ijһ���峿����ijһ��İ���Ľֵ��������ּ�����
���
����д��ƪ���µ�ʱ���Ҹոմ���ʦ�Ҳ��λ�����һ·�ϵƻ�Իͣ����ǵ���������������ǰ���ﲻϢ����ͬ��������������ص��ﻨ��
һ˲�����������˹���������Ȼ���ͷЦһЦ������ǰ�ߡ�
·�Ͼ���һ���㳡����һЩ����ĺ��������ﻬ���壬������������ˮ�����Ħ��ʱ��ʵ������������һ�����Ӹ����߳���һ�ι�������ɣ���֪�����Dz�ҽ����ҹ��Ũױ����ĸ��������ų�Ƭ�ķ������о����Һܳ�ݵĻ��������Դ���ר���Դ���������֪��Ϊʲô����ͻȻ����СA��Ҳ������Ϊ��Щ���Ả�ӵ���Ӱ̫������ԭ����ʱ����ҹ��ҹ�������棬Ȼ����������ʱ�����ػؼҡ�
ֻ������СA���ձ����ѧ�����ң����й����������ü�ƽҪ�����ˡ�
�ҷ����Լ��ڷ�һ���������Ĵ����ҿ�ʼ����Щ����һ����ĺ��ӳ�Ϊ����ĺ��ӣ��������Լ������껪���ŵ����ӡ����ҷ�����һ���ʱ���Ҳ��ɵø������������뿴����������û���ҳɳ��ĺۼ������������ۼ��Dz������ĵ���ǰ�����˺ܶࡣ��Ϊ���ҽ���ʮA����ѡ��һ��Ǹó��Լ�Ϊ���ӡ�
СA���ձ����ϵش�绰���������ʳ�;���źų���ز�ҿ��Դӵ绰����Լ��������Щ���������������������������ɡ���˵�������������˵���á���˵���þ��У������㲻���ġ�
���µ绰���Ҳ�������˵����ʵ�Һ��ۣ����ǣ�����˵��ʲô�á�
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