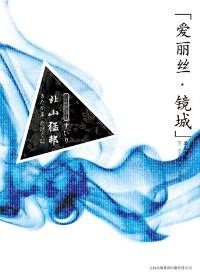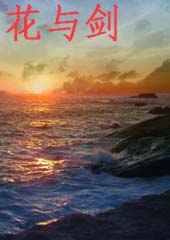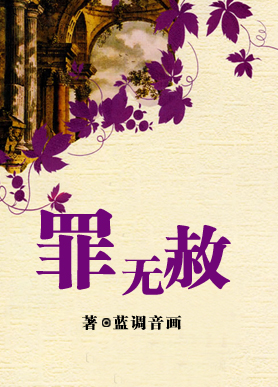花与爱丽丝九月号-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伦敦Dover Street Market开展的家具[F System]系列,是我与ME des GAR?ONS的合作,这些源于我非常崇敬在任何时期都能保持着高品位审美创作的人,川久保玲就是其中的一位。合作契机很偶然,我单纯为了个人创作,设计完成了[F System]这个体系。完成试验后制作了自己的工作室,产品却成为了真正稀有销售的产品。
围绕摄影这一表达方式,曾经一度产生厌恶,冲印也好,形式也罢,可依靠投入大量的钱,运用高深的技法去决定最终的表现,结果会变得很学术而感到疲软。我一直喜欢的是接近对象的统括性。时尚的工作也同样如此,和秀(时装秀)同系列的设计作品对我而言是和服装秀同样重要的东西。所以展览会才会变得那么自然。但是如果单只举行摄影展的话,在东京的小柳画廊有过一次。那次展览气氛惬意,但有种被保护的感觉。空间很不错,只可惜在那一周里事情实在太多,我被折腾得特别累。在纽约艺术馆的[Berlin]影像环境艺术展,因为使用的是柏林Kunst…Werke企划时的东西,运到纽约后的组装都产生了小小的变更。但那个美术馆很棒,是次很好的经历。其他几次展览也都配合了录影和环境装置,还有用灯光表现文字之类的,多种表现形式的组合。
激情式思维模式是我提倡的重点。按照印象中的配置生产的节奏,与印象中的调和,然后是印象与纸,留白,改变节奏的眼力,把以上这些综合起来,就可以把握一个好像电影一般的整体感。不希望交由任何人去做这些。决定摄影作品的关键也是激情,写真集《Stage》和《London Birth Of Cult》是在演唱现场所拍摄的作品,激情和构图感可以明确的体现摄影师的眼力与人性。我对于激情而言一直很有自信。如果是即兴的拍摄就要选择自己的直觉去控制快门。
作为摄影的特征,拍摄的图像在最初被冲印出来的阶段,常被称为显现瞬间。我针对被写体所产生的距离或是距离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我想这就是“匿名性”(偷拍)之美……就是这样,那些不知不觉的样子,我希望原原本本的展现隐含着这类题材的东西,所以绝不可能对拍摄的对象轻描淡写地表现。把伤害的可能性完全的隐藏,把他还原。也就是说,可以称得上把记忆封存起来的事,有时防守也是其中存在的必要性。冲印照片的空间应该常会带来与宠爱这一观念的连接。冲印我选择菲林和数码两种工具。在已经上了涂料的油画布上使用轮转印刷机印刷大开的海报,基本都制作得像苏联的政治宣传工具般来表现。这一切的制作都是大费周章。我特别喜欢弄成全黑的颜色,这就是我拍摄的肖像画大抵都是黑漆漆的缘故。印刷那样的黑色需要反复重叠印刷好几遍。在油画布的质地上用不同的技术,事实上也是我首次亲身实验的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过的经历。此外,在铝上的印刷更是最费功夫的。
Hedi Slimane:颠覆的美学(5)
除了印刷,声效对于我的装置艺术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早期开始创作就一直会这样。从2000年开始把所有的摇滚录像资料整理起来,发现从那时以来,就有录下身边声音的习惯。沉浸于音乐之中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要的。放的录音是Klaxons的演出开始时粉丝们的声音,因为对声音进行了加工,播放速度减慢了。我的装置中还有一块涂成全黑的正方形木板,那是Amy Winehouse舞台的一部分,是女性的,演出的碎片。站在舞台上的Amy确实就是站在这块板上的。纯属恋物癖,狂热信徒的隐喻崇拜。
城市——Reflection
Hedi Slimane坦言自己喜欢城市,他喜欢被围绕的感觉,需要看到身边有人在,但不是说要去真的接触他们。他就像一个孤独症患者,缺乏安全感,只有当生活在城市的喧嚣中时,才有生存感。
城市是他一切成长的土壤,灵感迸发的温床。无论是从Hedi的设计还是摄影,无处不显现着城市的烙印。
巴黎
巴黎是我出生以及成长的地方,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没怎么离开过那儿。我想,这正是为什么我很难离开大城市生活的原因,我真的会感到不安。”
柏林
柏林对我来说是一块空地。当我在那儿的时候,觉得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从巴黎搭夜车,在凌晨当整个城市只有一丁点清醒,寂静的时候抵达柏林。火车从西到东,创造了一种城市间的亲密感。这是非常舒服的,缓慢的旅行。
纽约
我相信纽约会变得比现在更有趣,911之后,人们之间的依存关系发生了变化,让我觉得它更像城市了。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地方。
东京
我一直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总怀疑是否真正已经人在东京,会发生什么全然无知,就好像人还在飞机中一般。
后记:
自从Hedi离开Dior Homme,已经将近8个月,这位设计师用点线和图片向我们交代了他的行踪。我们在西班牙认出了他,在柏林想象他,在全球出版物上找到了他的照片……就像翻看一本影像日记。今天,艾迪斯里曼展示在我们面前。通过他的摄影,他最爱的传媒工具之一。他在里面向我们呈现了音乐,他的另一种激情。在那我们找到了艺术家令人兴奋的三位一体:照片、音乐、年轻人。细心创造的侧影,精心剪裁的线条,带点脆弱的摇滚的羸弱的举止,不带一点陈腐,这正是Hedi里曼用来支撑时装的全部。不要忘了在摇滚回归的最初,那些涌现在伦敦舞台上的乐队同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一起同时也为Hedi走秀。Hedi我们解释道:“五年前我就开始了这项关于乐迷的工作,对我来说,这些乐迷是浪漫主义的化身。”而音乐,对他来说几乎是一次充满启发的旅程,一种哲学。“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音乐在个人修行中产生的影响,是通过音乐对自我的确立:情感、对社会问题的干预,当然也有一种风格的创造、态度等等。”
Hedi的照片并不是一次突袭,我们深知艺术家对图片的偏爱。他描述演唱会气氛、后台、化妆间的纯粹抽象的书籍,关于Pete Doherty的彻底无疑的展露,通过这些阴郁的自由人和流浪者他向我们展示了21世纪初的时代特征。这一次,Hedi来到了地面…他走到了人群中,混迹于世人共同的誓愿。这些黑白照片中的人物颂扬汗水与放任自流。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在紧急状态和集体歇斯底里中抓拍的照片流露出的却是一种奇特的温柔和凄切的克制。这些拍摄于混乱中的照片是沉默的:它们取悦于自己,只是呈现一种情感,呈现某一个私密的孤寂的极乐时刻。这些照片就像格斯?范?桑特电影中的画面,一幅接着一幅。身为大卫鲍伊、边缘乐队(Clash)的乐迷,Hedi流连于青春的项背,醉心于那些年轻脸庞上沁出的粒粒汗珠,他们又长又密的头发盖住了双颊,向我们诉说着另一些故事…。
扣上扣子:这仍是我们谈论的时尚,他照片里散发出的理想主义情怀也给他的服装披上了一种风格,今天追求穿衣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及那些想要穿出风格的人仍然是Hedi式打扮。对于这位设计师来说,摄影从来不是安格尔的小提琴:“这只是一个轮换的、补充的媒介,主题却没变。我用系列时装去描述一个人,然后用另一套时装去描述同一个人,现在我只是换成了用摄影去描述他。”看Hedi的照片,同时也是看他的时装。时装?对,没错,“它一直都是一个现实问题。”他是想说,很快,他又要奔赴另一场冒险。
Patrick Wolf:音乐狼的成长之…
音乐的神童往往比其他艺术领域的受世人青睐,比如莫扎特、比如《她比烟花寂寞》中的一双姐妹……当然,还有那位自称“小狼”的Patrick Wolf。6岁时前往英国学习小提琴,幼年起就跟随交响乐团欧洲巡演,11岁时开始写歌,还偷了学校一台四轨录音机器而逃出学校当起了街头艺人……这样的经历虽然比起音乐界其他天才们的童年并算不罕见,但也足以证明Patrick Wolf对于音乐的素养及天赋。
《Lycanthropy 》——色彩各异的童年幻想
专辑名:《Lycanthropy 》
风格:Folktronica ,Indie Rock ,Unclassifiable
发行时间:2003年
在第一张专辑问世前,Patrick Wolf还只是个沉溺于音乐世界的顽童,他从家里逃出来住在Richmond附近河旁的一所废弃的屋子里。玩弄着他发现的一架大键琴来消遣时日。偶然的机会,他引起了Fat Cat唱片公司的注意,并且得到了设备,开始“真正”的录制歌曲。
于是这张《Lycanthropy》更象是从小男孩向成人转变时期,充满着矛盾、懵懂和叛逆的一张作品。即使Patrick Wolf在此时真正将名字改成“Wolf”,即使他拥有着一副深沉的嗓音,但这张处女作听来还是多少有些稚嫩、粗糙,这毕竟集结他十一岁到十八岁的所有年华:海岸、城堡、灯塔,冰冷与甜蜜,灰蒙与虚幻,徘徊在流浪中的孤独、彷徨、幻想以及感伤。
正如专辑的名字“Lycanthropy”所代表的意思——可以人化为狼的巫术;变狼狂,于是听者可以在专辑中聆听到从头贯穿至尾的狼嚎声。由此看来,Patrick Wolf对于“狼”的着迷。从第一首《Prelude》的音乐响起,狼嚎声就随之而起,在电子弦乐混音中勾勒出一片阴郁景象,而到了之后的《Wolf Song》,则更理所应当的充分发挥狼嚎声了。带着自传性色彩的歌词,更多的是表现Patrick Wolf脑海中对于幼年时的记忆、对于世界的看法,当然还有性。
Patrick Wolf says:
“说来奇怪,我15岁的时候一直非常想发行一张专辑,虽然是直到19岁时才实现的,我可以说是等了很久。每天晚上写歌连轴转儿,到专辑发行了的时候的确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我首先想说的是我那时候对音乐工业完全没有概念,我想的就是:“哦,你今天发行了一张专辑,明天生活就变得美好无比!
“我那时候隶属于一个非常小的独立厂牌,他们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除了仅仅一份拷贝以外他们可能就做不了更多了。我那时有个非常好的新闻官,大家都很喜欢他,只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不得不和他分开了。我就准备了我的衣服和一些歌,你知道充满干劲的样子把所有东西打包。我那时候甚至连经纪人都没有,我就傻傻地坐在那看着窗外等手机响——当然它没有。然后我就决定做一件每每我觉得快发疯时会做的事情,就是写歌。我当时决定再写一张专辑,也就是《Wind in the Wire》,但真正发行是要一年半以后了。
“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名叫《Pigeon Song 》的歌曲,曾经我非常喜欢它,而如今却对它有些厌烦。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住在Cambrils,应该是17岁吧,那时候我天天在巡演的时候用中提琴表演,而现在我却发现用钢琴来编曲或许会我重新喜欢上这首歌。可能我对自己创作的歌曲,会有一个“沉迷—厌恶”的过程,特别是当我在巡演期间,每天晚上都必须表演同样的歌曲,会很容易时候对一首原本喜欢的歌心生厌恶。于是我试着在快要厌倦的的时候,用新的编曲来“拯救”它们,以此让我不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