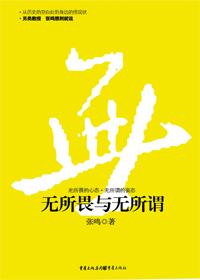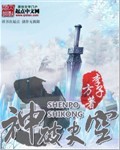从历史空白处到身边怪现状:无所畏与无所谓-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有些吃不消。拍马要讲点技巧,更要为主子排忧解难,主子不好说出口的事,要心领神会,主子不便出面的事,要悄然办在前面。只要做到这个份上,门客就大有可能被主子找机会推荐出去做官,过不了几年,自家也可以请门客了。
门客的名号在今天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门客的精气神,好像还在。总有些很有自觉性的文人,有意无意以门客自任,时常会主动地想为主子排忧解难。可惜他们认定的主子,却并不总是领情,因为门客的帮忙,经常会帮了倒忙。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自古以来,人如果作诗作得比较好,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意思。
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
反过来,建安七子,孔融诗作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起草*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
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12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作《铜鼓赋》,提笔立就。二十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骑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
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枚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被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外面来流窜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按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官的。可是,既能作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当年谢安待过,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园。从此袁枚在园子里饮酒作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职业诗人兼名士的袁枚,诗作得好,当时连高丽琉球都高价求之。除了作诗之外,他还有两件事特别有名。一件是关于美食的,袁枚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许多当时美食佳肴的做法。当时的随园,种菜养鸡养鸭还养猪和兔子,养法与众不同,加上他自己就是厨子中的高手,率领众多高厨,做出来的菜肴,自是别具一格。当时的随园,经常高朋满座,有次开筵,客人居然达500人。各处达官贵人、诗人名流,只要路经金陵,没有不去随园的。第二件是为人风趣,善解人意。到随园的人,除了可以饱口福,还可以饱耳福,随园老人(袁枚)的诙谐风趣,无人可及。《清史稿》说他,“……诙谐詄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一个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债券,一把火烧了,而且还拿出钱来帮助朋友的后人。
善于美食美言的袁枚,也会挣钱,否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银子哪里来。袁枚的官运不佳,但文名远扬,四方贵人和富人,求他给死去的爹娘写墓志铭的,不知凡几。求人例有高报酬,看在钱的份上,袁枚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你要什么,我写什么,反正最后胡乱写的,他都不收进自己的集子,只当是挣钱的买卖。
第二桩挣钱的买卖,是收弟子。中国是诗之国,虽说清朝诗有点衰,但喜欢作诗的人还是很多,加之袁枚不仅能诗,而且善绘,一手文人画,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来拜在门下者,相望于道。袁枚不仅收男弟子,还收了十三个女弟子,既教诗,也教画。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为人所诟病,男女授受不亲,但袁枚是名士,是有大才而弃官不做的名士,这种人,历朝历代都会有所优容,因此,骂归骂,皇帝却没有问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的影子里。按说,这样一个既能作诗,又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应得到赏识,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按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查,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稍微有点爱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欢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相比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材,因为庸材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在皇帝面前装点傻,才可以过得去。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在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文人之舌
文人的口舌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此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在游说得官的年代,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是得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立竿见影;其三是“忽悠”,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说话,就有风险。拍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马,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大怒:你们玩儿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
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龙须,龙颜大怒,自己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也还是得说话,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仍然比比皆是。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得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的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动静就特别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痛了雍正皇帝,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个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
花儿与皇帝
皇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凭刀枪打下来的,可是差不多像点样的皇帝都喜欢弄文作诗。刘邦当年不过一亭长,大队干部而已,斗大的字能认识几个都说不准,可是人家也有《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大抵也就是不识字的王熙凤“一夜北风紧”的水平,可是历代都夸好,说有帝王气象。不过,拿皇帝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