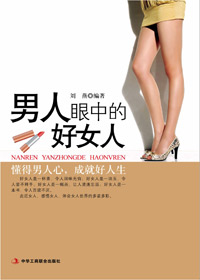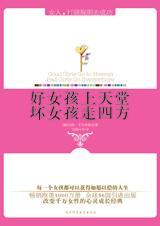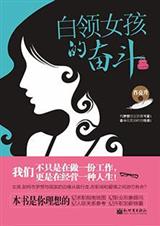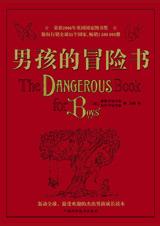好女孩的书与评-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沉重的肉身》:每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
讲故事是人类自我发现的一种方式。刘小枫说,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到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人们发现生活混乱不堪时。当一个人的生活遭遇挫折或不幸时,叙事能让人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生活中无暇发现的自我。人类的起源,似乎是从劳动开始的。但人的生活感觉,似乎是从讲故事开始的。 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讲述了叙述的伦理构想。生命的感觉来源于每一个个体的体验,因此,每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伦理探讨个体生命的意义,然后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叙事改变了生命的感觉,无论是听故事或讲故事的人,都曾经在讲述中改变事件本身的态度。于是生命感觉发生了变化,伦理产生了道德实践的力量。
阅读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仿佛踏入现化伦理学的深渊,在破碎的叙事片段中反复叩问。
萨宾娜像一个沉重的幽灵,出现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刘小枫把萨宾娜的身体暂且形容为“*玛丽昂”的再生。通往萨宾娜身体的感觉是反意识形态的。而特丽莎的身体则表征了“美好”。托马斯对生命感觉产生的疑惑,使他对两位女士的身体作出了两难选择。在电影《布拉格之春》里,托马斯像个三级片演员,把肉体的迷恋表现得丝丝入扣。但《沉重的肉身》提出了问题:身体感觉的差异来自灵魂还是身体?
没有差别的身体等于没有自己的生命时间。灵魂才使身体有超出身体局限的感受能力。托马斯与萨宾娜有相同的生理反感。在那些报纸头条所编织出来的道德理想主义言论中,他们都看到了最大的“媚俗”。
卡夫卡似乎是拒绝身体的。当他即将与菲莉斯小姐走进婚姻殿堂时,他想到的是,在夜深人静时,他是否需要跟一个女人睡在一起,还是独自一人看书。卡夫卡想通过婚姻来摆脱父亲的阴影。但他又害怕给自己带来的负罪感。摇晃在灵魂钢丝索上的卡夫卡,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对自己进行追问。是面对自己还是隐藏?对于卡夫卡来说,他追问得越多似乎就越发现自己的罪:自私、虚荣、怯懦……
结婚当然是一对男女从灵魂上互相认识,但卡夫卡对这种认识充满了绝望。刘小枫把卡夫卡的生命感觉总结为“一片秋天干枯的树叶”。这片干枯的树叶也追求过幸福的阳光,但最终还是希望以自我审判的方式重返天堂。
薇娥丽卡很幸运。她有两个身体。斯基洛夫斯基的《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中,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与巴黎的薇娥丽卡互为灵魂。为什么呢?难道生命感觉可以一分为二吗?刘小枫说,是的,一个人的生命具有各种生活的可能性,慈悲的上帝不会来过问这个身体的偶然遭遇,只对个体遭遇中的生命意味抱以关注。
薇娥丽卡从另一个薇娥丽卡身上体验到我在感。不管是热情、快乐还是死亡。当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身体死亡之时,巴黎的薇娥丽卡也感觉到了尖锐的伤心。
难道这就是死感吗?当灵魂感觉到身体之死时,当作何感受?身体与灵魂分离的薇娥丽卡总在寻找生命的感觉。她热爱唱歌,她的所有热情都是为唱歌而生的。薇娥丽卡的生命中交识着*、死感和哀歌,但没有一个人能懂得她的灵魂。
似乎总在讲故事。故事激发了每个人的生命想象空间,并探讨叙事观望到的个体生命的伦理深渊。每个人都可以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依从自己的道德自律做出生命中的各种选择。 。。
《兔八七的小时代》:我们美好的小时代
如果不是看《兔八七的小时代》,不会在心里牵动起那么多复杂的记忆。那个小兔子的编年体回忆,把我带到个人成长的氛围中。关于八零年代生人的成长环境和集体特怔,从学院派到网络都写过不少,而我也曾像模像样的在《当代文坛》里发表过一篇《谁来影响这一代人的青春》。作为同样生于八零年代的人,我觉得自己比前辈更适合描述一些自己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影响。虽然我也不喜欢用一个“代”就笼统地把一群人的个性都打发了。
跟小兔子一样,小时候我最喜欢看动画片,最讨厌上幼儿园。亚运会那年我收集了一块印有熊猫盼盼的三角旗,这块旗子至今仍蜷缩在我床底的玩具箱里。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们家在吃晚饭的时候总是在看《新闻联播》,可我当时不知道叶利钦是谁,因为我不关心政治——到现在还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曾叫我们每个人都摊开手板,看我们的尾指是否长到无名指第二截的位置,尾指够长的到文化馆考试学二胡。当时我们几个有幸选上的战战兢兢到二胡老师的教室考乐理、视唱。没有乐感的我就在这时候被刷了下来。当时我伯父跟我说,他认识二胡老师,只要跟老师说一声,就能让我去学。但是对二胡兴趣不大的我就此放弃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学书法和国画,以后坚持了一段时间,断断续续,虽然没有老师教,可是有空余时间会自己练。国画学了一个学期就得了一个县里的小奖,这让我感到很骄傲。可惜后来再获过什么大奖。我仅有的一点艺术细胞没有发育成熟。等到我有机会走出小县城,到了大城市之后,才发现像我这种小时候看起来比较聪明的孩子实在太多了。
1995年我上初中二年级,开始看琼瑶、岑凯伦的言情小说。《同桌的你》堂而皇之的在校园广播站里翻来覆去地放。上语文课时,语文老师说鲁迅的散文代表作是《朝花夕拾》,同学就异口同声接“杯中酒”。那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坛最辉煌的时代,那首电台点播率最高的《祝你平安》,至今仍像魔音一样不时在我脑海中萦绕。
考完中考的第二天就是香港回归。跟兔子的感觉一样,整个仪式的感觉就是“中国解放军的正步太帅了,而英国兵走起路来和狗熊有一拼。”《兔时代》用活泼可亲的方式让我回忆起一九九七年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去世、香港回归、金融风暴、男足甲A热潮、戴安娜遇难、王小波去世。就是从那时候起,王小波的作品如同圣经一样摆在各大书店的显要位置。这个人的作品影响了我一辈子,从此以后每年的四月我都特别伤感。
跟60、70年代的人相比,80年代生人的成长期似乎特别长。人生中大部分美好的时光都是在校园上度过的。1998、1999年我的记忆是趴在课桌上做永远做不完的习题。“高考”是人生中绕不开的词。与此同时,一个叫“娱乐圈”的名词渐渐在兴起。不管是四大天王还是“情歌王子”,“天后”“*掌门人”,港台文化让人看到了时尚,也发展了八卦。食堂的大娘每天一边给学生打饭,一边谈论《妙手仁心》的剧情。而我们则经常围绕在哪个女明星红得没道理之类的问题上。很多女生都梦想着将来可以做一个像剧里那样的白领丽人。
2000年以后,有关80后的恐慌开始浮上水面。因为互联网时代到来了。先是上聊天室,论坛,然后是QQ,网络日记。这新兴事物把长者与我们拉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不会上网的前者眼睁睁看着我们用网上搜索,在三秒钟内找到几十万条相关词条,并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跟千里之万的陌生人聊得不亦乐乎。网吧在一夜之间花开大地,见网友成为一种时尚。从最初的纯粹娱乐,到用电脑写作、办公,电脑逐渐成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我曾试图与比我小近十岁的表妹沟通,但她看起来似乎对于我所津津乐道的过往经验嗤之以鼻。从私人经验出发的叙述只能归还于每一个人。《兔时代》让人感兴趣的不是一个天才少女的成名之路,而是从幽默的小故事里铺出的一条回忆之路。这条回忆之路风光依稀相识,让我走在上面踏实又亲切。每个人都有关于自己成长年代的回忆,每一天我们都在感受着时代进程对于我们的影响。尽管这影响潜移默化,不能轻易察觉。今天,那些生于八零年代的小屁孩,已经长成这社会的中流砥柱,不管如何评价,他们都已络绎进入社会,为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寻找一席之地。隔着厚重的时间回望,任何回忆都变得可爱美好。当撕裂了成长的疼痛,把回忆当作与时代握手言和的重要仪式时,那些属于个人的幸福与美好,便挟着时代的名义汹涌而来。 。。
《致一九七五》:寻找历史深处的舞蹈
《致一九七五》:寻找历史深处的舞蹈
用女性主义的眼光看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可能变得尖酸刻薄。林白在她的新作《致一九七五》中,沿袭了她一贯高扬女性意识,书写女性经验的做法。但这一次,林白把观察历史的重任放在了一个十七岁少女李飘扬身上。从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女眼中看去,历史显得那么饱满、张扬、有力。 小说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回忆体散文,下部分是写实录。上部《时光》被戏称为“史上最长的前言”,小说通过少女李飘扬的追忆,构造出一个虚实相间的南方小镇。在略带感伤的情绪化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学校、工厂、医院……独特的七十年代社会场景随作者的思维情绪任意转换,在看似零散的回忆中完整地构造出一个存在于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小镇面貌。作者的叙述时而欣喜,时而感伤,吃红茶菌、打鸡血针的荒诞场面与伙伴间的友谊驳杂交错,共同构成南方温热空气下的政治气候。童年伙伴姚红果、雷朵、张英树……以各自活泼的形态出现在回忆者的讲述中,他们独特的性格、作派在那个特定时代相映成趣,在时间的长河里编织成一代人的悲喜命运。李飘扬的成长身陷于历史的宏大革命话语中,看似喋喋不休的回忆事实上充满了反思、追问和自我寻找的色彩。
小说下半部分主要描写李飘扬作为知青下乡的所见所闻。叙述由虚转实,但仍然不能构成条清理晰的故事。作者跳跃的思维继续在乡村游走。她看到了安凤美、猪精、政治粪屋……在乡村朴实而愚昧的空气下暗含着嘲讽、反抗、渴望,少女青春期冲动、叛逆和富于幻想与狂躁的政治气候不谋而合。思想仿佛不受控制般左右冲突,幻想天马行空。大量穿插于叙述中的幻想使小说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它看似贴近历史,又似乎在历史中游离。语言的飞翔感是林白小说的特点。这一次,她再次充分运用广西北流本地俚语,将原生态语言与革命叙事相结合,制造出一种独特的语言效果。从少女经验出发,最终又回归于少女经验,少女情怀、南方俚语与革命叙事,共同混杂成于一九七五年独特的人文景观。
《致一九七五》不是政治文本,也不是“*”题材,但它为我们找到一条通往回忆与自省的道路。写作为林白寻找到从生命出发的体验,并最终将这种写作体会向每一个人传达。个人生命与时代洪流总会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不管是自我认识或自我消解,都表明了我们与历史相处的一种态度。《致一九七五》提醒我们如何在历史中发现自我。每个人都活在历史中,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