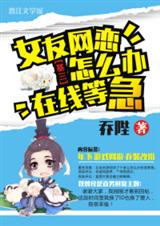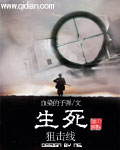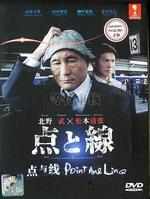地平线-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在基层官兵中引起不小的反响,拥毛者大有人在。毕竟,这支部队是他带上井冈山,又转战闽赣边界带到闽西来的。然而,复出的毛泽东却以他那独有的政治坚忍态度引而不发,每日忙于找人谈话搞调查,红四军那些军政领导人物都像飞蛾扑灯一样,围着他团团转,似乎在酝酿着什么。柳达夫稍稍安心的是,看来毛泽东顾不上立刻清算那些反对过他的同志,也许是时辰不到?平静的等待中,本身就蕴藏着一场即将来临的大风暴。进入12月以后,国民党与军阀之间的战事再次平静,广东、江西方面的敌军又频频调动兵力,准备“围剿”闽西红四军。这种时候,柳达夫的心情怎么能好得了?当他得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他立刻就萌生了去意,早些离开红四军,回上海去,在中央工作,远离毛泽东、朱德和陈毅这些人,那将会使他更加心平气和。他的优势与其说在上海,不如说在中央。与毛泽东相比,柳达夫当然更愿意与周恩来这样的人一道工作。
剩下唯一的念头:如果离开闽西,他想带走罗翠香。
相识不到一年的时间,也是他来红四军这年把光景,他唯一的成就感,就体现在这个闽西女孩的身上了。是他,一手将那个黑色上帝的女儿,脱胎改造成为初步具有革命品质的赤军女战士。如果再假以时日,他相信罗翠香将会变得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作为中央特派员,他在红四军的使命失败了,他得承认他改变不了朱、毛那些人,改变不了红四军,可他最终还是成功地将玛丽亚改造成为了罗翠香。
罗翠香——也就是玛丽亚,本身就像红四军一样,是个复杂的综合体,她那不同风格的两个名字或许就是个佐证。你说她是个村姑吧,她生长在水旱码头汀州县城,算得上半个省城了,又在学校受过教育,还在教堂中做过事,特别是在福音医院当护士这些年,耳濡目染,接触的西式文化远非一个普通乡姑所能企及。她喜欢喝咖啡,知道吃西餐时左手拿刀右手拿叉,还知道叉尖不能朝上,必须朝下。她还会几句带有客家口音的英语,甚至还认得几个拉丁文单词。你说她算得上淑女吧,她不过是出自于县城裁缝之家,不认得*的画像不说,甚至不知道列宁是哪国人。说她是上帝的女儿,未免言过其实了。把复杂的玛丽亚掰碎了杂糅之后的重新分派,注入了一些红色的元素之后,她就变回了罗翠香。不过,柳达夫也得承认,他随红四军来闽西快一年的时间,多数时间并不开心,长长的日子像山藤一样缠得他喘不过气、翻不过身来,他那脆弱的心灵像幼儿一样需要抚慰。也就是说,罗翠香给予他的,可能和他给予罗翠香的一样多。柳达夫早就看出了罗翠香对他的深深爱慕之意,说实话,有时他觉得这女孩挺可怜的。那种爱是有些非分之想,但还算不得罪过,就她的出身和共产革命的理论素养来说,爱是永远无罪的,这也正是她尚需要改造的地方。换到他自己身上,那就不行了。一个职业革命党人,怎么可能在事业未竟之日谈情说爱呢?更何况,这当中还夹了一个兵痞子丁泗流。不过,这又有什么呢?*主义者用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耶稣和他的信徒之间,不还夹杂着一个犹大?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之间,也还有个托洛斯基嘛。。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十三 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和革命式的爱情(2)
丁泗流那个丘八一而再、再而三地出事,已经被从连长撤成了排长,这让柳达夫觉得好笑。就是这样一个傻丘八,怎么会让罗翠香这样的女孩儿多看几眼呢?真是打死他也想不通。从本质上说,改造尚未完成的罗翠香还是半个玛丽亚,这一点毫无疑问。尽管柳达夫的造就计划苦心孤诣,也初见成效,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将玛丽亚打造成罗翠香,她不过将玛丽亚的名字换成了罗翠香,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酒。这样的判断是残酷的,也常令柳达夫沮丧。现在,他将离开闽西红四军,那个改造了一半的罗翠香或者说是玛丽亚怎么办呢?将她丢在这山沟沟里,任其蜕化,重新变回玛丽亚吗?那岂不是半途而废?想到他唯一的那点成就感将要扔在原地,柳达夫的心就像被子弹撕裂开一样疼痛。那样一来,他还剩下什么呢?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柳达夫一次患上了重度流感,被医生怀疑为伤寒,转送到一座乡村疗养院隔离观察。那是一个风光秀美的乡村,木制的板房和后建的黄砖红顶的小楼错落有致构成了一个村落,紧傍着村子的就是一条小河,冬天的日子,河水封冻,小心翼翼地越过河面就能走进一片白桦林中,阳光下,积雪像一只只硕大的松蘑,挺立的白桦树简直就像一群俄罗斯男人一般骄傲。若是那些密密层层看不透的白桦林,倒也令人思维单一,偏偏走到近处,总能看到几棵倒下的白桦树,恰恰是那些倒下的白桦树横着的树干,与那些笔直挺立的白桦树形成视觉上的交叉,令人顿生感慨,感悟到生命的脆弱与不朽。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缜密的观察,很快被排除了伤寒可能性的柳达夫痊愈了,可他并不急于返回莫斯科,他喜欢上了这个乡村疗养院,喜欢上了那个负责护理他的俄国女孩。她叫玛丽亚,就是本村人,父母原来打猎、种地、捕鱼,什么都干,却很难说是农民还是渔民,抑或是猎人。莫斯科当局在村里建起了疗养院,村里很多人都为疗养院服务,冬天的路面冰封雪盖,汽车无法进出,玛丽亚的父亲就和村里其他男人驾起雪橇,为疗养院拉给养,包括运送病号。
现在想起来,事情就像距离和时间那般遥远。当坐着摇摇晃晃的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的秋天,通过*设在满洲里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回到中国境内时,柳达夫差不多就把那个俄罗斯乡村的玛丽亚忘掉了一半。当然,这和中国革命的事业有关,与有着严格自省自律精神,并时刻以职业革命家自诩的柳达夫有关。学成归国的柳达夫,和其他中国同学一样,满肚子不仅装满了俄式“列巴”,那是一种俄国式大面包的叫法,还装满了俄国同志传授的布尔什维克理论,装满了*列宁主义的光辉。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前景满怀憧憬,并对各自在中国革命中将要担当的大任深信不疑。赤化中国,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全面布尔什维克化,他们人人心中充满了舍我其谁的凛然大气。当柳达夫辗转来到上海中央报到时,苏联乡村玛丽亚的模样他都已经差不多全忘光了。来到闽西,他在汀州遇到玛丽亚也就是罗翠香后,那个千万里之外的俄罗斯女孩的音容笑貌才重新回到他脑海里。后来,为了有所区别,他把俄国的玛丽亚称为“俄玛”,他宁肯把两个姑娘搞混了,再努力甄别出来,也不愿意将两个玛丽亚混为一谈。当然,罗翠香这个名字他还是蛮喜欢的,充满了乡土气息,有种乡间小诗的韵味。还有,“俄玛”要比闽西玛丽亚丰满得多,那姑娘的性格更像冬天中熊熊燃烧的火炉。病房里到处都是用汽油桶改制的火炉,里面堆积着秋天备下的桦木柈子,死于冬天前的桦树在寒冷的冬天里造出了温暖的春天。玛丽亚的脸膛被炉火烤得通红,积淀着某种成熟后的自信,一次又一次的,忘记柳达夫都说了句什么,玛丽亚高兴地哈哈大笑,一头亚麻色的长发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她那双湖蓝色的瞳子,就像冬夜雪地泛出的光泽,令柳达夫心猿意马。那个玛丽亚多大岁数来?十八还是十九?和这个玛丽亚也就是罗翠香差不多吧,但“俄玛”更像一匹奔放的俄国马,到了荒野中撒起欢来跑得惊天动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十三 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和革命式的爱情(3)
离开疗养院那个最后的夜晚,玛丽亚来到柳达夫的病房,她沉默得像被人灌了哑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拼命朝炉内填着桦木柈子,铁皮桶壁烧得通红,似乎马上就要融化成水了。柳达夫拿起一根柴棒,轻轻在桶壁上一划,一串猩红色的火星犹如理性的光芒闪烁而过,并且很快消失了。房间内空气焦躁,热得人穿不住衣服。玛丽亚早把她的皮衣脱了,后来还是抗不住热,又把她那件蔷薇色的毛衣也脱了。她那天穿了件丝质的胸衣,香槟色的,在红色的炉火照耀下有种粉色的质感。玛丽亚对中国男人柳达夫抱有好感,在疗养院几乎人所共知。除了冒着严寒,带他跨越冰河,进入白桦林之外,她还曾把他带到家里,品尝玛丽亚父亲自酿的烧酒,还有她母亲最拿手的酱鹅肝、熏牛肉、熏鱼干。玛丽亚和她的父母不在乎这个中国男人是干什么的,是职业革命家还是搞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在苏维埃政权中比比皆是,他们喜欢的是中国男人那种几分腼腆、含蓄,就连喝酒也是小口抿,不像俄国男人那样牛饮一气。柳达夫的俄语口音很轻,像春天开冻的河水一样潺潺流淌,他的言行举止一切都是那样东方化,那样智慧,那样典雅,看上去就像文学中的中国皇帝的侍从一样规矩,这让他们处处感到惊讶和新奇。
在那个火炉被烧得就要爆裂之前,玛丽亚终于开口了。
“柳,留下来吧,我可以嫁给你。”她轻轻地说。
柳达夫没有回答,他甚至弄不清玛丽亚是让他留在这个乡村还是留在莫斯科。他又用木棒划了一下烧得通红的炉壁,又一串火星闪烁而过,犹如一队红军士兵军帽上的红五星。
见他不开口,玛丽亚几分失望,她扔掉手上的一块桦木柈子,一把将柳达夫的头抱在胸前。柳达夫像失去知觉一样一动不动,他怀疑回到了儿时的梦境。玛丽亚那对猫一般的乳房挤压得他喘不上气来。他想,就这样昏厥吧,就这样死去吧,他仿佛一不小心堕入了普希金的诗行,或者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要么就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之中……
在莫斯科校园里,他们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常在周末的舞会上受到苏联女同学的热情邀请,那时柳达夫的感觉是跋涉在托尔斯泰的华丽的波斯地毯上,相比之下,屠格涅夫来得更真实些,似乎伸手可触。面对着亲密的肉体接触,感觉上像被另一个烧得通红的汽油桶拥抱着,柳达夫当然不敢伸手。他知道,只要他的手一伸出去,他就等于把自己的什么都伸了出去,摸一摸那对发烫的乳房,甚至摸一摸玛丽亚那火热的脸颊,就像木棒擦刮炉壁一样,将划出一串燃烧的火星。在这个远离莫斯科的乡村,在这个风雪之夜,他几乎可以不考虑道德的约束,但他不能不考虑党的纪律。俄国“二月党人”在流放西伯利亚时,面对的就是恶劣的天气和温情的女人。他这位中国布尔什维克的中坚分子,难道能轻易被一炉烈火烧化了吗?
那一晚,柳达夫既没昏厥,也没死去。他活着走出了那片冰天雪地。
他还是柳达夫,而不曾变成了别的什么人。
这一点,至今还令他骄傲。
主义的光辉,真是无可匹敌啊!
还记得的是,“俄玛”的舞跳得极好,歌也唱得棒极了。这一点,闽西的玛丽亚与她极为相似,尽管她们唱的歌词不同,却都是充满乡村情韵的农家小调。有几次,柳达夫与罗翠香携手钻进密密的竹林,或者草木葳蕤的青山小径,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与“俄玛”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