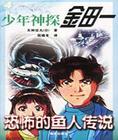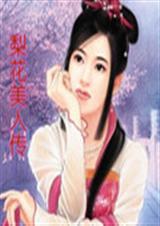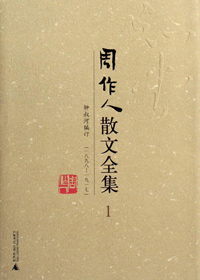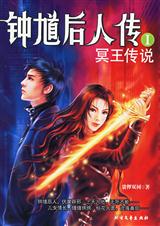�����˴�-��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³Ѹ�������뿪�ձ��������ձ������⣬�����ֳ���Щ�ֱ𡣽��������ձ��Ĺ�ϵ�����ʱ��ʵ���ؼ���³Ѹ�ߺ�����������ѧϰ���ġ���������ѧ�IJ������鱾�ϵ��ձ��ģ�������ʵ����������ŵ������ˣ���������������ִ���С˵��Ϸ�磬���ⷶΧ�ܴ����ô��������ֺã����Ծ���ֻ��ڶг��������������ѧ�ϱ����ǡ����ԡ��͡��������������ķ�����Ǵ�����һ�ֶ�ʫ�����������������ʱ������ѧ�������й�ʱ�ڣ�ȥ���Լ���İ����ˣ������뻬������Ȼ�ǽ����Ľ���ʱ��������������Ҳ���Ƕ�����ǰ���ҵĶ������������ԴҲԼ������ʱ��������Щ�ο������ϣ�����������������ҵ��������ȥ�ˡ����������ڻ��������ţ�����������ˣ����ÿ�����ţ��뽲̸����ͬ�������˻�ӭ���ִ�����������������ĺܺ����ϣ�����������ϯ��ȥ����������ҵ�һ�����֣�Ҳ����˵ѧУ�Ĵ��ã���Ϊ����������Է��İ����Ǻܴ�ġ�����164�����Ӵ���Ϊ����ʫ���Կ��Գ�Ϊ�����ĸ�����Ҳ��ϲ��������ǰ�ߡ���ʱ�����е������İ�����ں�����ǿ��������߳���һĨ��Ӱ��������������Ȼ֮�С�165������ע�����ձ�������ص������������������顣�����Ժ������ᵽ�Լ������ձ��Ĵ������ر��ǡ�ĩժ�����ı࣬�õ������Ӱ�족166����ʱ����ʼ����������е��˵������о�������Ҳ�ǡ������ڹ�����������167���ر����ڽ̷��棬���������˽��ձ������顣һ��һ����ʮ���£����Ϸ�Ǩ���鲼ɭԪ����ӽӽ��ձ���ͨ�˵������������ǻ������ȵij˿ͣ�����ʲô����������ʹ��к���Ҳ����̸����������Щ�о�����������£�Ҳ�ͻ��˽�������168�Ժ�������˵���䡰��ѧ������ִ�������������֪�ķ��棬���ձ�����������ķ���Ϊ�ࡱ169��ֻ��ͨ�������ⷬ�Ķ���������ŵ������뵽���顱�IJ���ȥ�����ձ��Ļ�������ת��Ϊ�Լ����Ļ����ɣ��������������������ԡ��������������봨������Ϊ�Աȵ�һ�������й�����ѧ�������϶�ȱ�ٻ������ӣ����ǽ���������������α��ѧ�����µIJ���죡���170��������˶����ձ���ѧ�����ر����Ȥ�㣬�������롶����ѡ�������������á��͡����������ݡ��ȣ���Ϊ�ⷽ�����Ҫ�ɹ���
�����˴������ڶ��¡���һ�š�����11��
���������Գ��ȴ������С�Ҫ�˽��ձ�������ֻ����ѧ��Ҫ��Ҳ������������֮���������������ֵĻ����ձ�������֮����ֻ�Ǹ���Ȥζ���ѡ��������ʾ��ͬ171���������ϸ��˾���������أ���Ϊ��Ϊ���ߣ��������ձ�������ѧ�ļ�֤�ˣ���������������ʮ��ǰ����ѧ�������ˣ���������ʱ����ѧ����ر�е�һ�����뻳��������ַ��棬��������Ҫ��Ҳ��ֻ������̳�ļ�λ�������ԡ����ǵǼ��١�����Ի�ž飩Ϊ���ݵ���Ŀ��ʯ���߱����ӣ����絾����ѧ����ƺ����ң�����屧�£������ǡ������ٲ���������Ի���ǣ�����������ѧ����ɭŸ�⣬�������������ɷ磬��лҰ����λ��������ʮ���ʱ��ҴҵĹ�ȥ�������Ѻ�ʱ��������𣬸�������⻪���������ڸǣ����������Լ�ȴ�ܾ�������ʱ�����Ӵ��������������Щ����־Ҳ�·���ʱ��������ã�����Ȼδ���е�����ƾɣ���Ҳ������֮���ɡ���172����˵�����˶��ձ�����Ȥ��ʼ�������Լ�����������������������ر�ǿ����ʱ�ձ���δ��������������һ��������������ѧ֮�С����������౾��Ȫ�ӷ�ӳ����ͯ���������η��ס�173�ġ����μǡ����������礷����������ģ�Ҳ�Ǽ���ij�ֻ���֮�顣����������ѧ����������������ȡ�ᡣ�����ձ��ڼ䣬��Ȼ�����˶��������ϣ���Ŀ��ʯ��ɭŸ�����Ϊ�����������˵Ŀ�ζ����ƫ���ں�һ���棬��ϲ�������Ҿ�������Ȼ������ѧ��Ӫ������³Ѹ�dz��ӽ�����Ҳ˵�����ǵõ�ʱ��������ߣ������ձ��ģ�����Ŀ��ʯ��ɭŸ�⡣����174�պ��ֵܶ��˺��롶�ִ��ձ�С˵�������ͽ���Ȼ����֮���ų����⡣���ƺ�������ij������������ѧ�����ijɾ��俴�أ�ͬʱ��Ҫ�����ܹ������������ձ顢���߸����ԵĶ������������뿪�ձ�֮ǰ��Ψ���ɵĹ�����һ�ɣ������ɵ�����С·ʵ�ơ�־��ֱ�ա��е����ɣ��Լ�ʯ����ľ����½���dz���Ҳ��Ϊ������ע������С·ʵ���Ժ����˼���ϵ�Ӱ����Ϊ������
����³Ѹ�ߺ�������ֻ��һ��һ����ݵ����أ�Beatrice��Danford��175��Ӣ�뱾ת����һ������Ħ������ƪС˵����Ǿޱ����A��S��rga��R��zsa���������ɼ����Բ����������������δ�߳�������С˵����ʧ�ܵ���Ӱ������Ҳȱ��³Ѹ���ٵ�Ե�ʡ���ǰ���������������£����������ʱ��������裬ס����������³Ѹ�����ˣ��������һ����ϯ�ķ�������Ƶúܣ������������������³Ѹ�����ͻ�����ϴߴ������飬��ȴֻ�dz�Ĭ�������Դ�����һ������Ȼ������������������ȭ������ͷ�ϴ��ϼ��£���������ƅ����Ȱ���ˡ���176���ڴ�粻�����ߣ�����������Լ���˵�ġ��ζ�����177��txt���������ƽ̨��
�����˴������ڶ��¡���һ�š�����12��
����Ǿޱ��ϵ����Ħ��һ###��������������С˵������ԭ���ܳ�����Ӣ���߽��������ƪ��178���뱾�������ƻ�����������˵����������С˵���������٣��˶�ȡ���ߣ��ж����ɣ�һ���˹��ԣ�һ�������ԡ��������������������飬�Ƽ���ɫ������˼��������Ȼ��ʫȤ��������Ե�����ơ��ƻ���һ�飬Ϊ���������������ϣ����ʫ��֮�飬�ذ����ټ�����������Ҳ����179��ν�����˹��ʡ����Կɹ�ᵽ���ܡ���С������ѧ����һ�����������������ԡ�����Ϊ��������ǿ��������С˵��д������������ʫƪһ�㡣�ɴ��黹����������ϣ������ʫ�����п��ж�˼����С˵�����ʸ�˼��Longos��180�������йط�������Ľ��ܣ��������������µ���Ȥ���ڡ��Ժ�����ֱ��������С�����λ����Ʒ������������˵������Ǿޱ������һ���������ѡ���С������ѧ�����ϣ����ϵ�������������롶������ʷ�����������Ƴ������С˵��ϣ������ϵ����һ����������ɣ��þ�δ��������Ҳ������ȡ������С˵����һ·�뷨��С˵�����ֲ������ȡʤ��Ե�ʡ�ֱ��һ�Ŷ����꣬���в�Ԫ������ʮԪ��������ӡ��ݣ��ֹ������꣬������档
�����������Ⱦ��ձ����Ըù������������ģ�Ȼ��һ��һ�����ձ�������ıɱ������������ҵ���ˮ���˵ġ������¼�����ȴ������һ���ܴ�Ĵ̼�������Ϊ����ص��´��ѳ������εķ�Χ����ͳ��˵�����漰�˵��������ˡ���181��������˵�������ձ���ʱά�µķ���Ҳ�����֣����Դ��永Ϊһת�۵㡣��182�����Ҳ����������ʶ�ձ���ת�۵㡣̸���ձ��������������������߶����������ߣ���һ̬�ȴ�Լ����ʼ�ڴˣ���ȻдΪ���£����ڶ����Ժ��ڵ�ʱ�����������ȴ���й������顣һ�ũ������Ϊ��̿����д��С�����ƣ���������ޣ�����������һ����ƣ���֮���磬��ũŮ���Բ��⣬��Ϊ֮����Ϊ֮�����������ԣ��������������������̾Ϣ���֮���ߣ���ƽ����Ҳ����������ͷ��֮�£�������Լ��ӡ�����ϵ��Գ�͢��ʱ����ļ����ܶ�����ּ���������������й��Ĵ����αض���һ����ͷ�����ɡ�183�����ֲ�Ϊ�������ζ�ֱ�ﱾ�ʵ��۹⣬�ú��ۼ�ʱ�£������������֡�һ��һ�������¶�ʮ���ա����˹��������صġ�����֮������һ�����ƣ��������й�����������������ͼ��ǿ��ʹ��²����������ǻۣ�������֮�����Ѵ���������֮ѧ�������ۣ����������к����ʸ����ϰ��ʩ�Խ�����ʹ������Ȥζ���Խ��������ǣ��Ǽ���ĩ��ʵΪ����֮����Ҳ�������ŵ�����³ѸͬΪ�����ϡ�������졣���Ϸ�������ƪ����ϣ��֮С˵��184���ֱ��ʸ�˼����Ʒ��·����ŵ˹�ġ���ʷ����Al��th��n��Di��g��mat��n��185�������йع�ϣ����ѧ����Ľ������¡���һ�����������Ϊ�����˹������������Ҷ�Ȼ��������ϣ����������Ephtaliotis������ʲŵ˼����186��
����һ��һһ����������˼����������̴�ѧ�Ĺ�ϣ����ѧҵ��������ѧһ�������δ��ʵ�֡���³Ѹͬ�����������ڸ������ѵ�����˵�����������飬ν������ϰ���ģ����⼴��֮����Ե���IJ��ܱ�����Ҳ����������ʱ���о�����ʵ������֧�������˼�����ѧ������³Ѹ���ɣ����䷵������Լ�����µ�ǰ��������Я���ص����˼���187����������ǰ��С������Ԥ�Եģ��ʹ�����Ȼ����һ�����Ρ���������������ר�����ص�ѹ���£�����������ܡ�188������������дʫһ�ף��㷢���ڽ����������������Ļ���֮�飺��Զ�β�˼�飬�ÿ������硣�ż��������˥��ͽ�Իơ����β��ɵ��������İ���
������������������뿴����
�����˴����������¡���һ��һһ��1��
�����˻ع����ã�������������������������������������ع�˵�����ڵ�ʱ������ǰҹ�����Dz�û�м��籩���ǰ�ף��������ľ������Ǻ��ձ飬���֪���籩������ȴ���ϻᵽ������������ˡ���189�������Լ���δͶ�����У������������һص����ˣ�һֱ���ڼ���������Ÿ����������¼���Ҳû�г�ȥ��������190��Ȼ��ʱ���������´�Լֻ��ÿ�ճ��飬���ǰ�ͬ³Ѹ�����������飬��¼����С˵�������͡�����������Ӽ����IJ��ϣ�������������������ġ�����¼��֮�ࡱ191����ȴδʼ�����ģ���˼�����������º��������õġ�Խ���ձ�����������������ƪ���£������ⳡ��������������⡣����������һ���������ĵ�һ���ش������¼�����Ҳ��һ�α��ֳ�һ��˼���ߵ���̬��
�����������ڡ���Խƪ��192�п����й�����ʷ����ʵ��ָ��Ҫ�����ڡ���ҵ����������֮��һ������֮����������ҵΪ������������ҵ�ߣ����ڹ����͵£�����ϰ��������������������֮�����£������˳ɣ����ڳ���ǧ�꣬�����������ꡣ������һ����˼����ͨ����Ϊ���⣬����ʥ�ߣ�Ī��һ�ǡ��������ҵ���������ǣ��������ˣ��������ˣ��������ߡ���������Ϊ��֮�࣬��Ϊʱ֮��������Ȩ���������������Ѫط�ߣ��ಢϮ����飬�������ܣ�Ī�����⣬Ψ��������ҵ�����������Ϊ��Ϊ���������Ŵ�֮��η��������Ҳ�������ʹ�ȷ�����Լ��ķ���ʼ������й��ġ���ҵ���༴�Ŵ���Ϯ�Ĺ����Լ������У����ڵ�ʱ������������������ڴ���������ǧ��һʱ�����ʼ֮�ʣ��費֪����֮������ϴ�ĵ��ǣ���Ȥ�����������Խ�����������������»λ�����ڴ��ڱˣ���Ϊ��֮�����������ִӸ����Ͻ�������Ҫ��ʵΪ����������˼�������֮ǰ�࣬�����ݵ�����ǰ�ġ���̿����С�������Լ�������³Ѹһ��Ϊ�����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