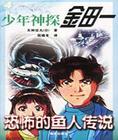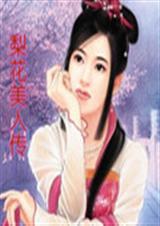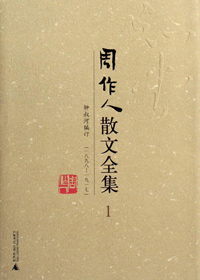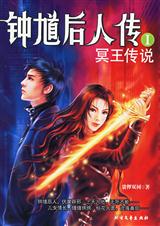周作人传-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九二二年十月,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梁实秋登门拜访周作人。多年以后,梁氏回忆说:“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406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24)
六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周作人发表《妇女运动与常识》407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人的文学》中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从前他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已有“反求诸己”之意;现在或以“讲人道,爱人类”未免虚幻,而“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实在得多,所以就来切实解答这一问题:“我相信必须个人对于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Thales)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Gn?thi seauton),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我所主张的常识,便即是使人们‘知道你自己’的工具。”“知道你自己”乃是“回到根本”;强调此点,正是周作人的独到之处。他所列举的“常识”包括:“第一组的知识以个人本身为主,分身心两部;生理又应注重性的知识”,“第二组是关于生物及人类全体的知识”,“第三组是关于天然现象的知识,第四组是科学的基本知识。”以上四组,“他们的用处是在于使我们了解本身及与本身有关的一切自然界的现象,人类过来的思想行为的形迹,随后凭了独立的判断去造成自己的意见,这是科学常识所能够在理智上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好处了”,“第五组特别成为一部,是艺术一类,他们的好处完全是感情上的”。这里所说,既是周作人有关“人”的理解,又是他对自己的总结。他的全部思想,即以上述“正当的人生的常识”为基础。
不久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开辟一个新的专栏,题为“绿洲”,皆为读书之作。较之此前的“自己的园地”,这组文章更接近后来所谓“周作人小品”——或者说,真正的周作人风格,是从这个专栏开始酝酿的。其中《猥亵论》408介绍道:“蔼理斯(Havelock Ellis)是现代英国的有名的善种学及性的心理学者,又是文明批评家。”自此周作人便与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以至有“中国蔼理斯”之称。周作人对蔼理斯的评价:“他的好处,在能贯通艺术与科学两者而融和之,所以理解一切,没有偏倚之弊。”使人联想到《妇女运动与常识》中对于艺术科学两类常识的强调;他从这时开始把蔼理斯引为知己,似非偶然。两氏最大的相同之处,正在总是基于常识发表意见。几个月后周氏又在《文艺与道德》409中讲到蔼理斯,他自己也将成为这样的人:“他毫无那些专门‘批评家’的成见与气焰,不专在琐屑的地方吹求,——却纯从大处着眼,用了广大的心与致密的脑估量一切,其结果便能说出一番公平话来,与‘批评家’之群所说的迥不相同,这不仅因为他能同时理解科学与艺术,实在是由于精神宽博的缘故。”周作人最看重的还是蔼理斯关于性心理的意见,上述两篇文章均涉及这一问题。以后他说:“性的心理给予我们许多事实与理论,这在别的性学大家如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特威耳特诸人的书里也可以得到,可是那从明净的观照里出来的意见与论断,却不是别处所有,我所特别心服者就在于此。”410蔼理斯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让周作人深感契合,求之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25)
这里又要讲到两件事情。爱罗先珂末次来华期间,发生了“剧评事件”。先是爱罗先珂对北京大学学生的演剧有所批评,由鲁迅译出,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在《晨报副刊》刊出;不久魏建功发表《不敢盲从》,文中“看”字又特加引号,对于失明的爱罗先珂显有侮辱之意。鲁迅遂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袭用爱罗先珂的话回击道:“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411周作人也在一月十六日和十七日发表了《见了〈不敢盲从〉的感想》、《爱罗先珂君的失明》,态度不似鲁迅激烈,意见则完全一致。“事情是这样下去了,但是第二年的正月里,他往上海旅行的时候,不知什么报上说他因为剧评事件,被北大学生撵走了。到了四月他提前回国去了,什么原因别人没有知道,总之是他觉得中国与他无缘吧,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被撵走了,也未始不可。”412四月十七日,即爱氏离京次日,周作人作《再送爱罗先珂君》,多有感慨:“他的去留,在现在的青年或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413嗣后又以《出京后的爱罗先珂》为题发表友人来信,显见未能忘怀。然而去者自此再无消息。——直到一九###年,周作人才由日文杂志得知,爱罗先珂“于五二年十二月在故乡死去,现在俄文全集已出云”414。
有阮真者,撰文声言决意与妻子离婚,并自称是此一关系中的牺牲,引发一些议论。周作人三月二十九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关于谁是牺牲的问题》,四月二十五日发表《离婚与结婚》,而阮真也写了《答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回答说:“我并不非难(而且可以说是赞成)他们的离婚,但也决不能赞许他凭倚旧道德的那种态度。”415在“绿洲”的一篇《〈结婚的爱〉》416中,又说:“我很怕那些大言破坏一切而自己不知负责,加害与人的,所谓自由恋爱家的男子。”此文系介绍斯妥布思(Marie Stopes)417的同名著作,所述斯氏“两性关系应该是女子本位”的主张,最能代表周作人自己有关这一问题的是非标准,尤其体现在以后他对两个兄弟婚姻问题的态度上。《晨报副刊》继而又有因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而引起的“爱情定则讨论”,参与者中,“大多数的道学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为物,不是玩具便是偶像,决不当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是以周作人说:“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褊隘,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418
周作人所作《“重来”》419一文,可以视为有关“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深刻思考:“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说遗传的可怕,名叫《重来》(Gengangere),意思就是僵尸,因为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出现。……若譬喻的说来,我们可以说凡有偶像破坏的精神者都不是‘重来’。老人当然是‘原来’了,他们的僵尸似的行动虽然也是骇人,总可算是当然的,不必再少见多怪的去说他们,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重来’,如阿思华特一样,那么这就成了世界的悲剧了。我不曾说中国青年多如阿思华特那样的喝酒弄女人以至发疯,这自然是不会有的,但我知道有许多青年‘代表旧礼教说话’,实在是一样的可悲的事情。所差者:阿思华特知道他自己的不幸,预备病发时吞下吗啡,而我们的正自忻幸其得为一个‘重来’。”这与前一年发表的《思想界的倾向》一样,在周作人的思想进程中都是不容忽略的环节;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所说可能是一回事。周作人有如鲁迅,对于青年一向未必寄予希望,但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失望。而他在对现实做出判断的同时,也在调整自己的方向;此后他所反抗的对象,相对来说就以“青年的‘重来’”为主了。而当他说:“人间最大的诅咒是肖子顺孙四个字。现在的中国正被压在这个诅咒之下。”不仅重申了《祖先崇拜》的立场,而且深化了相关认识:“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应该也只能从本质上去理解,“重来”正是本质使然。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26)
周作人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日记说:“起首作‘土之盘筵’。”这是他在《晨报副刊》上开的一个新的专栏,包括翻译的童话、知识小品和儿童剧。小引有云:“我随时抄录一点诗文,献给小朋友们,当作建筑坛基的一片石屑,聊尽对于他们的义务之百分一。”420似乎比“绿洲”更接近于他曾经讲过的“胜业”。然而才发表到第二篇,就在附记中说:“关于儿童剧的内容本来有应当说明的地方,现在不及说了。‘土之盘筵’我本想接续写下去,预定约二十篇,但是这篇才译三分之一,不意的生了病,没有精神再写了。”421——这番话写在七月二十日,其实并未“生病”,所指的是两天前发生的一件大事:一向志同道合的周氏兄弟失和了。
有关这一事件直接的文字记载,只有鲁迅与周作人当时的日记,以及周作人写给鲁迅的一封信。合而观之,可知大致经过。七月十四日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同日周作人日记不见异常迹象,似乎与之无关,他亦无所察觉。十七日周作人日记“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当是涉及此事;但多年后他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用剪刀剪去了”422。次日他作书一通:“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423十九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得斐然函,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同日鲁迅日记:“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二十六日鲁迅日记:“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二十九日鲁迅日记:“终日收拾书册入箱,夜毕。”三十日鲁迅日记:“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八月一日鲁迅日记:“午后收拾行李。”二日鲁迅日记:“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同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424
关于周作人信中所云“昨日才知道”的“过去的事”,亦即兄弟失和的具体原因,世间议论纷纷425,均无确实证据。鲁迅只隐晦地起过“宴之敖者”的笔名426,此外没有只字发表;周作人则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427所以只能说是“不知究竟”。
此前此后周作人所作文字,也许多少反映他的想法。七月十七日——即“才知道”的当天——他为前一日译完的武者小路实笃作《某夫妇》428写了“译后附记”,有云:“《约翰福音》里说,文人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犯奸的妇人来问难耶稣,应否把她按照律法用石头打死,耶稣答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这篇的精神很与他相近,唯不专说理而以人情为主,所以这边的人物只是平常的,多有缺点而很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