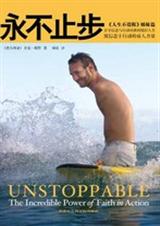书生的欲念-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前一分钟挂机,后一分钟拨打她公司的电话,亲切的接线员用甜美地声音对我说:“你好,这里是两岸文化传播公司,请问你是否需要帮助?”我说找你们的责任编辑。对方礼貌地说请稍等。两分钟后,有一个男声沉沉地喂了一声,我问他怎么称呼,他说姓莫。我说莫主编,你是否编辑过一本名为《情极隽永》的书?他警觉地问我是谁,我说是宋微澜,你们马主任的朋友,这本书的其中攥稿人之一。我马小爱不喜欢被称为经理,喜欢当编辑部的主任,她认为这样称显得有学问。莫编辑肯定地回答:“有,内页部分已经送到设计的手里了。”我再次确定:“什么时候送去的?”莫编辑说送过去两天了,马主任说争取在下个月底能发行。我说我知道了,谢谢你,当时气得肺都要炸了。
我抓住了证据,反拨马小爱的电话:“马小爱,你休想赖账!”
马小爱见我来势汹汹,声音抖得像跟钢线一样:“我没,没那意思,你的稿子真的需要修饰的。”
“狗屁!都送去设计了,还修饰你个头!”我脏话连篇,得理不饶人。她硬是狡辩:“谁说不要改啊?设计了也能改,不到印刷的最后一刻,还要改。”
“你少装蒜!难道我不知道出版社流程?”我气得拍桌子:“你听着,别跟我耍赖,否则,法庭上见!”
马小爱急了,忍不住把实情抖出来:“就算你拉我去砍头也没办法,公司不是我的,给不给钱是张彼说的算!”
我全明白了,浑身软了下来,“啪”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
老潘找我到办公室私下谈话,说这段时间写稿子要收敛点,上头似乎注意到报纸内容的质量了。我满面堆笑地说是是是,心里特恼怒,想你坐观山虎斗,白白地分得一杯羹,竟然还嫌这混汤咸水不好喝。老潘好茶,对茶文化有着深远的研究,特别是春茶,对其爱好深过海枯石烂。我抓起水性笔在一张旧报纸上写:杭州的朋友稍来绿茶,我给您带了一袋,晚点送到家给你。他看了一眼,脸色亲切起来。我撕下那一截报纸,揉在手里,点头哈腰地说先告辞。老潘笑着送我离开。刚刚出门,张芸的电话就来了,我对着手机哈哈大笑,昨天给她的电子邮箱发了一个3000字稿件,语言字字铿锵,句句锥心,把她给哄了出来了。
我一接电话,张芸就泼口大骂,我没狡辩,把手机拿开,不想去听,对着手机嗤嗤地笑。她那些骂架的陈词滥调我基本能背诵,除了分贝一次比一次大,没有其他创意。等她骂停后,我淡定地问她骂累了没有?她问我想怎么样?我半哄半逼地说:“看你的表现咯,周日我去你家找你,你把钱准备一下。假如你还是失约,那么,那稿子将会印成一万份单页,在你的学校门口分发。”张芸吼了起来:“你敢?!”我狞笑不止:“敢不敢不是你说的算,既然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做什么?你占了我的便宜,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事到如今,我打定和张芸翻脸不认人了。张芸的妈妈和我的妈妈是单位里的同事,两人同在一个车间工作,上班没事就大家一起聊天,天南海北,家长里短地说个没完没了,两人的感情亲如姐妹。我妈妈结婚得早,却一直不怀上小孩,张芸的妈妈是个大美人,眼光高,挑三拣四总找不到合适的,拖到了27岁,都拖成老姑娘了。那个年代女人27还未婚一定是有问题,没办法,就随便嫁了个罐头厂的工人,结婚才半年就怀孕了,害喜得厉害,整天和人聊怀孕的事情,等到上班的时候又把锁知道的东西和我妈妈聊,说得她连睡梦都梦见自己怀孕。没想到,不到半年,我妈妈就怀上了,欢喜得不行,都说是张芸妈带来的福气。分娩后,张芸妈是女孩,我妈也是女孩,两家人皆大欢喜,都说是命中的缘分,两个孩子才五岁就抓来跪在祖宗台前烧香磕头,结拜金兰,誓为姊妹。
在我和张芸发生冲突之后,我常常问自己,若是黄天在上,祖宗有眼,他看见我们为利益反目为仇,会是何表情?是羞耻惭愧,还是各自护着自己的子孙,怒眉对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最好的txt下载网
难散筵席
周五我请老潘吃饭,顺便叫上了刘军。三人一块开车到60公里远的三塘镇吃干锅红烧狗肉,在简陋的大排档里,他俩意兴阑珊地喝起了米酒,又划拳又猜马,喝多了就攀着肩说往事,刘军罪得厉害,说话都上句不连下句,两片嘴唇一直在打哆嗦,硬是压着老潘听他诉衷肠。老潘一边嗑瓜子,一边点头说是,也不知道能听进几个字。刘军说到了他们10年前刚刚进报社的样子,多单纯多正义,他第一次去参加兰丹县举办的党记思想研讨会,在县城里免费吃喝住了3天,走的时候,接待处还给了300元的会议补贴,自己都不好意思要,推脱来推脱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傻,换做现在,没有补贴就不去,给少了转身就骂娘,下次不去了,找累受。
老潘也深有感触,随声附和道:“对,没有什么甜头谁去啊?咱风雨十年也不容易,总不能老当见习记者啊,反正那些当官的,一个个都是养得肥头大耳的,他们每天的事情就是收刮民脂,鱼肉百姓,我们花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既然取之于民,就用之于民,属天意。”
刘军像找到了共鸣,与老潘击掌,笑道:“咱子民,用爷爷的钱是应该的!哈哈哈。”两人高兴地碰杯,如寻觅到了相见恨晚的知音。我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两个老小孩,反问自己,他们曾是仇人么?他们之前有过仇恨么?
回去的时候,轮到我开车,刘军和老潘已经醉不行,两人昂着头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我的方向感差,晚上开夜车不习惯,行驶速度相当的慢,熬了近两个小时才到市区,那时,老潘也醒了,我说先送他回去,他自悟地说当然当然,我可不愿意当你们电灯泡。我听这话十分的刺耳,知道他说的意思,扔故意反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嘿嘿地笑,劝我:“小宋啊,你也不小了,赶紧嫁吧,刘军他人不错。”
我注视着前面的弯道,沉住气,上了城南的立交桥,路况好点后,我设法纠正他的自以为是:“老潘你和刘军那么深的交情,他心里有谁你不知道?”
他啧啧地叹:“你说怎么能不知道呢?还有你们在浴一美子开房我也知道。”我惊讶地横他一眼,感到大事不妙,一定是张彼拿着事情出去说三道四了。我一走神,没注意到前方路况,差点撞到前面的车尾,我赶快急刹车,老潘随着惯性狠狠朝前倾,头磕在玻璃上。
他捂着额头嗷嗷着叫:“你这车怎么开的?你还行不行啊?”我慌神了,打转方向盘想改道,谁知旁边有一辆宝马急速飙过,我被吓的又是急刹车。老潘也跟着颠簸得瞪直眼睛,紧闭着嘴,像要呕的样子,我故意开了几步又急刹车,他已经顶不住了,手直敲车门意思是要下车。我停下车,开启车门锁,他一下车跑就到路边的绿化带边呕个不停。我偷偷乐,却假装很担心的样子,打开车门问他怎么样?老潘看似状态很不好,摆摆手说你先回去吧,我自己打车就好了。我说那怎么行呢?我送你吧。他突然一声大喝:“你再送,差不多送我上西天了!”我得逞地笑:“那劳您破费了,我改天给你报销车钱!”我咯咯地笑,踩了一脚油门,直奔城南。
开到青砖桥,刘军突然发话,我送你回去吧。青砖桥是一个十字口立交,朝左开是城南,朝右拐是去我家的方向。我说你还能开车么?他说我没醉。听他思维清晰,吐字清晰,根本不是如之前看到的烂醉如泥,想必是装的。我放心地把车朝右边的辅助弯道上开,到了小区门外,我疲惫不堪地下车,浑身肌肉酸胀疼痛。刘军坐回驾驶室,对我挥手说:“晚上回去做个好梦,谢谢你。” 从未有过的客气。我听着别扭,反问他:“谢什么啊?平时不都是这样的嘛?”他笑了,启动车辆:“谢谢你帮了我那么多,我才发现,我的身边一直有一位好姑娘陪着。”说完,“唰”地把车开走了。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奇怪,和他共事那么多年,他对我总是骂的多,赞的少,如这样暧昧的话语还是头一次听到。深夜的风很清爽,我坐在花圃的水泥凳上贪凉,仰望星夜,揣摩半天也读不懂他话中的意图。 。。
儒夫之交(1)
周五下午,刚刚开完总结会,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电话刚刚接通,对方就问我有没有空,有事想和我谈。我警惕地问他是谁?口气很不友好。他诚恳地说:“我是郭威,你看有没有时间出来坐坐。”郭威是张芸的老公,这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一时没认出他的声音。我说刚刚开会出来,你在什么地方。他很和善,主动说,我去找你吧,我不想被张芸知道。他这话的意思是这是我们私下的事情,千万别给第三者知道,特别是张芸。他如此神秘兮兮的,一定另有来头。我说行,我在建政路的上岛咖啡等你。
半小时后,郭威如约赶到,看样子是赶路赶得着急,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一坐在我面前连话都说不出,一直在喘气。我问他是怎么来的,他说坐公车。我喝了一口咖啡,用余光打量他的着装,黑西裤,白衬衣,很多年前最保守的搭配,衬衣看似穿了很多年了,失去了面料笔挺的质感,领口边也有被磨破的痕迹,显得十分的寒参。
我递给他菜单,让他自己点东西喝,他仔细地看了半天,都没叫出一样来,大概是被价格给吓怕了。我鼓励他放松,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看着菜单紧张得直冒冷汗,捂着嘴在思考,时不时尴尬地对我笑,可怜巴巴的样子,要我越看越心酸,心想难道他们的生活真的是这样的卑微贫贱,连咖啡厅的消费都要他们望而怯步?或者是他装的?明明是为谈判而来,硬是装出一副酸涩气来蒙蔽事实,迷惑肉眼,好让自己在沟通的过程中占有更多的感情分,争抢优势地位。我知道自己的劣势是感情,女人是感性的动物,我不能在没有开战之前,就动了恻隐之心,被对手轻易俘虏。
我伸手对服务生招手:“来一杯巴西咖啡。”话刚刚落音,他就低头小声地补上一句:“多少钱啊?”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一点都不阔达,跟个娘们似的。我白了他一眼:“别着急,我请客。”他立刻抢着说:“这哪能呢,应该是我请客,毕竟我是男的嘛。”他还知道自己是个男人,我心里鄙视极了,想张芸就这点眼光,这辈子就攀了这么一个窝囊废。
服务生上咖啡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问他价钱,服务生看了看我,没敢说。我托着下巴神情淡定地吐出一个数字“40”。他立马把上手放到桌子底下,瞪着桌子上的一小杯东西惊呼“呃……好贵。”我用小餐勺搅动咖啡,轻轻地品:“这里的咖啡豆是进口咖啡豆,纯手工磨制,当然是滴滴值千金了,超市里的速溶咖啡与这没法比。”他还是不能理解,觉得这眼前这玩意不值那个钱,直摇头:“40块能买两天的菜了,张芸她昨天买了一条裙子还不到这个数。”我哼了两声,不想去接他的话,感觉两人真的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话不投机半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