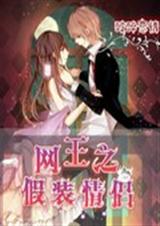假装深沉-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倒是说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他说生活有三个层次,最初级的是物质生活,中间是精神生活,最高级的是灵魂生活,前两个我尚能理解,可是何为灵魂生活呢?它和一般理解的精神生活又有什么区别呢?丰解释说,精神生活是指对学术文学艺术上的追求,然而当人不满足于此的时候便开始探究人生更深刻的问题,比如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而这就需要代表于宗教的智慧来解答,于是就有了灵魂生活,它一般指的就是宗教生活。当我理解了丰子恺先生的这番话以后便开怀了许多,对现实生活的厌烦和对更高层次生活的追求是可爱的,然而我却自知尚没有足够的智慧,文学和艺术于我还是相当高深的,更何况于宗教和灵魂。只是由此我也找到了方向,我的解脱之道不需要告诉城市,不需要远离喧嚣,只需有够力量的文艺作品就可以了,比如我迷恋的黄梅和红楼。此二者,足矣。。。
想要追寻李叔同,吾辈尚远。。。。呵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从七仙女的择偶标准说起
迷上黄梅这么多年,有一个疑问我一直耿耿于怀,七仙女怎么会看上董永的呢?这个问题似乎没人关心过,也许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好事怎么也不会轮到自己,琢磨了也是白琢磨,索性就懒得想了,不过我还是要自作多情地去考究一番。
最直接的线索是里面的几句唱词:“我看他忠厚老实长得好,身世凄凉惹人怜”,解读这两句话就大致可以得到七仙女看上董永的几大原因了,“忠厚老实”是指性情,“长得好”是指容貌,所以连起来就是既要性情好又要容貌好,其实这两条也是最典型的传统择偶标准,并无特别之处,况且天底下这样的男人多得是,蔡某自己也是的,怎么就没有仙女看上呢?只好再来解读后半句:“身世凄凉惹人怜”,我发觉“怜”总与“爱”连在一起,有了怜,就离爱只有一步之遥了,在黄梅戏里尤是,比如《送香茶》里也唱到“宝童哥生得好真真不错,倾诉说伤心的事他珠泪滂沱,流泪眼相顾盼,深深地打动我。。。”这里面吸引这个女孩的除了“生得好”,接下来的就是由怜生爱了。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由怜到爱往往更容易产生在强势的一方,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这两个戏里面竟然都适用,七仙女是仙子,在一个凡人面前自然有心理上的优势了,而送香茶里面这个女孩作为收留对方的人,她也自然占有心理上的优势,于是由怜生爱也变得顺其自然了。
但我以为以此来解释仙女没什么偏偏要看上董永依然有些牵强。这里面似乎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仙女寂寞了,思凡了。而事实确实如此,刚开场七女就一个人在那儿唱“天宫岁月太凄清,朝朝暮暮数行云,大姐常说人间好,男耕女织度光阴,我有心偷把人间看。。。。”,在这里面,七女思凡的心思已表露无疑,我觉得这恰是最关键的,带着这样心境去看人间,也许,哪怕看到的是李达钟魁也会顿生爱意吧,何况还是个“忠厚老实长得好”的董永,如此想来,天底下这么多好男儿都没有仙女垂涎,这过并不在我等了,实是仙女无此心罢了。
呵呵,玩笑扯远了。其实不管仙女也罢,神女也好,不都是咱凡人随口编造的嘛。所以,真正值得探究的是隐藏在这故事深处的一些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和观点。就以择偶来说吧,前面已经讲到了七仙女看上董永的一个表面的原因是性情好加容貌好。这其实正好反应了我们长久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择偶标准,即人要好心要善,次而又是容貌。虽然“人不可貌相”之类的话代代相传,但真正听进去的却不多,特别是在择偶的时候还是相当重视的。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这也是天性里的东西,也是怪不得的,值得玩味的是前半句“忠厚老实”。要知道,这在当代几乎是被当成缺点甚至是可耻点来看的,谁被人评价为“忠厚老实”自己心里都会觉得不舒服,在当代,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贬意词,忠厚老实的人轻则稍稍能够混口饭吃,但总要受尽欺负,重者混不下去,没饭吃,讨不着老婆,被人踩在脚底下,总之,忠厚老实者绝大多数都是很可悲的下场的。而恰恰在当代处于最底层的一类人为什么曾经在那个时候会受到一致的欢迎,以致于被作为首要的择偶标准呢?颇为费解。
首先,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被弃是女子的第一大隐患和威胁,而只有跟随忠厚老实的人才能把这一风险降到最低。而实际上连这也还不是绝对安全的,比如诗经上的《氓》,起初氓就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物,所以那女子才心甘情愿的随他去的,不想到后来却完全变了以致于最终被弃,所以,为了获得相对高点的安全感,女子们择偶的首要条件就是忠厚老实,长得好倒是其次了。
其次,过去我们纯粹是农业社会,绝大多数的人都以务农为生,务农是纯技术性的活,并不需有太多的交际能力不需要懂得太多的人情世故,只老老实实种地就能过得相对幸福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也是相当适合于忠厚老实型的人的,于是挑选一个这样的老公至少可以衣食无忧了。
仅此两大理由就足以让当时的贤德纯朴的女子们选择忠厚老实型的男人了。只是时代变得太快也太无常,今非昔比,今 天选择做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也许会很惨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时代的悲剧。。。
许久不更新了,今夜突发奇想胡言乱语几句。。。惹君一笑尔。。。
说酒
忽然发觉自己近来对酒越来越有好感了。不过这好感仅限于“品”,还没有到“酗”的地步,我也时常告诫自己,若到了酗的地步,酒便俗了,而自己也就跟着一起俗了。然而,究竟如何区分是品还是酗呢?《红楼梦》里的妙玉说,“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四杯便是饮驴了”这原说的是喝茶,不过我以为用在喝酒上也是合适的。于是蔡某为了装出品酒的架式来,常常一口三渍以示回味无穷。然而蔡某究竟还是俗人,始终不曾品出其中的甜美,生生把陈酿的好酒给糟蹋了,可惜哉。。。
在渍酒的时候,我也时常怀疑起古人发明酒的缘由或者说动机来。不可否认,酒是个相当伟大的发明,远比同时代的其它发明要了不起得多,石器已经被黄土深埋,战车早已成了朽木,尧舜已经入土千年,惟有这酒,一直还在酿下去,而且依然不改当年的香醇,不但酒未改色,就连喝酒之人也比当年更具雄风了,君不见,如今七八个小伙,一次聚餐就可以一气灌下几十斤。张飞李逵武松见了恐怕也要丧胆的。不过这是题外话,我的兴趣仍然在于古人究竟对酒怀着怎么样的期待呢?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这似乎是一个答案,后人也说“借酒浇愁”,却紧接着又有人加上了“愁更愁”三个字,使得原本有些眉目的疑问又陷入了困惑,不过由此却也可以知道酒与古人的忧愁密切相关。由此我们至少知道,酒无关温饱,它是与人的精神世界关联的一样东西,由此也拉开了它与果腹充饥的稻梁之间的距离。酒的地位便从此升高了。历代清高人士都爱说“文章不为稻梁谋”,却没有人说“文章不为好酒谋”,酒是文人爱不释手,甚至是生活必须的东西。李白必得酒醉方能作得一手好诗,曹操喝多了便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酒竟然使他如此痛快,此不能不说是酒的神奇所在了。至于酒究竟能使人解忧还是愁更愁,这已经不重要了。就让它成为千古谜团吧。
可是,酒所带来的矛盾也不止在解忧与更愁之间。有时还在于是与非,真与假之间。人道“酒后胡言”,这原本很可以理解,酒后疯言狂语不足为怪,偏又有人说“酒后吐真言”,却也是一句大实话,于是酒后之言一下子又变得真假参半难辩真伪了。至于酒后豪言壮语者更是缕见不鲜了。酒带给人的痛快和失意实在一言难尽。
然而酒的这些功效在现代人眼里却一下子渺小起来。现代人说,如果要兴奋,直接服兴奋剂得了,如果要解忧,直接服安眠药得了。是的,在现代医学面前,酒一下子显得苍白而无力。似乎它也已经到了行将就木该被埋入黄土的境地了。然而可喜的是酒却依然未受冷落,究其原因,我想无论是服用兴奋剂还是安眠花,终究显得太功利了,为兴奋而兴奋,为镇静而镇静,目的太明确,毫无趣味可言,反而让人感觉不自在,唯有酒,是在自然而然不知不觉中给人以想要的,那种飘飘然,似醒非醒,似梦非梦的境界。酒是如此的体贴人性,因而也为人所长久地爱戴和享用。
酒的妙处是说不尽的,不过还是要记住妙玉的话,一杯为品,喝多了就俗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猪头肉与诗
有美食家说,难道诗还香过猪头肉吗?这本不是一个疑问句,然而在我听来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难题。不过暂且不论哪个更香,单是把猪头肉和诗放在一起也已经够有创意的了。
不可否认,猪头肉实在香得很,无论何时何地想起它,都有令我掉口水的力量,而同样的,曾经在某段时间里,当我想起某首诗的时候也总会怆然泪下(只是那善感的岁月也许已经不去不返)。口水和泪水,一个代表我的食欲,一个代表我的情欲,都是源于我灵性深处的东西,也都是我不会轻易掉落的东西。由此我认定,猪头肉与诗,两者皆不是俗物。
我曾经在某篇文字里说,酒是属于文人的,而猪头肉却又以佐酒而著称,于是我可以相信,自古以来猪头肉对于文人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在这上面,诗似乎逊色了。不过好在对于文人,酒过之后便是诗意爬上来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说,猪头肉于诗,非但不是风马牛不相及,恰恰是极为重要的铺陈。
我见识过的美食家大都能说会写,常在报端开辟美食专栏赚人口水。我也常听说文人也大多精于饮食,对食物常像对文字一样评头论足左右挑剔。大概在文人眼中,食物与文字都是值得把玩并且爱不释手的东西吧。也如同猪头肉在食物中的独特位置一样,诗自然也在文字里是极为精巧的形式了。这样想过一遍之后我不免要对说出那句话的美食家报以惋惜了,想来作诗者有高低之后,品美食者也自然有高低之分了,说诗不及猪头肉香的“美食家”其实也只能算是普通食客一级的人物吧,冠以“家”字显得有些抬举了。红楼梦里妙玉说一杯为品,二杯便是解渴的俗物了,我们不妨也可以这样看,啃一口猪头肉呷一口酒,溜达出一句诗为品,若是只顾着啃猪头,啃了一口又一口,那它便是充饥的俗物了,那啃猪头的人也刹时显得俗了。
仔细想来,将诗与食联系到一起也并非今人的首创。《红楼梦》里湘云在行酒令时说“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美食由此入诗了。也许在红楼梦之前还有更早的例子吧,暂且就不追究了,总之诗与食是素有渊源的,更何况行酒令本身也是一种将诗与食联系到一起的举动。可见古人还是相当有闲情逸致的。甚至我曾怀疑每一首妙诗的背后都有阵阵酒香吧,酒仙李白尚且如此,何况芸芸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