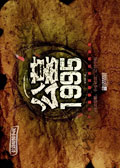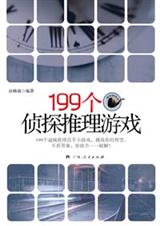1938·花园口黄河大决口:黄河殇-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从中国出版的史书中查到,公元1938年5月14日,日军攻陷菏泽,守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三师进行了顽强抵抗,师长李必藩中将、参谋长黄启东少将英勇殉国。一位曾在第二十集团军作战部任职的抗战老人对我说,日本人的进攻决非轻易得手,他们当然是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才占领菏泽城的。
尽管日本记者大肆渲染侵略军的所谓重大胜利,我们还是不难从“笔武士”的战地报道中发现真实战场的冰山一角。记者写道,当日本军旗在残破的菏泽城头猎猎飘扬时,他惊讶地得知敌方战死者中竟有一位手持步枪的###将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中国人的决死精神赢得日军的尊敬,指挥官下令把尸体交还敌方。记者为此得出结论说:虽然战死的###将军像个武士,但是他的部下却很怕死,我相信这是敌人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鬼子来了5
土肥原下令向派遣军发出报捷电。
本来一旦占领菏泽城,第十四师团即告胜利完成任务,因为按规定山东地面是第二军的作战范围,土肥原只是临时渡河来支援而已。但是没容他喘过气来,司令部里电话铃声大作。
土肥原拿起话筒,立刻“嗨”地绷直身体,脸上的惊讶表情将一对金鱼眼撑得滚圆。他听出来对方并不是派遣军那帮装腔作势的参谋幕僚,甚至也不是他的直接上司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那个以独断专行著称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
寺内总司令是个来头很大的上级,他出身于日本显贵的寺内家族,其父寺内正毅为日本第十八届内阁首相,他本人曾任内阁陆军大臣,连当朝的近卫首相也要让他三分,所以飞扬跋扈常常令下级敢怒不敢言。此刻总司令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傲慢,他无需征求下级意见,再次下达一道出人意料的简短命令;放弃菏泽,立即向南转进,切断陇海铁路。
根据最新情报,徐州当面的薛岳兵团正沿陇海铁路筑起多道战线与日军对峙,他们身后便是被称作“兵家必争之地”的开封和郑州,那里囤积有更多中国军队随时准备进行支援。至此土肥原方才如梦初醒,他明白总司令的意图显然是要将第十四师团作为一支奇兵,从侧背长途偷袭中原地区,切断陇海铁路,堵住薛岳兵团退路。土肥原不由得感到一阵气紧。因为如果达到上述目的,敌人北方防线便名存实亡,夺取开封、郑州犹如探囊取物,问题是第十四师团必须孤军深入数百里,单独对抗十倍以上的中国大军。更重要的是,他将面对的中原之敌不再是那些不堪一击的杂牌军,而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中央军精锐兵团。这简直是个疯狂和不可思议的赌注啊!但是他不敢对抗总司令的意志,只好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师团是……单独转进吗?
总司令当即给予肯定回答。
土肥原身体晃动一下,有些站不住了,他知道此前东京大本营有令在先,华北派遣军不得逾越徐州以西战线,而总司令却命令他长途奔袭数百里外的陇海铁路,须知越权进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于是他只好婉转地表示说:据卑职所知,中原至少有数十万敌军啊!
总司令立刻毫不留情地敲打这个前特务机关长,他冷冷地说:阁下害怕###人吗?怪不得阁下行动迟缓,不希望是这个原因吧。
土肥原后背上立刻渗出冷汗来。
他从总司令话中听出了一种威胁的意味来。在华北派遣军中,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同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尖锐矛盾已是公开秘密,第十四师团隶属第一军建制,土肥原是香月清司的老部下,是公认的“香月派”,如果总司令迁怒于他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如今第十四师团渡过黄河立足未稳,如果一旦未能达到目的或者遭遇意外失利,岂不等于授人以柄,这个“擅自越权进攻”的罪责难免落到他的头上。于是土肥原绝望地抗辩说:请允许卑职向第一军司令官请示吧。
总司令大怒,在那一头申斥道:混蛋!这是阁下在接受派遣军总司令的命令吗?你听着,如果第十四师团不能完成任务,阁下将被立刻召回东京。
电话挂断。
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很快得知此事,他两次向派遣军提出抗议,均遭驳回。此时军司令官权力已经被架空,他甚至指挥不了自己的部下,而土肥原则明智地选择了服从。战后出版的《大本营陆军部》载:华北派遣军两次命令第一军增调第十四师团主力东进,协助第二军进攻,但第一军未予执行。土肥原指挥官……冒着被追究越权责任和敌人围攻的风险去发动一场新的战役。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鬼子来了6
国土沦陷,敌人逞凶,菏泽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
数百被俘官兵被敌人驱赶到一座空地上集中,一个挎战刀的日本大佐带着翻译官噔噔地走过来,连比带划地吼叫一通,可惜那些硬梆梆的日本话俘虏听不懂。翻译官是个猴脸台湾人,讲一口蹩脚的国语,他把大佐的话翻译过来,大意就是皇军天一亮就要出发,去进攻驻守山东的###军队。大太君说,你们这些俘虏,统统都要转移到城外去。
俘虏一听就炸开锅,日本鬼子所说的转移就是要将他们赶到城外去屠杀,敌人此类暴行数不胜数。俘虏高声抗议:我们不走!死也要死在城里面!
翻译官叽叽咕咕地讲了一阵,大佐就发火了,翻译官赶紧翻译说:大太君说,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有什么资格死在城里?你们要是像个真正的军人,为什么不死在战场上?
俘虏立刻泄了气,他们听懂日本军官的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死在城里的人必须是战士,而不是俘虏。第二是俘虏不值得尊重,他们将像牲口一样被任意屠杀。日本兵涌上来,明晃晃的刺刀一阵乱捅,将俘虏强行赶往漆黑一片的城外去。
时值立夏,经过一冬生长的麦子正在进入灌浆成熟期,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像乳汁一样香甜的小麦气息。很快俘虏发现,押解的日本人并不太多,看守也不十分严密,加上天空没有月光漆黑一团,让人们重新开始燃起生存的希望。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死逃跑,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只要挣脱绳索的束缚像鱼儿一样游进黑夜的大海,日本人再凶恶也是枉然。有的俘虏率先行动起来,他们悄悄挣脱捆绑,眨眼工夫就钻进路边的庄稼地不见了。更多俘虏受到鼓舞,争先恐后地解开绳索,然后飞快地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等到日本人发现俘虏队伍像火炉上的冰块一样迅速融化时,那些幸运的逃亡者已经不知去向。残暴的日本人枪杀了来不及逃跑的俘虏,当凄厉的枪声和受难者的咒骂惨叫渐渐平息下来,大佐军官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诡异和满意的微笑,然后下令收兵回城。
一些俘虏终于逃回自己人阵地,他们的生还简直是个奇迹,更重要的是俘虏为中国军队带回来一个重要情报,那就是敌军即将对山东境内的第二十集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个情报受到前线指挥官的高度重视,立即上报上级和战区总部。
几个小时以后,武汉大本营获悉日军这一重要动向,总参谋部除命令第二十集团军高度戒备严阵以待外,同时还命令郑州第一战区往山东方向调动兵力,随时准备支援第二十集团军作战。
。。
鬼子来了7
战后日本出版的陆军战史证实此事,称第十四师团故意放走俘虏去向中国军队报告日军进攻山东的假情报。原来这是诡计多端的土肥原玩弄的一个花招,他派出一支小部队向山东境内做出大张旗鼓的佯攻姿态,而师团主力则偃旗息鼓地朝着数百里外的中原腹地隐蔽疾进。
1938年5月中旬,一支日军快速部队忽然出现在河南民权地面上,随即与守军发生战斗。日军接连占领民权县城西北的野鸡岗、石楼、楚庄寨和内黄集等地,其前锋推进至距离民权火车站不足千米的李家集。在日本指挥官的望远镜里,一条乌黑的铁路已经隐隐可见,而火车拉响的汽笛声则像潮水一样在暮春的豫东大地上涌来涌去,刺激着日本人的贪婪胃口和野心。
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近在咫尺。
风云突变1(1)
湖北棉纱大王张松樵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造就的传奇人物,他的发家史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艰难成长的历史见证。《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载:张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卒于1960年,享年八十八岁。他一生历经坎坷磨难,是我国民间纺织业的开拓者之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裕大华资本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纺织王国,分别拥有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石家庄、广元、台北等多家大型纺织厂,另有铁路、矿山、码头、银行、学校和房地产投资等等。湖北裕大华集团与沿海申新(荣氏)集团双峰鼎立,并称中国纺织界两大巨头。
许多人或许不理解,何以我爷爷张松樵姓张,而他老人家的后代比如我父亲和我却姓邓?关于家族姓氏的来历,多数人只知道裕华纱厂老板名叫张松樵,却不知道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邓旋宗。在这个有关姓氏来历的故事后面隐藏着张松樵乃至我们家族鲜为人知的身世之谜。
父亲告诉我,我们邓氏家族并非湖北原住民,张松樵的祖母也就是我的太曾祖母是从中原地区逃荒来到湖北的灾民。我在史书上查到,清朝道光元年(1821年)至同治年间,黄河大水多次溢道,其中尤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河南###决口为甚,洪水冲垮大堤达三百余丈,淹没州、县二十余个,中原一地流离失所者甚众……
据湖北《汉阳县北泉乡志》记载:清咸丰年间,有河南妇女邓彭氏携一邓姓男孩流落北泉乡万子山村……该村张姓乡民无子嗣,遂将其收养,改姓张。
这个“河南妇女邓彭氏”就是我爷爷张松樵的老奶奶,邓姓男孩就是我的曾祖父,张松樵的父亲。上述文字记载的就是我们邓氏家族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风雨中走过的艰难坎坷的迁徙历程。
张松樵七岁进城讨饭,小小年纪做过学徒、伙计、帮工、管账,历经大半个世纪的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湖北棉纱大王,这是一个有关财富和命运的世纪传奇,也是我在另一部传记作品里将要讲述的家族故事。张松樵一生娶过三房太太,前两房分别是他的救命恩人,杂货店老板女儿和上海一位徐姓买办的千金小姐,她们所出子女也就是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都姓张,是所谓“正姓”。前面说过,张松樵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叫邓旋宗,此为“祖姓”,也就是“邓彭氏”从河南老家带来的祖宗姓氏。父亲说,曾祖父去世早,曾祖母过世之前把儿子叫到跟前,此时张松樵已经发迹,曾祖母念念不忘嘱咐儿子的一件大事就是,你是俺河南老邓家的后人,你得为老邓家“三代还姓” ,要不俺老邓家就要断子绝孙啦。“三代还姓”是一种古老的中原习俗,指被外姓收养的男孩可在第三代恢复祖姓,所以“三代还姓”就是关系河南老邓家薪火相传的祖宗大事。
曾祖母去世这年张松樵已经五十二岁,他为了遵从母命决定迎娶第三房太太,而这位未来的女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