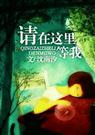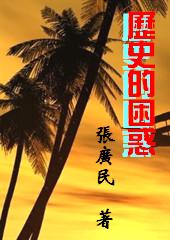历史在这里沉思-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广袤无际的沙漠里,连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烘烘的。天上没有一丝云霓。地上没有一寸树荫。在沙地上,每踏上一脚,都要溅起一股烟尘。我的头发里、耳朵里、衣袋里,全是细沙。
在库木库都克,我一边参加搜索彭加木,一边进行着采访。搜索在每天清早进行,那时候气温略微低一些,警犬能够恢复嗅觉。另外,清早通常不刮风,也有利于搜寻。
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冒着热浪,我采访了彭加木的老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还采访了许多彭加木的同事以及搜索指挥员……
经过实地采访,当我回到上海,很快就写出《彭加木传奇》一书,全面反映了彭加木为科学、为边疆献身的可贵品格。意想不到,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五行大字标题和整版篇幅,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宣称彭加木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餐馆里!这下子,彭加木变成了“敏感人物”,我的《彭加木传奇》一书在报审时,有关部门要我作许多删节和修改,据说是“避免给海外的谣言提供证据”!后来,这本书再三删节,仍无法出版。
这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不再报审,打了纸型,准备出版。然而,就在付印前夕,又一次受到干涉。上海人民出版社无可奈何,放弃了出版计划!
我以满腔热情投入采访、创作的一本新书,就这样流产,不仅我想不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极感遗憾。
这本书在我的书房里“雪藏”了二十六个春秋。已经被人们淡忘的彭加木,由于2006年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经过媒体广泛传播,使彭加木再度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热点人物。
我记起二十六年前写的《彭加木传奇》,进行了大修改,补充了十多万字,写成长篇纪实文学《追寻彭加木》一书,
一部“雪藏”了二十六年的书,在新疆全国书市上亮相之后,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5)
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第一次。我在1961年写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被出版社退稿。“雪藏”了十七个春秋,在1978年出版,一下子就印了三百万册!
这似乎印证了“酒越陈越香”这句话,尽管这样的“雪藏”充满了苦涩与无奈。
查清密探的来历
1921年7月30日晚上,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的时候,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男子。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意识到来者不善,一拍桌子,立即决定散会。
那幢石库门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李书城在此居住。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那天,代表们按照马林的紧急决定刚刚散去,那个陌生男子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这表明马林当机立断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那个闯入*“一大”会场的陌生人确实是密探。
翌日,会议转到浙江嘉兴东湖举行。*“一大”在东湖的游船上顺利闭幕。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查找:那个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究竟是谁?
当时,出席*“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十四人:其中*“一大”代表十二人(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之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据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由于没有详细的线索,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查清这个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
我在创作“红色三部曲”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查清了这一历史谜案。我的查证,得到了许多*党史专家们的认可。
“红色三部曲”总共150万字,是写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红色历程。“红色三部曲”由三部长篇组成,即《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这套“红色三部曲”在大陆、香港、台湾分别出版,产生广泛的影响:
我用三句话,概括“红色三部曲”中三部长篇的主题: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txt小说上传分享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6)
《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
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我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程,内中就涉及那个突然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一大”会场的呢?
经过查证,是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来华时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1921年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正是因为马林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所以在7月23日晚当马林来到上海“李公馆”出席*“一大”开幕式,便使“李公馆”引起密探的注意。
也正因为这样,当7月30日马林再度来到“李公馆”,出席*“一大”闭幕式,密探就突然闯入“李公馆”……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破解这个历史之谜的重要线索。
1990年暑日,我的长子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里。中叔皇问他:“你爸爸最近在写什么?”长子看过我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的手稿,答道:“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书。”长子说及书中描述*“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情形,中叔皇便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法租界的情况,可以去采访一下。”
依照中叔皇的提示,1990年8月9日,我前往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家中拜访。
当时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他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他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知道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7)
薛耕莘先生说起他的传奇经历:
他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他出生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薛仲江是陆家嘴英商鸿源纱厂棉花部主任。母亲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出生在英国一个大户人家。
在薛耕莘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送他到比利时读书。薛耕莘颇有语言天赋,在比利时读书精通了中英法三国语言。
在薛耕莘十三岁那年,母亲病重。薛耕莘接到电报,从比利时赶回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嘱咐他:“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中国。”
1930年,二十六岁的薛耕莘参加了法租界工部局的招聘考试,被法租界巡捕房录取,成了一名翻译。凭着过人的聪颖和勤奋,他很快从一名低级翻译晋升为巡捕房的特级督察,并享受外籍待遇。在法租界任职期间,他又在震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薛耕莘周旋于法国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既要执行法国总领事的命令,也为国共两党都做了些好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于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曾经帮助过国民党,他被国民党政府授予金质胜利奖章。凭藉着法租界的根基,薛耕莘出任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局长,直至上海行动总指挥特警组组长。
解放后,薛耕莘在*反革命运动中,于1951年4月29日被捕入狱。
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决:“薛耕莘勾结帝国主义反动派,罪大恶极,本应处死。姑念该犯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
薛耕莘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后来关押在内蒙,直到1975年在太原遇赦。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五年。
1981年,薛耕莘案获得彻底*。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
1990年5月起,薛耕莘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成为上海文史馆终身馆员。
薛耕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法租界巡捕房特级督察、国民党政府少将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离休干部三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尽管度过二十五年艰难的铁窗生涯,却一点也看不出苦难生活烙下的影子。他非常健谈,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直至我在2007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03岁的他仍健在。他甚至在2006年还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
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薛耕莘先生是在1926年才进入法国巡捕房的,他不可能参与1921年搜查“李公馆”事件。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令我兴奋的是,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薛耕莘回忆说,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8)
我连忙问起程子卿的情况。
薛耕莘说,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