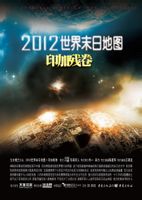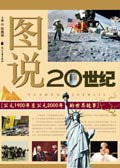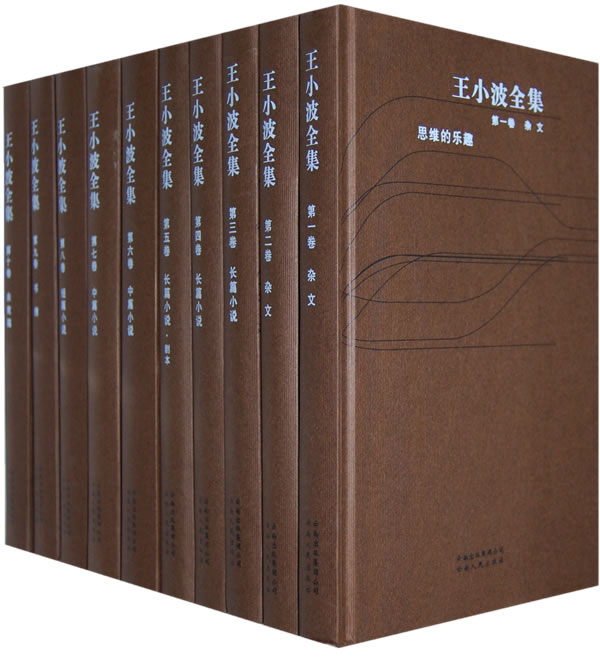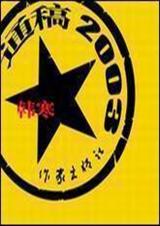2007年第2期-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威辛》第8页,岩波书店1995年版)。只有经过这种抗争,人类才能与过去的历史达成和解,最终实现普遍的正义。高桥在阿伦特的“忘却的洞穴”说的启发下,结合日本的现实政治课题,提出有必要建立一种连接历史和当下的“记忆的政治学”。然而,阿伦特的“忘却的洞穴”说以及她对于二战中的大屠杀的思考并非前后一贯,特别是后来,在写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她强调“彻底的忘却”是不会存在的,她甚至认为:“所谓忘却的洞穴等并不存在。人类所做的事情不可能那么完美无缺。实际上人多得很,彻底的忘却是不可能的。肯定有生还者出现讲述所见到的事情”(《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日译本第180页,みすず书房,1969)。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阿伦特的这个重大转变呢高桥哲哉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无法否定存在“忘却的洞穴”的可能性,阿伦特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明显地是一种思想倒退(《记忆的抗争——战争、哲学与奥斯威辛》第17页)。高桥哲哉批评阿伦特前后矛盾,意在强调“大屠杀”和对于大屠杀的“忘却”决非历史上的“特例”,而是“一般历史”的原暴力本身:“如果说历史‘一般’是由胜者,或者至少是由‘幸存者’所书写的,那么受到无法恢复的忘却之威胁的,就不仅仅是波兰的犹太人社会和华沙犹太人区了。‘忘却的洞穴’决非仅存于奥斯康辛等场所,而是无所不在的。或许,正因为有‘彻底的忘却’,这无所不在的大屠杀才成了我们的记忆所难以企及的地方。”(《记忆的抗争——战争、哲学与奥斯威辛》第18页)
阿伦特的“思想倒退”恐怕与她对“他者的历史和记忆”缺乏感受力有关。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她的著作中的“非洲印象”及其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2卷第5章中,阿伦特探讨了“民族国家的没落与人权的终结”,她一面指出普遍人权与为此提供保证的民族国家之民族中心主义特征之间的矛盾,一面用“欧洲心脏的非洲化”比喻失去基本人权保障的大量难民的出现,以此强调“文明世界的内部崩溃”造成了无数欧洲人跌落到与野蛮部族一样的境地。由此可见,阿伦特明显地将欧洲与非洲视为“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她甚至强调早期欧洲对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和对原住民的杀戮不值得记忆,因为这两个洲在当时处在“法之外”。在这里,欧洲-历史-法-界线构成了一个逻辑思考的圆环。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高桥哲哉认为,我们对此必须提出严厉的批判,需要记忆的东西并不局限于“人们所记忆并具有连续性的世界”,最紧迫地需要记住的东西是暴力,是一切暴力,是“灭绝的暴力”,不管是存在于“世界”外部的灭绝还是来自“世界”本身的灭绝。或许所谓“人们所记忆并具有连续性的世界”(欧洲世界)本身就是通过“灭绝”的暴力而创立的,就是通过忘却或者隐蔽“灭绝”之暴力而确立起自己的“法”。我们必须记住“世界”本身的暴力性,“法”本身的暴力性,制造“壁垒”、用“界线”划分领地的暴力性,以及作为“法”而发挥作用的记忆之暴力性。(《记忆的抗争——战争、哲学与奥斯威辛》第106页)。简言之,一切暴力都应该在我们的记忆的范围中,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与所有“忘却的政治”相抗争,所谓“记忆的政治学”也才能被更有效地建立起来。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中提到人类具有做出“判断”的责任,这是高桥哲哉关心的另一个问题。阿道夫·艾希曼是一个平庸而循规蹈矩的德国党卫军成员,从1942年起被任命去协调和管理将犹太人押送到死亡营的后勤工作,有数百万犹太人经他之手而惨遭迫害。1946年他逃过美军的追捕,此后隐居于阿根廷。1960年以色列特工抓获了他并将其偷渡出阿根廷。1961年,艾希曼在以色列接受审判,不久被判处绞刑并被立即执行。阿伦特一直关注此案件并主动要求作为记者旁听以色列法庭的审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便是有关此案件的评论文章的结集。阿伦特的评论涉及到艾希曼是否有判断能力,偷渡以及在以色列法庭的审判是否合法,欧洲犹太人委员会在战争期间被迫与纳粹合作的罪责等等问题。作为亲身经历了纳粹迫害的犹太裔美国人,阿伦特的位置十分微妙,但她始终把思考集中于和人类的“判断”有关的道德问题上,并结合对责任人的处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哲学上的重要课题。高桥哲哉在思考“慰安妇问题”和日本的战争、战后责任时,对阿伦特的“判断”概念做了创造性解读,并从中获得了重要的参照。
所谓“判断”涉及到如何对纳粹统治下的各种犯罪进行伦理、政治、历史乃至法的判断的问题。针对那些对判断的责任持否定态度的观点,阿伦特提出了“判断”问题,她强调人类应该履行“判断”的职责,回避判断或者判断力的衰退,正是使艾希曼的犯罪成为可能的极权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精神结构。高桥哲哉注意到,阿伦特强调判断责任的不可回避性,其原因首先在于正义的呼唤,这和她对自由与人类境况本质的认识密切相关。在阿伦特看来,“自由是人类境况的本质,而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境况之本质。换言之,自由是个人的本质,而正义是共同体的人类之本质”(《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著)。如果人们不履行判断善恶的责任,正义就无法得到维护,以正义为本质的人类共同生活就将面临崩溃的危机。阿伦特还强调,做出“判断”的目的,在于通过回应正义的要求,实现当下的我们与悲惨的过去之和解。由此,她在《人类的境况》中并列地提到“惩罚与宽恕”问题,认为宽恕作为惩罚的替代,是将我们自己从一直束缚着我们的负面遗产中解放出来,为重新开始与他者的共同活动而实施的积极行为。当然,宽恕不适用于“有意识的恶行和极端的犯罪”,在这种场合代替宽恕所实行的惩罚是要切断过去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在《人类的境况》中依然保留着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立场——像大屠杀那样的犯罪,超出了人类理解的范围,是一种无法宽恕的根源性的恶。对此,高桥哲哉提出了质疑:如果坚持这种“根源性的恶不可饶恕”的立场,势必造成“恶恶相报”的后果。应该说,“不包括任何宽恕的惩罚将成为复仇,不包括任何惩罚的宽恕将成为上帝的宽恕。而现实中的惩罚与宽恕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战后责任论》第109页)。此外,阿伦特以“杀害犹太人的纳粹没有生的权利”为理由,支持耶路撒冷法庭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判决,高桥哲哉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种观点源自阿伦特自己本该反对的极权主义逻辑——仿佛自己有权利决定谁能够住在这个世上一样,我们应该从超越“恶恶相报”的立场,来探索“惩罚”问题(《战后责任论》第121页)。
最后,高桥哲哉还注意到,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阿伦特有意识地把“法的逻辑”与“政治逻辑”区别开。在对艾希曼的审判中,法官为维护法的逻辑努力排除来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治影响,阿伦特对此做出了高度评价,同时,她还特别强调要对被“法的逻辑”牺牲掉的、有关大屠杀的各种政治性和思想性问题做出思考和解释。因为,在阿伦特看来,刑事审判不是为被害者而是为正义代辩,故所谓“判断”必然包括对法的责任、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的判断。这是阿伦特关于这场审判的思考中最深刻、最有启发性的地方,它在高桥哲哉关注的“从军慰安妇”、历史认识和日本的战争、战后责任问题中也有所体现。高桥哲哉对阿伦特的解读不是一般的学术阐释和知识介绍,而是带着解决现实政治课题的目的与阿伦特进行的一场艰难的思想对话。在批判性的省察、认同和论争中,高桥哲哉形成了自己观察和“判断”日本当下政治问题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唤起记忆来与“忘却的政治”相抗争,强调人类的“判断”的责任以审视日本的殖民主义的侵略历史,并且通过厘定日本的战争和战后责任,使之负起法、政治和伦理的责任,以回应他者和正义的呼唤。
艺术是怎样变成垃圾的?
吴迪(启之)
一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兄弟俩,兄名刘忆苦,弟叫刘思甜。这既合乎逻辑,又符合国情。“忆苦”和“思甜”一奶同胞,但一定要苦在前,甜在后。这个前后又有一个铁打的规矩——以1949年为界,如果把这个规矩颠倒过来,就要吃苦头。某老工人老贫农上台忆苦思甜,诉了半天苦,竟说的是那界线之后的事。会议的主持者恼羞成怒,诉苦者即成现行。这种故事在今日是饭后茶余的笑谈,在当年可一点也不好玩。人们以为1952年的院系合并取消了心理学,心理疾病从此求医无门。此言大谬。殊不知,风行数十年的忆苦思甜就是绝好的心理疗法。此法的要诀在于比较——或跟本国的过去比,或跟别国的现在比。此种药方普适而长久,唯一的缺点是不能包治百病。不过,我最近发现,如果采用中外古今相结合的比较法,这一缺点将被彻底消灭。这是邵牧君的书——《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给我的大启示。
在我以前的印象里,好莱坞拍片子似乎百无禁忌,可以批总统,可以骂政客,可以揭露司法腐败,可以痛斥警察恶行,可以搞软硬情色,可以拍两性激情……总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老美简直自由之极。看了邵先生的书才知道,上帝是公平的,老美原来也难受过——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天主教道德联盟、执行局这两个恶婆婆以“海斯法典”为权杖,大施淫威于影业,高扬道德至上;篡改真实为虚假,一味歌功颂德。编导们即使摧眉折腰,仍旧动辄得咎:改编名著、话剧要挨骂,写实主义遭封杀,揭露资本罪恶挨枪毙,社会题材被禁止,谈情说爱不能拥吻,下层粗汉也要举止文雅,不许说“狗狼养的”、“他的”一类的话……英雄盖世的八大公司,求为小妇而不得,竟沦为奴颜婢膝之贾桂。看到这里,我的心里莫明其妙地升腾起一种浩荡的快感——忆苦方能思甜,老美当年的苦日子,足以让国人大开眼界,大获平衡,大感宽慰。
二
邵牧君给我们举了二十多个个案,说明好莱坞当年在性、暴力、政治、名著改编与社会热点题材诸方面受的苦。兹从中各选一例,以便诸位举一反三。
性方面的典型案例首推《安娜·卡列尼娜》。各位可能会奇怪:这不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吗写的不是一个追求爱情的贵妇人的故事吗诸位有所不知,海斯法典是以维护传统道德为己任的,排斥婚外恋情,反对非婚生育,保护家庭完整,而这些都与性有关。恰恰在这些方面,托翁和他的《安娜》都触犯了法典。第一,这是一部表现婚外恋、非法同居和非婚生育的电影。第二,托翁的倾向性——同情敢怒敢爱、反抗传统、追求幸福的安娜;憎恶面目可憎、虚伪乏味的卡列宁(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