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着一栋栋帕夏官邸被夷为平地,我的家人处之泰然,就像我们沉着镇定地面对王子发狂、后宫妻妾抽鸦片、小孩被关在阁楼、女儿背叛苏丹、帕夏遭放逐或谋杀的种种故事以及帝国本身的衰亡。如同我们在尼尚塔石所见,共和国已废除帕夏、王储和高官,因此他们留下的空宅只成了老朽破旧的怪物。
04帕夏宅邸的拆毁(2)
尽管如此,此一垂死文明的哀婉愁怨依然包围着我们。虽然西化和现代化的欲望强烈,但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颇像被抛弃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照片。但因为没有西方或当地的东西前来填补空缺,西化的强烈欲望通常相当于抹去过往。对文化产生缩减矮化的效应,导致像我们这类家庭,虽在各方面乐见共和国的进步,却把房子布置得跟博物馆一样。我后来所谓的根深蒂固的忧伤和神秘,儿时的我觉得是枯燥和沮丧,一种呆板的烦闷,我将之设想成我祖母穿拖鞋的脚随之踏节拍的“阿拉土喀”音乐。我借筑梦来逃避它。
惟有的另一种逃避之法是跟母亲出门。因为当时的人还不习惯每天带孩子去公园或花园呼吸新鲜空气,因此跟母亲出游的日子是重大事件。“明天我要跟妈妈出门!”我会跟小我三岁的堂弟夸耀。我们走下回旋梯后,停在面对大门的小窗前,管家(当他不待在他的地下室公寓时)从窗里看得见大家出入。我对着窗中倒影检视衣着,母亲确认我的每个钮扣都扣上。一走出门,我便惊奇地叫道:“马路!”
阳光,新鲜空气,光线。我们的房子有时很暗,跨出门就像在某个夏日骤然拉开窗帘——光线刺痛我的眼睛。我牵着母亲的手,着迷地注视橱窗里的陈设:透过布满水汽的花店橱窗,仙客来花看起来像红狼;在鞋店的橱窗里,几乎看不见的铁丝把吊在半空中;跟花店一样水汽腾腾的洗衣店,是父亲把衬衫送来浆烫的地方。但是我学到的第一课是从文具店橱窗看到,窗内的学校笔记本跟我哥哥用的一模一样——我们家的种种习惯和使用的东西并非独一无二,我们公寓外还有其他人过着跟我们相像的生活。
我哥的小学——我也在一年后进这所小学——就在大家举办葬礼的帖斯威奇耶清真寺隔壁。我哥在家兴奋地大谈“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导致我猜想,就像每个小孩都有自己专属的奶妈,每个学生也有自己专属的老师。因此当我隔年走进学校,发觉三十二个小孩挤在一间教室,而且只有一个老师时,我大失所望——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外面的世界无足轻重,于是我更离不开母亲以及日常家居的舒适。
当母亲去当地的商银分行时,我会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陪她走上六个阶梯到出纳员那里:木阶之间有缝隙,我跟自己说我有可能掉下去,永远消失。“怎么不进来?”母亲会从上面叫我,我则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我会想像母亲不断消失的情景:现在我在宫殿里,现在在梯井底部……假如我们一直走到奥斯曼贝或哈比耶,经过街角,覆盖某栋公寓楼房整面侧墙的广告牌上的飞马,就会进入这些梦里。有个织补袜子兼卖皮带和钮扣的希腊老妇人,她也卖“村里来的鸡蛋”,像取珠宝似的从一只漆匣里取出一个个蛋。她的店里有一口鱼缸,在缸里浮动的红鱼张开它们吓人的小嘴,企图咬我按在玻璃上的手指,傻头傻脑地舞来舞去,总是把我给逗乐。
接下来是亚库和瓦席开的小书报店,兼卖香烟和文具,店面又小又挤,多数时候我们一走进去就出来了。有一家叫“阿拉伯店”的咖啡屋(正如同拉丁美洲的阿拉伯人通常被称做“佬”,伊斯坦布尔的少数黑人被称做“阿拉伯佬”),当店里的巨型咖啡研磨机像家中洗衣机开始隆隆作响,使我躲开它的时候;“阿拉伯佬”就会对我的恐惧宽容地笑笑。当这些过了时的店铺一家家关门,让位给一连串更现代的企业时,我和哥哥会玩一种游戏,其灵感与其说出自怀旧之情,不如说是想测试我们的记忆。游戏是这么玩的:一个人说:“女夜校隔壁的店”,另一个人便列出它后来的化身:一、希腊妇人的糕饼店;二、花店;三、手提袋店;四、表店;五、足球彩券商;六、画廊书店;七、药局。
在进入一家跟洞窟一样、一名叫阿拉丁的男人五十年来贩卖香烟、玩具、书报文具的店铺之前,我会设法请母亲为我买个哨子或几颗弹珠、着色本或溜溜球。她把礼物放进手提袋后,我立即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但原因不单是新玩具的魅力。“我们一直走到公园吧。”我母亲会说。但突然间我从脚到胸痛得厉害,知道自己再也走不下去了。多年后,当我女儿在这个年龄跟我出外散步时,她也对极其相似的疼痛表示抱怨,我们带她去看医生,医生判断是一般性的疲劳以及成长的疼痛。一旦疲劳侵蚀我的身体,刚才令我着迷的街道和橱窗便逐渐失去色彩,整个城市在我眼中开始变成黑白。
04帕夏宅邸的拆毁(3)
“妈妈,抱我。”
“我们走到马奇卡吧,”母亲会说;“搭电车回家。”
电车道打从1914年就在我们那条街来回行驶,把马奇卡和尼尚塔石跟塔克西姆广场、突内尔、加拉塔桥和其他古老贫穷、似乎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街区串连在一起。每天睡觉时,电车的忧郁乐声把我带入梦乡。我喜欢电车内的木头装潢,隔开驾驶舱与乘客区的靛蓝色玻璃门;我喜欢我们在终点站上车等开车的时候驾驶员让我玩的操作杆……在我们回家前,街道、公寓,甚至树木都是黑白影像。
05黑白影像(1)
由于习惯待在我们半昏暗的荒凉博物馆房屋里,我喜欢留在室内。底下的街道、远处的马路、城里的贫困地区,似乎跟黑白警匪片里的同样险恶。这个昏暗世界的吸引力让我一向喜欢伊斯坦布尔的冬季甚于夏季。我喜欢由秋入冬的傍晚时分,光秃秃的树在北风中颤抖,身穿黑大衣和夹克的人们穿过天色渐暗的街道赶回家去。我喜欢那排山倒海的忧伤,当我看着旧公寓楼房的墙壁以及斑驳失修的木宅废墟黑暗的外表——我只在伊斯坦布尔见过这种质地,这种阴影——当我看着黑白人群匆匆走在渐暗的冬日街道时,我内心深处便有一种甘苦与共之感,仿佛夜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街道、属于我们的每一件东西罩在一大片黑暗中,仿佛我们一旦平平安安回到家,待在卧室里,躺在床上,便能回去做我们失落的繁华梦,我们的昔日传奇梦。同样的,当我看着暮色如诗般在苍白的街灯中降临,吞没城里的贫困地区时,知道至少在晚上,西方的眼光窥视不到我们,外地人看不见我们城里可耻的贫困,是令人宽慰的事。
古勒有幅摄影作品,捕捉了我童年时代的僻静街巷,街巷中的水泥公寓和木造屋并排而立,街灯空茫,明暗对照的黄昏——对我来说它代表这个城市——已然降临。(如今水泥公寓虽已挤走老旧的木造房屋,气氛却不变。)这幅摄影吸引我之处不只在于使我忆起童年时代的卵石子路,也不在于卵石路面、窗子的铁护栏或摇摇欲坠的空木屋,而是因为它暗示着,随着夜的降临,这两个走在回家路上、身后拖着细长影子的人,其实是在将夜幕披盖在城市上。
在1950和1960年代,我跟每个人一样,喜欢看全城各地的“电影摄制组”——车身两侧有电影公司标志的面包车;以发电机发动的两盏巨灯;喜欢别人叫他们souffleurs(法文)的提词人,他们在浓妆艳抹的女演员和罗曼蒂克的男主角忘了台词时,得隔着发电机的轰鸣声扯着嗓子叫喊;戏外跟小孩和好奇的围观民众挤来挤去的工作人员。四十年间,的电影工业不再(大半由于导演、演员和制片人不称职,但也因为无法跟好莱坞竞争),电视依然播放这些黑白老片,而当我看见黑白影像的街道、老花园、博斯普鲁斯的景色、倾颓的宅邸和公寓时,有时我竟忘了自己在看电影。惆怅令我茫然,时而感觉自己仿佛在观看自己的过去。
十五至十六岁的我,想像自己是描绘伊斯坦布尔街道风貌的印象派画家,画一颗颗卵石是我的最大乐趣。在积极的区议会开始毫不留情地将卵石路铺上柏油之前,城里的和“多姆小巴”司机对石子路面所造成的损害大表不满。他们也抱怨为下水道、电力、一般维修而进行的挖路工程没完没了。挖路时得把卵石一颗颗撬掉,这让工程无止境地拖下去——尤其当底下发现拜占庭时代的回廊的时候。完工时,我喜欢看工人把一颗颗卵石放回原位——以一种令人陶醉、充满韵律的技术。
我童年时代的那些原木宅邸以及位于后街较为简朴的小木房,处于一种断垣残壁的迷人状态。由于贫困且无人照料,这些房子从不上漆,岁月、尘土和潮气的结合使木头颜色渐渐变深,赋予它那种特殊的颜色,独特的质地,小时候我在后街区看见的这些房子十分普遍,我甚至以为黑色是它们的原色。有些房子是褐底色调,或许贫民区的房子根本不识油漆为何物。但18世纪和19世纪中叶的西方旅人形容有钱人家的宅邸油漆鲜艳,认为这些私宅和其他的富裕风貌具有某种丰饶有力之美。小时候的我时而幻想为这些房子上漆,尽管如此,失去黑白布幕的城市仍教人心悸。到夏天的时候,这些老木屋干透,变成一种黯淡、灰质、打火匣般的褐色,你能想像它们随时都可能着火;在冬季漫长的寒流期间,雪和雨水同样让这些房子蒙上朽木的霉味。老旧木造的僧侣道堂情况亦同,共和国禁止这些地方作为朝拜场所,如今多已废弃,除了街头流浪儿、鬼魂和古物收藏者之外没人会去。这些房屋使我产生了相同程度的恐惧、担忧和好奇:当我从颓垣断壁外透过潮湿的树丛探看破窗残宇时,心头便掠过一股寒意。
05黑白影像(2)
由于我是以黑白影像来理解这城市之灵魂,因此少数目光独到的西方旅人的线条素描——例如柯布西耶,以及任何一本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附黑白插图的书都令我着迷。(我整个童年都在等待,却始终不见漫画家埃尔热以伊斯坦布尔作为丁丁历险的背景。当第一部丁丁电影在伊斯坦布尔拍摄时,某盗版书商发行了一本名为《丁丁在伊斯坦布尔》的黑白漫画书,作者是本地漫画家,他把自己从电影画面的演绎,跟丁丁其他历险的画面拼凑在一起。)旧报纸也使我着迷,每回读到谋杀、自杀或抢劫未遂的报道,我便嗅到一股长久压抑的儿
时恐惧。
在某些地方——帖佩巴丝、加拉塔、法蒂赫、翟芮克、博斯普鲁斯沿岸的几个村落、于斯屈达尔的后街——也看得见我所描述的黑白之雾。在烟雾弥漫的早晨,在刮风的雨夜,海鸥筑巢的清真寺圆顶看得见它;在汽车排放的烟雾、烟囱冒出的袅袅煤烟、生锈的垃圾桶、冬日里空寂荒芜的公园和花园以及冬夜里踩着泥雪赶回家的人群中也看得见它;这些都是黑白伊斯坦布尔忧伤的喜悦。几百年没再喷过水的残破喷泉,贫民区里被遗忘的清真寺,突然出现的一群身穿白领黑褂的学童,沾满泥巴的老旧卡车,因岁月、灰尘和无人光顾而更加昏暗的小杂货店,挤满落魄失业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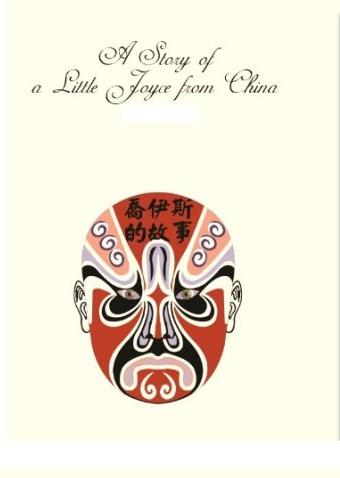
![[夜访吸血鬼]吸血鬼莱威尔 作者:银色徽章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