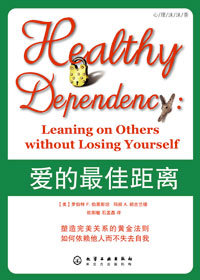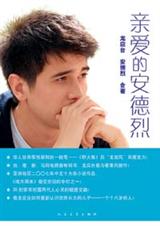我亲爱的甜橙树 作者:约瑟·德维斯康塞罗-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说。他这人有时候也很能让人腻烦。
“你主修什么?”我问他。“性变态吗?”我是成心逗他玩。
“你这算什么——滑稽?”
“不,我跟你逗着玩呢,”我说。“听着,嗨,路斯。你是个聪明人。我需要你的忠告。我目前遇到了可怕的——”
他冲着我重重地呻唤了一声。“听着,考尔菲德。你要是能坐在这儿好好喝会儿酒,好好谈会儿——”
“好吧,好吧,”我说。“别着急。”你看得出他不想跟我讨论任何严肃的问题。那般聪明人就是这个毛病。他们从来不肯跟你讨论任何严肃的问题,除非是他们自己想谈。因此我就只跟他讨论些一般性问题。“不跟你开玩笑,你的性生活怎样?”
我问他。“你是不是仍旧跟你在胡敦念书时候的那个姑娘在一起?那个极可爱的——”
“老天爷,不啦,”他说。
“怎么啦?她出了什么事啦?”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既然问起,我想她这会儿大概在新汉普夏当婊子啦。”
“这样说不好。要是她过去待你挺不错,老让你跟她发生最亲密的关系,你至少不应该这么说她。”
“哦,天哪!”老路斯说。“难道这是一次标准的考尔菲德谈话吗?我马上要知道。”
“不,”我说,“不过你这样说总不太好。要是她过去待你挺不错,老让你——”
“难道我们非照着这个可怕的题目谈下去不成?”
我不再说下去了。我有点儿怕他站起来离开我,要是我不住嘴的话。所以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又要了一杯酒,我很想喝个烂醉。
“你现在跟谁在一起?”我问他。“你愿意告诉我吗?”
“你不认识。”
“是吗,不过到底是谁呢?我也许认得她。”
“一个位在格林威治村的姑娘。女雕刻家。你要是非知道不可的话。”
“是吗?不开玩笑?她多大啦?”
“我从来没问过她,老天爷。”
“嗯,大概有多大啦?”
“我想她都快四十了,”老路斯说。
“都快四十了?嗯?你喜欢?”我问他。“你喜欢这么大年纪的女人?”我之所以这样问他,是因为他的性知识的确非常丰富。我认识的真正有性知识的人并不多,可他确是其中的一个。他早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破了身,在南塔基特。一点不假。
“我喜欢成熟的女人,要是你问的是这个意思的话。当然啦。”
“你喜欢?为什么?不开玩笑,她们在性方面是不是更好一些?”
“听着。咱们把话说清楚。今天晚上我拒绝回答任何一个标准的考尔菲德问题。你他妈的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我有一会儿没再说话。我让我们的谈话中断了一会儿。接着老路斯又要了杯马提尼,还叫掌柜的再去掉点儿甜味。
“听着,你跟她在一起有多久啦,这个会雕刻的姑娘?”我问他。我真是感兴趣极了。“你在胡敦的时候认识她吗?”
“不认识。她到这个国家还只几个月哩。”
“真的吗?她是打哪儿来的?”
“好象是打上海来的。”
“别开玩笑!她是中国人,老天爷?”
“当然。”
“别开玩笑!你喜欢吗?象她这样的中国女人?”
“当然。”
“为什么?我很想知道——我的确想知道。”
“我只是偶然发现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有道理。你既然问了。”
“真的吗?你是说‘哲学’?你的意思是不是包括性一类问题?你是说中国的更好?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一定是中国,老天爷。我刚才说的东方。
咱们难道非这么疯疯癫癫谈下去不可吗?”
“听着,我是跟你谈正经呢,”我说。“不开玩笑。为什么东方的更好?”
“说来话长,老天爷,”老路斯说。“他们只是把性关系看成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关系。你要是以为我——”
“我也一样!我也把它看成——你怎么说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我的确是这样看的。可是关键在于跟我发生关系的是他妈的什么人。要是跟我发生关系的是那种我甚至都不——”
“别这么大声,老天爷,考尔菲德。你要是不能把你的声音放低些,那我们干脆就别——”
“好吧,可是听我说,”我说。我越说越兴奋,声音就未免太大了一点。有时候我心里一兴奋,讲话的声音就大了。“可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说。“我知道那种关系应该是肉体和精神的,而且也应该是艺术的。可我的意思是,你不能跟人人都这样——跟每一个和你搂搂抱抱的姑娘——跟她们全都来这一手。你说对吗?”
“咱们别谈了吧,”老路斯说。“好不好?”
“好吧,’可是听我说。就拿你和那个中国女人来说,你们俩的关系好在什么地方?”
“别谈了,我已经说过啦。”
我问的都有点儿涉及私人隐事了。我明白这一点。可老路斯就是这些地方让你觉得不痛快。我在胡敦的时候,他会叫你把你自己最最隐秘的事情形容给他听,可你只要一问起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他就会生起气来。这般聪明人就是这样,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在发号施令,就不高兴跟你进行一场有意思的谈话。他们自己一住嘴,也就要你住嘴,他们一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也就要你回到你自己的房间。我在胡敦的时候,老路斯一向痛恨这样的事——那就是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向我们一伙人谈完性问题后,我们还聚集在一起继续聊一会儿天。我是说另外那些家伙跟我自己。在别人的房间里。老路斯痛恨这类事情。他只喜欢自己一个人当大亨,等他把话说完,就希望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不再言语。他最害怕的,就是怕有人说出来的话比他高明。他的确引得我很开心。
“我也许要到中国去。我的性生活糟糕得很呢,”我说。
“自然啦,你的头脑还没成熟。”
“不错。一点不错。我自己也知道,”我说。
“你知道我的毛病在哪儿?跟一个我并不太喜欢的姑娘在一起,我始终没有真正的性欲——我是说真正的性欲。我是说我得先喜欢她。要是不喜欢,我简直对她连一点点混帐的欲望都没有。嘿,我的性生活真是糟糕得可怕,我的性生活真是一塌糊涂。”
“这是最自然不过的啦,老天爷。我上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就跟你说了,你该怎么办。”
“你是说去找精神分析家?”我说。他上次告诉我该做的是这个。他父亲就是个精神分析家。
“那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老天爷。你怎样处理你自己的私生活,那完全不是我他妈的事儿。”
我一时没吭声,我在思索。
“我要是去找你父亲用精神分析法治疗,”我说。“他会拿我怎么办呢?我是说他会拿我怎么办呢?”
“他不会拿你他妈的怎么办。他只是跟你谈话,你也跟他谈话,老天爷。有一点他会帮你做到,他会让你认识自己的思想方式。”
“我自己的什么?”
“你自己的思想方式。你的思想按照——听着。我不是在教精神分析学的基础课。你要是有兴趣,打电话跟他约个时间。要是没有兴趣,就别打电话。我一点也不在乎,老实说。”
我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嘿,他真让我开心。
“你真是个够朋友的杂种,”我对他说。“你知道吗?”
他正在看手表。“我得定了,”他说着,站了起来。“见了你真高兴。”他叫来了掌柜的,要他开帐单。
“嗨,”我在他离开之前说。“你父亲对你作过精神分析没有?”
“我?你问这干什么?”
“没什么。他作了没有?有没有?”
“说不上分析。他帮助我纠正某些地方,可是没必要作一次全面的精神分析。你问这于什么?”
“没什么。只是一时想起。”
“呃。别为这种事伤脑筋,”他说。他把小帐留下,准备走了。
“再喝一杯吧。”我跟他说。“劳驾啦。我寂寞得要命。不开玩笑。”
他说没法再喝一杯。他说他已经迟了,说完他就走了。
老路斯。他确实非常讨人厌,可他的语汇确实丰富。我在胡敦的时候,全校学生就数他的语汇最丰富。他们测验过我们一次。
我坐在那儿越喝越醉,等着老提娜和琴妮出来表演节目,可她们不在。一个梳着波浪式头发,样子象搞同性爱的家伙出来弹钢琴,接着是一个叫凡伦西姬的新来姑娘出来唱歌。她唱得并不好,可是比老提娜和琴妮要好些,至少她唱的都是好歌曲。
钢琴就放在我坐的酒柜旁边,老凡伦西姬简直就站在我身旁。我不断跟她做媚眼,可她假装连看都没看见我。在乎时我大概不会这么做,可我当时已喝得非常醉了。她唱完歌,马上就走出房间,我甚至都来不及邀请她跟我一块儿喝一杯,所以我只好把侍者头儿叫来。我叫他去问问凡伦西姬,是不是愿意来跟我一块儿喝一杯。他答应了,可他大概连信都不会给她捎去。这些家伙是从来不给人捎口信的。
嘿,我在那个混帐酒吧间里一直坐到一点钟光景,醉得很厉害。我连前面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不过有件事我很注意,我小心得要命,一点没让自己发酒疯什么的。我不愿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让人问起我的年纪。可是,嘿,我连前面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只要真正喝醉了酒,就会重新幻想起自己心窝里中了颗子弹的傻事来。酒吧间里就我一个人心窝里中了颗子弹。我不住伸手到上装里面,捂着肚皮,不让血流得满地都是,我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已受了伤。我在努力掩饰,不让人知道我是个受了伤的婊子养的。最后我忽然灵机一动,想打个电话给琴,看看她是不是回家了。因此我付了帐,走出酒吧间去打电话。我老是伸手到上装里边,不让血流出来。嘿,我真是醉啦。
可我一走进电话间,就没有心情打电话给琴。
我实在醉得太厉害了,我揣摩。因此我只是给老萨丽。海斯打了个电话。
我得拨那么二十次才拨对号码。嘿,我的眼睛真是瞎啦。
“哈罗,”有人来接混帐电话的时候我就这样说。我几乎是在大声呦喝,我醉得多厉害啊。
“谁呀?”一位太大非常冷淡的声音说。
“是我。霍尔顿。考尔菲德。请叫萨丽来接电话,劳您驾。”
“萨丽睡啦。我是萨丽的奶奶。你干嘛这么晚打电话来,霍尔顿?你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啦?”
“知道。我有话跟萨丽说。十分要紧的事。请她来接一下电话。”
“萨丽睡啦,小伙子。明天再来电话吧。再见。”
“叫醒她!叫醒她,嗨。劳驾。”
接着是另一个声音说话。“霍尔顿,是我。”
正是老萨丽。“怎么回事?”
“萨丽?是你吗?”
“是的——别呦喝。你喝醉了吗?”
“是的。听着。听着,嗨。我在圣诞前夕上你家来。成吗?帮你修剪混帐的圣诞树。成吗?成吗,嗨,萨丽?”
“成。你喝醉了。快去睡吧。你在哪儿?有谁跟你在一起?”
“萨丽!我上你家来帮你修剪圣诞树,成吗?
成吗,嗨?”
“成。快去睡吧。你在哪儿?有谁跟你在一起?”
“没有人。我,我跟我自己。”嘿,我真是醉啦!我依旧用一只手捂着我的心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