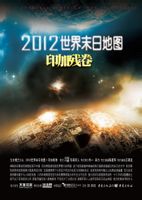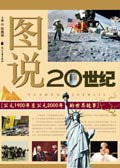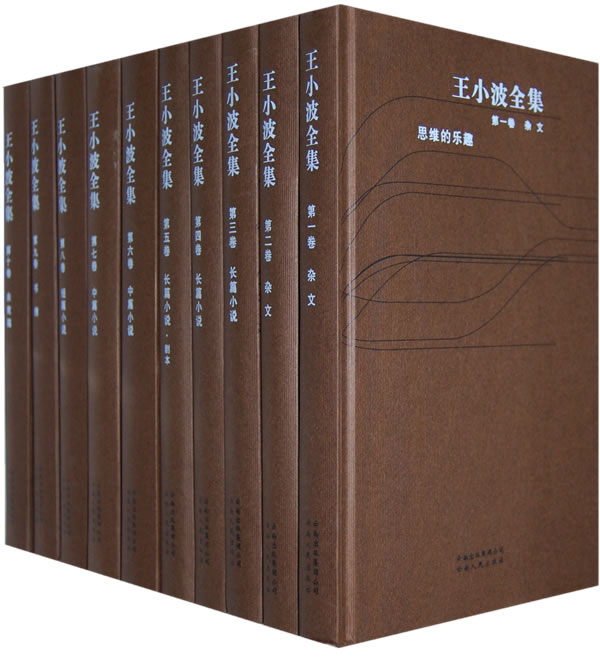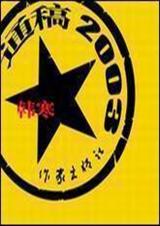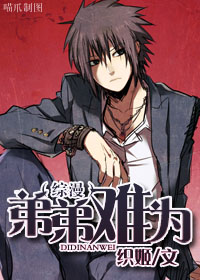2005年第05期-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按照时间推算,朱元璋出生时,距离那场大战过去了五十年;朱元璋童年甚至少年时,这位老人应该依然健在。我们可以想见,这么一位经多识广的老兵,对于少年朱元璋的心智影响想必不会小。
朱元璋的母亲是陈家二姑娘,据说,此女自幼开朗大方,深得乃父喜爱。于是,饱经沧桑的老先生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历史掌故和各地风土人情。有一种说法认为,长大后,陈二娘能歌善舞,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常常大受欢迎。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下朱元璋后,尽管家境千难万难,父母还是勒着省着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大约一年多将近两年的书。随后,为割草放牛、补贴家用而辍学。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继续学完《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为他打下了文字根底。并且,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打开了他的眼界与心胸。
公元1344年,即元顺帝至正四年,淮河流域遭遇大旱、蝗灾与瘟疫,半月之间,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大哥与大哥的儿子先后死去。一个虽然贫穷但不无温馨的家庭,霎时变成人间地狱。
当时的情形至为悲惨:朱元璋与活下来的二哥身无分文,没有棺木,没有寿衣,没有墓地,兄弟二人用门板抬了草席裹着的亲人,走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时,下起霹雳暴雨,抬着门板的绳子断了,二人躲雨并找人借绳子。结果,回来后大吃一惊地发现,山土崩塌,已经将亲人埋在一个新的山包之下。当时,为了得到一块立锥之地以便埋葬亲人,他们兄弟二人曾经苦苦哀求一个大户,遭到拒绝;此时,幸亏这块山坡地属于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家,他们才就此千恩万谢地葬下亲人。
这段往事,对于朱元璋创巨痛深。以至于数十年后,他已经当了皇帝,然而每每触及此事,仍然嚎啕痛哭,不能自已。并且多年不许臣民为自己庆贺生日,原因是会令他想起父母死时的惨状。
这一年,朱元璋十六岁。
不久,十里八乡之内,连树皮革根都被吃光,朱元璋走投无路,出家做了和尚。在此后的八年佛门生活中,至少有三年以上,他是在云游四方、托钵化缘中度过的。这种与沿街乞讨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的生存方式,可能是在中国观察人间冷暖、体会世态炎凉、领略人类各色嘴脸的最好方式。很久以后,朱元璋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经万分感慨地形容自己:“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具体遭遇,然其饥寒交迫、身心备受煎熬的情形却可见一斑。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青春成长期的经历,于人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古人似乎亦可作如是观。我们找不到更多资料证实朱元璋在此期间究竟遭遇到了什么。当时的史料过于简略,朱元璋自己的回忆,则以形容居多,具体事例太少;后世的传记作品涉及此处时,或一笔带过,或多为想象。好在从古至今同类的事例堪称触目皆是。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倘不是身陷绝境,一般人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其次,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将人逼上新的绝境的概率大大增加。
经历过这种残酷生存方式打磨的人,比较起来,更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形:那些为了讨回自己的工钱甚至不惜自戕的民工,大约是他们之中最为良善的一端;而那些于绝望之中铤而走险,充斥于当今各类传媒的犯罪报道,则告诉了我们另外一端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犬儒主义算计和“胆小不得将军做”之类亡命徒哲学,便自然而然地分别成为上述两个极端的追求。
善待生命
■ 梅 洁
我发现,在经历了人生太多的苦难之后,我们才会警觉除却人类自身和我们自己的苦难外,我们身边的另一类生命所遭际的苦难与不幸。它们面临的残酷境遇,恰恰是我们带给它们的。比之人类,它们的弱小、它们的无辜都使我产生深深的忧虑。
儿童的天性中是最喜爱小动物的,而儿童的天性中又是最能毫无顾忌地戕害弱小生命的。这是儿童天性伪悖论。我在这种悖论中长大……
蟋蟀“比尔”及其他
童年的夜晚,仿佛遍地响着蟋蟀的叫声,那此起彼伏,抑或是无休无止的声音使夜晚充满了诱惑。
在这些夏日的夜晚,我总是和弟弟、申子哥他们一起溜出家门,拿上手电筒,或顺着墙边、或来到一片长满灰灰菜的生地里逮蟋蟀,我们那时不叫它们蟋蟀,而是叫蛐蛐儿。白天,我们早已做好了各种不同大小的装蛐蛐儿的泥罐子。泥罐子做得精致而光滑,内里掏着一些拐弯抹角的洞,地道似的,我们企图让逮住的蛐蛐儿住进去有家的感觉。泥罐子上面我们做着泥盖,防止蛐蛐儿逃跑;泥盖上留着瞭望口,好观察它们在房子里的动静。
我们撬石搬土,在一些潮湿的地方寻找我们心中的“勇士”。这些“勇士”都是公蛐蛐儿,我们能认出公母,我们甚至能根据鸣叫声音大小来辨别它们的性别和年龄。我们常常能逮住一些被我们称为“王子”、“公爵”的漂亮英俊的公蛐蛐儿,也能逮住一些叫“关公”、“赵云”的英勇善战的公蛐蛐儿。我们不要母蛐蛐儿,因为母蛐蛐儿不会“战斗”,它们从不参与“男人们”的战争。我们有严格的规矩,谁逮住的蛐蛐儿算谁的,装进各自的泥罐儿,以待第二天“决斗”。泥罐儿可以互相赠送,但决不允许相互偷蛐蛐儿,谁偷谁是“美国”,立即不再跟他玩。那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人们把坏人坏事都称为“美国”。
有一次申子哥的弟弟偷了我弟弟的“赵云”,且不小心把“赵云”强健的腿弄掉了一只,我弟弟大哭起来。我弟弟的“赵云”剽悍英俊,它有着漂亮的黑褐色,脑袋上两只细长的触须就像大将赵云手中百战百胜的长枪,他还有两条强劲健美的后腿,决斗时两腿蹲得很长,很有力!它的两只尾须翘起,像扇起的两翼黑色披风!夜间,它鸣叫的声音也特别嘹亮,能从弟弟睡觉的屋子传到我睡觉的屋子,“姐,听见了吗?‘赵云’……”弟弟在那间屋子里喊。“听见了……”我扯起嗓子愉快地回答。我和弟弟因有“赵云”而骄傲着。现在,“赵云”残废了,弟弟和我都哭得不吃饭。
申子哥执仗正义,揍了他弟弟一顿之后,随之将他的“关公”赔偿了我弟弟。他弟弟好几天被我们骂成“美国”,不理他。“关公”是我们仰慕敬畏已久的蛐蛐儿,它不仅有黑里透红的身体,而且十分的勇敢顽强,每次决斗,它不是咬断对方的腿,就是把对方的触须给拔下来,弟弟的“勇敢者1号”和“勇敢者2号”都曾在“关公”阵前毙命。申子哥将红色“关公”赔给我们,那一刻,我们对申子哥也充满了敬畏。后来,申子哥成为我们“家属院”十几个孩子的“王”。
一开始,我是认不准公蛐蚰儿和母蛐蛐儿的。有一次,我把自己逮住的一只肥硕的大蛐蛐儿装进我的蛐蛐儿罐儿里,罐儿里有一只弟弟送我的蛐蛐儿,这只蛐蛐儿名叫“比尔”,弟弟给它起的名字——弟弟在看一本连环画,“比尔”可能是连环画里的什么人物。“比尔”在与申子哥他们的蛐蛐儿决斗时,表现得不英勇,总是退让、逃跑,于是弟弟把它送给了我。我想,我那只肥硕的大蛐蛐儿进去后,三下五去二会把“比尔”打得落花流水的。没想到,相反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大蛐蛐儿和“比尔”非常友好,它们用长长的触须相互碰了碰,然后又很久地碰着不动,像是在紧紧地握手。过了一会儿,它们的身体开始接触,先是拥抱,不久,尾与尾便接在了一起。很久很久,它们都很安详、很平静。不像我在弟弟和申子哥的罐儿里看到的现象:来一个“不速之客”,立即“吱吱”地咬起来,直到缺胳膊断腿。其实,更多的时候,我是不喜欢看到这种场面的。我主要是觉着断了腿的蛐蛐儿,身体一定很疼。
我把罐儿捧给弟弟和申子哥看:“看呢,它们不打仗……”我豁着牙嘻嘻地笑着——我直到11岁两只前门牙都没长出来,妈说是我总用舌头舔的过。要按现在的说法可能是缺钙。
谁知弟弟和申子哥他们看完之后,相视着一笑——他们笑得很腼腆很难看的样子,然后说:“母的……”然后又说:“连呢……”我长大之后回忆这句话时,我想他们当时可能是说“恋呢”。说完,他们就不由分说把我的那只大蛐蛐儿捉住,恶狠狠地分离了它们,并一扬手把它摔出老远,他们说:“不要母的……”我那只大蛐蛐儿肯定被摔死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比尔”也死了。它歪倒在罐儿里,腿脚僵直,很痛苦的样子。
我那一天也很难过,其实,也说不清为谁。为我那只母蛐蛐儿还是为“比尔”?还是为别的什么……
黄儿
黄儿是舅奶奶家的一只母狗。我看到它时,它已很老了,没人记住它的年龄。它有点枯瘦如柴,肚子总是吸得扁扁的,脊梁的肋骨很突出;尾巴也不蓬松卷曲,总是有气无力地拖在身后,一点也不好看,像只可怜、孤独的老狼。我跟它开始有感情是在小妹生下之后,小妹拉巴巴后,只要母亲唤一声“黄儿,喔——”,它就迅速地跑来,把地上的巴巴舔得一干二净。然后走到门槛外边,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望着我们。有时它望我们望很久,有时,我发现它眼角有泪水流下来,很苍老的泪水。
“妈,黄儿在哭……”我对母亲说。
“它想它的孩子……”母亲说。
我们住的这山里,人烟很稀,好几里地才有一两户人家,没有人家就没有黄儿的同伴。黄儿这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是山里那个卖货郎路过舅奶奶家时,他随身的那只雄健的公狗和黄儿相爱了。后来,黄儿就怀孕了,生了三只小狗娃。黄儿还在哺乳期时,舅爷爷就把三只毛茸茸的小狗娃偷走,换了几烟锅鸦片。黄儿失去了儿女,日夜狂吠不止。舅奶奶拿热毛巾给黄儿敷奶,它的奶因没有小狗娃吃奶水已肿胀得通红。“老剁头的,害死黄儿……”舅奶奶骂舅爷爷。“你狗都不如!你有本事屙啊……”舅爷爷是咒骂舅奶奶不会生养。黄儿终于痛苦不堪,疯狂地出走了,好几天没有回来。夜里,舅奶奶听见它在后山上狂吠,它在找它的孩子。7天后,它无望地回来了,瘦成一把骨头,再没“返醒”过来……“返醒”是鄂西的土语,指“恢复”的意思。
母亲讲黄儿的故事时,很忧伤,这故事肯定是舅奶奶讲给母亲的。我不敢和舅奶奶说话,我感觉她很古怪,很陌生,她有时想和我们亲近,有时却又故意疏远着我们,带着一种敌意。
有一次,我抱着小妹到水塘那边的石坡上玩,回家时把小妹的一只小鞋弄丢了,正着急呢,黄儿叼着那只小鞋“颠颠地”回来了。放下小鞋,它依然一声不吭地蹲在门槛外边望我们,望很久。
有一次,母亲到城里看父亲和哥哥,交代我看好弟妹。当晚山里下起了大雨,雨水从山墙沟流进了屋里,我害怕极了,我让弟妹坐在床上别动,我蹲在木板凳上为弟妹煮了萝卜白米粥,因为我还没有锅台高。我不知放多少水,把萝卜粥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