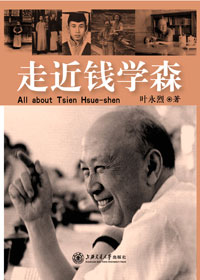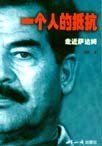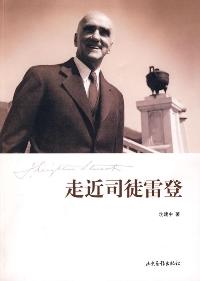走近艾滋病 作者:李锦华-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只有43户人家的村寨,就有36户没有房子住,这些人只能常年栖身在岩洞中。
有一个村,改革开放以后全村人劳动致富的热情很高,年人均收入从过去的150元增加
到了1000元,成了县上的先进典型。但从1987年开始有人染上吸毒后,这个村的许多人因
吸毒而丧失了劳动力。农业生产一年不如一年,1990年全村种植甘蔗50亩,只占1987年
种植面积的27%。
那些被毒品毁灭了的村寨,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困兽,蜷缩在破烂的草棚里,潮湿的岩
洞中。
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越穷越要吸,越吸就越穷,哪怕家中还有一只鸡、一碗米,甚至
一个鸡蛋,都要拿去换毒品来吸。
染上毒品恶习的村民,便精神萎靡不振,再也无心下地去生产劳动。
丰硕的田地荒芜了。
欢乐的村寨凋敝了。
过去,傣族人家是从来不留人守家,出门也从不锁门,竹楼始终是为客人开着的。走过
此地的人,无论你认不认识主人,也不管主人在不在家,客人可以自己走进竹楼,可以自己
做饭吃,也可以自己烧水喝。如果累了,还可以在竹楼上甜甜美美地睡上一觉。
可是,自毒品侵入了这些地方后,偷鸡摸狗,凿门入户的事一天天多起来,人们出门怕
家里的财物被盗,回家又怕地里的庄稼遭偷,弄得相邻的村民人人自危,不能安生。
更可悲的是,有的吸毒者为了获取毒资,不得不卖儿卖女、卖妻、卖淫、卖家产,轻者
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有的甚至走上了盗窃、抢劫、诈骗、贪污等犯罪的道路。
认识艾滋病毒携带者
1991年秋天,我因患脑神经衰弱经常失眠,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中医———
欧医生。
欧医生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开专家门诊,于是我就每星期三到医院一次,开上三副中药,
刚好服用一周。
那时候我们卫生报已经改为周报,我每次去看病就顺便带上几张新出的报纸送给欧医
生,也让他散发给周围的同事。
一次,欧医生为我开好处方后就拿起放在桌上的报纸翻看,突然,他抬起头来问我:
“你们还开辟一个专栏来宣传艾滋病。说实在的,你见过几个真正的‘艾滋病’?”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艾滋病的宣传搞了好长时间,其实我一个也没见过。很想见一
下,看看这些人的临床体征究竟是什么样。可惜没这种机会,因为医院里面根本不收这类病
人,其它地方又找不到。”
“你找不到。我可是不用找人家就自己来。”欧医生苦笑了一声。
“你治疗艾滋病人?”我非常惊讶。
朋友在给我介绍欧医生的时候说,欧医生虽然年轻,却相当富有临床经验。他们家是中
医世家,他从小就跟着祖父和父亲在中药房里长大,后来又考上了中医学院,理论和实践上
都相当有一套。特别是他对肿瘤、乙肝、脉管炎等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颇有独到之处。没想
到居然还能够治疗被称之为“世界瘟疫”的艾滋病。
“你进门时遇到的那个人就是。”欧医生淡淡地说。
“进门时……”我竭力回忆刚才的情景。
欧医生上专家门诊时病人很多,所以我每次来都是安排在5点多到达医院,这时病人已
经少了,稍微等一会,5点半左右开好处方送到一楼划价拿药,基本就不用排队等候。今天
我才走到门口就很高兴,因为诊室里一个病人也没有,这是平时很少遇到的事。进门时我确
实碰到个男的刚好拿着处方出去。那人高高的个子,好像穿一件米灰色的长风衣,因为仅仅
是我进门他出门的那么一会儿工夫,我根本就没留意那人的年龄和相貌。
“他在我这里看病半年多了。朋友介绍来的,没办法。”欧医生低着头整理抽屉里的书
本。“其实,我哪有能耐去治艾滋病。什么叫艾滋病我还是从见了他以后才去找了点资料来
看看。这种病,中医西医的书籍都没有任何发病原理和治疗方案的记载。”
“那你怎么给他医?”我更为惊讶。
“怎么治?你们报纸上宣传的都是100%死亡,本世纪无药可治。我又不是神仙。不过
是受人之托,死马当活马医而已。”
“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细细品味着欧医生的这句话,突然为这个毫不相干的艾滋病人感到一阵悲哀。在医院
里,医生最无奈的就是这句话,而病人最害怕医生说出的也是这句话。
“他是如何感染上的?”我问话的声音很低。
“出国进修。目前基本情况还好,潜伏期。”欧医生的回答很简短。
“我能见见这个人吗?”我望着欧医生。
“见他?”欧医生吃惊地抬起头。
“你刚才不是笑话我搞了这么长时间的艾滋病宣传,连个真正的病人都没见过。他下次
什么时间来看病,我专门来见识见识这种特殊的病例,怎么样?”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这……”欧医生犹豫了。“我先得问他一下。朋友再三交待,一定要为他保密。我们
也是朋友,又是同行,你现在又办什么咨询,我才对你讲的。这样吧,你下个星期三来再
说。”
到了星期三,我特意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医院,没想到欧医生把我叫到外面的走廊上低声
对我说:“对不起,他不同意见你。”
“为什么?”我顿感失望。
“这事怪我没处理好。我说有个记者要见他,他一听记者脸马上就变了。知道你这段时
间在我这里治疗,他就说最近不来医院了,让他弟弟代他来拿药,病情有什么变化就在电话
里告诉我。唉,我当时应该说你是本院的医生就好了。”欧医生有些后悔地说。
话已到了这个份上,我只有叹气遗憾了。
后来,我的失眠症状好转就没有再去医院。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陪家人到公园游玩,没想到在那里碰上了欧医生。
欧医生和一个身材瘦高,穿件淡绿色茄克衫的男子迎面走来。欧医生似乎在给那人竭力
地解释着什么,那男的一声不吭,面无表情地默默走着。
见到我,欧医生显得十分热情,他叫住了转身退开的那个男子,向我介绍那是他的朋
友,但他却向那人介绍我和他是一个医院的同事,搞妇产科的。
我困惑不解地瞪着欧医生,却发现他悄悄地向我使眼色,意思是要我注意这个男子。
我留意打量了此人一眼(欧医生没有介绍我们双方的姓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清瘦
的脸庞,五官长得也还端正和谐,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镶边的金丝眼镜,一副文弱书生的
模样,可我发现那镜片后面的目光显得呆滞木然,里面似乎包含着很深重的忧伤。
听到欧医生的介绍,他很机械地咧嘴冲我笑笑,然后弯腰来了个日本式的鞠躬。
我当时正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没料到对方并没有握手的意思,幸亏我的反应还算灵敏,
马上也朝他弯腰还了一礼。
欧医生邀请我和他们到湖中划船,我看到那个男士虽然非常礼貌,但始终不言不语一副
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感到不大方便,就婉言谢绝了。
第二天,我给欧医生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要编造我是医院搞妇产科的,是不是有什
么为难的事,需不需要帮忙。
没想到,他说:“哎呀,你怎么那样笨哪,还当什么记者?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
现实生活的尴尬
警车沿着坎坷不平的盘山路行驶,车窗外,山乡那明丽璀璨的秋色似一幅珍藏已久的彩
色图片,渐渐地掀开了我记忆中的扉页。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群龙腾虎跃的身影,一片童音
未改的呐喊声,欢呼声……
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山顶上有一所乡办的小学,体育活动开展得非常
好,一连几年在市里的中小学体育运动比赛中夺得了多项冠军。
警车终于在山顶上的一座围墙外停下了,市公安局派来陪我采访的刑侦队李队长跳下
车,帮我打开车门,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干警已从大门里迎了出来。
我却坐在车上不想下去。
我的情感上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的确是我曾经到过的那所小学,而且我曾经为
该校如何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通讯。警车还没有停稳时,我却已明明
白白地看清了挂在大门上“强制戒毒所”的牌子。
李队长以为我是晕车,连忙过来搀扶我。
我强挣出笑脸谢绝了他,怀着一种十分苦涩的心情走进了这所当年是学校如今变成戒毒
所的大院。
十年前,我作为省卫生报的记者,曾随着省卫生检查团到过这所小学校来检查卫生设施
和学生的健康情况。记得那天来到学校时,刚好是学生课间休息在打篮球,宽敞的球场四周
站满了围观的学生,一个个兴致勃勃显得比打球的队员还要激动。虽然不是比赛,但是场上
的小队员却打得认真激烈,生龙活虎,有个队员为了争夺一个球,竟然抱着篮球从另一个队
员的胯下泥鳅样地钻了过去,还翻了两个跟斗,把场上的队员也撞倒了好几个,引起了球场
上一片喝彩声、抗议声,还有临时小裁判命令停止的口哨声……
如今,那宽敞的球场依旧,球场那一排花坛依旧,那围成四合院的房屋依旧,可原来楼
下的一排教室已改成了戒毒学员的住房、政治学习教室、健身房、医务室;楼上原来的教
室、教务处、校长办公室已改成了公安干警、协管人员以及医务人员的宿舍;那曾经矮得能
够飞出篮球的围墙上增添几道长长的铁丝网;那雪白围墙上,原来书写着的是“锻炼身体、
保卫祖国”的大红标语,如今却改成了“有毒必肃、吸毒必戒、扫除毒害”;当年我们卫生
检查团坐着观看学生打球的走廊上,现在坐着的是一排瘦骨嶙峋、面容憔悴,正在等待服药
治疗的戒毒者。
我悲怅地举目望着四周青翠的山峦。青山依旧,楼房依旧,可物是人非。为什么会是如
此惊心动魂的改变?
为什么?
我想起了前不久在一个县的强制戒毒所采访时听到的一个故事。
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军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赶来这个县的戒毒所看望女儿,没想到,他
来到戒毒所却没有随着其他家属慌慌忙忙进去看人,而是在大门外抚摸着围墙外的建筑物放
声大哭,痛不欲生。原来,四十年前。正是这位颇有才华的建筑工程师亲自勘定并指挥在此
地建筑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工兵营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十年后,这座当年极为得意的杰
作会成为他独生女儿接受强制戒毒的地方。
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巧合。
不!我不接受这种“巧合”。
没有谁会想到曾经用于为人类创造幸福安宁的工兵基地四十年后会成为解除人体毒害的
场所。正如我没有想到十年前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学校,如今在我面前却是一所冷寂无声的强
制戒毒所一样。
这不是巧合,这是人类的一种悲哀。
毒害。这一切都是毒品所造成的危害。
本不该让一百多年前给中华民族留下过切肤之痛的毒害在神州大地上重新蔓延。那么,
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