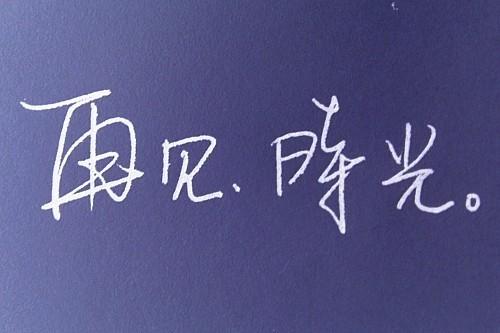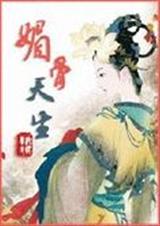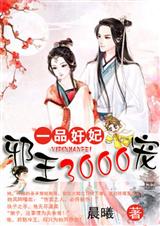诗刊 2007年第2期-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99年底,精疲力竭的我开始撤退,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要么进行新一轮的反技术实验,要么停笔,在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进行我所说的新一轮的反技术实验了。反技术,不是不要技术,不看重技术,是将它放在诗歌的恰当位置。这个过程有些艰难,因我是有意而为之,因我这样做,就是一种冒险,因我离开了我的时代,进行着同时也是反时代的试验。
我回到了词语本身,我把词语本身的生命力放在了第一位,当我从细节退回,我发现,我的写作开始获得一种生机,没想到这样做,我反而看见了我的时代,看见了我与日常生活所应该建立的基本关系。
在海边的风声里
北 野
1
一到冬天,海边的房子就变成了勃朗特姐妹笔下的呼啸山庄。
风往往是整夜整夜地刮。尖利的风声,好像携带着圆盘锯溅出的火星子,令人想起正在被切割的岩石、船坞、楼盘、森林和整个海岬。
有时大风摇晃着门窗,就像刚刚登陆的加勒比海盗,挥舞着火枪和大刀,凶悍地愤怒地嚎叫着。
2
就是在这样的夜里,有一次我独自到海边散步。
海啊,那诞生风暴的地方,黑得像命运。而夜空,那原本是高挂星星的地方,低得像绝望。这时,我突然注意到一个垂钓的人,他戴着皮帽子站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向着汹涌的海浪使劲地抛撒着渔线。
风呼呼地吹刮着,浪哗哗地翻卷着,海水之上只有一点点微弱的灯光,连多腿的虾爬子都钻进了海底的石缝。
那么此刻,这个两足的、无毛的、直立行走的、戴着皮帽子的垂钓者,他到底指望着什么呢?
他是不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结,需要通过一条渔线向大海诉说?
或者他幻想着普希金童话里的小金鱼,在这个恶浪滔滔的夜晚重现?
3
这是200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
它距离我最初“把思想写在纸上”的冲动,至少有二十多年时间了。
在海边的风声里,我渐渐意识到二十多年来我所热爱的诗歌,正像今夜这恶浪滔滔的大海:
它没有星光,没有魔瓶,没有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也没有海妖的女儿那迷人心魂的歌声!
它的表面翻滚着豪华游轮倾泻的现代垃圾,它的深处游弋着鬼魂般的纯物质的核潜艇。
它不适合垂钓,不适合洗澡,不适合想象,也不适合为了爱和美而进行的远征!
它只适合:茫然和沉没。
4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在远离大海的中亚草原,在远离泡沫的宁静内心,我开始了纯属个人的诗歌之旅。
我相信“诗歌曾是神圣的语言”,并坚信它依然应该神圣。
我相信“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尽管有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我相信“灵魂是肉体的气味”,尽管有人对灵魂嗤之以鼻。
“生活并不美好,”我勉励自己:“而我们的心,要向着美好死而无憾地飞呀!”
“把大地留给庸人去治理吧,”我写道:“我要天空!”
5
转眼之间我已经43岁。
“从前我四处流浪/带着短剑和诗行//如今我一片荒凉/青春和才华已快用光”。
当我顾影自怜的时候,我发现面目全非的不仅仅是从雪山到海洋的物理空间的变化,也不仅仅是从青春年少到英雄迟暮的岁月流逝的变化——最令我吃惊的是:
我常常被人们称作诗人,而我感到生命和生活中的诗意正在消失或已经荡然无存!
并且,像诗意、诗歌和诗人这类从前十分明晰的东西,现在变得一团混乱!
6
“诗歌精神”是我十五年前提出的一个模糊概念。
我当时给它的定义里包含着“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之类的更加模糊的元素。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日神的向上(如《浮士德》),还是酒神的向下(如《恶之花》),“诗歌精神”都是拒绝“庸众习俗”的;好像诗意就是对恶俗生活的一种反动,好像写诗就是对恶俗生活的一种抗击。
然而,很快,恶俗生活全面击溃了我那可怜的幻想,恶俗胜利了。其标志是:
整个社会根本不把诗意、诗歌和诗人放在眼里,社会尊重强权和钞票,欣赏恶和丑。
在这个过程中,诗意蒸发了,诗人隐遁了,诗歌则作为一种没心没肺的“文本”选择与时俱进,开始大面积地转基因繁殖:先是“恶作”满天飞,继而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撕开衣裙就地“恶搞”。
7
诗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谚云:“大道运行,各行其是可矣!”
是的。如果我瞎了眼或者死了心,也许我可以做到保持沉默。
遗憾的是,我修行太差,尚未破掉偏狭的“我执”,故有此嗔怒之文。
万望列位看官大人读者诸君海涵,并一笑了之!
随时间流逝的写作
海 男
从18岁在滇西永胜小镇开始涂鸦中的第一次书写生活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漫长的时间在日后等候着我。这种漫长包括人生不停止地迁移、栖居;也包括变幻莫测的写作之旅出现的一系列的困难;还包括你的心智,你写作的情结和环境都要经受住时间的熔炼。我是在一个暮色激荡的时刻离开滇西的,我上了火车。上了北去的火车,从那一刻开始,语词就在纷乱之中碰撞着铁轨,我带着写作笔记本、箱子,把自己塞进火车厢的角落,仿佛塞进一只火炉,历炼自我的时刻是在那个晚上开始的,然后我到了北京,到了鲁迅文学院的一间房子里。
很多年以后,我栖居在昆明,这是我最为明智的选择,因为,一个写作者必须寻找到适宜想象力、虚构的语词所需要的磁铁之乡。所以,我回到了云南,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北京不适合我,北方不适合于我的居住和写作,我依然是乘火车回到云南的。于是,在下火车时,风来了,不仅仅是从滇池边呼啸而来,也是从哀牢山、横断山脉,从滇西古驿道上而来,直抵我的胸口,这正是我灵魂落地的地方,也是我的魂灵游荡的边疆省份。
居住在昆明已经16年了,作为我私人生活的栖居地,它容纳了我写作的跳跃变化,也容纳了我写作生活的流逝。我想述说的是在时光如此变幻莫测的时间里,我依然每天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没有任何人命令我写作,也没有任何学会机构需要我来写作,我写作,这是一种宿命。
在经历了难以言喻的许多生活事件以后,写作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它伴随着时间的煎熬。不错,许多事情都需要时间来确证,词语也一样,它就像任何事件一样,必须落进时间的刀锋和沙漏器中去,随同刀锋的锃亮,我仍会看见许多东西都被揭穿之后的一团秘境;而从沙漏中过滤出去的沙粒,给我们的选择和困惑带来了真理。
此刻,我刚写完一本书,题为《最漫长的煎熬》,记录了云南洱海地区白南诏国到大理国时代的一段秘史。在里面,我依然触摸到了时间,凡是与生或死谜团纠缠一体的,都是时间的影子,所有被祭师和诗人们吟唱不休的只不过是时间的碎片而已。
自从多年以前给《诗刊》邮寄诗稿时,命运就编织出了这样的蛛网:诗歌像是温柔无止境的私人之旅,携带着我生命中难以拒绝的美妙的时光;诗歌像是黑夜和白昼交织中发出的任何一种切人我胸口的声音,它奴役着我上半辈子和下半辈子的现实生活。如今的我,居住在滇池边缘,使我不断地生活于语词中,并为此沉溺于语词的是快乐;是因为我的生活之旅从不缺乏与心智相遇的灵性生活,比如,在辽阔的云南边疆区域,在与一只狐狸相遇时,我同时也滋生了诡计和狡黠的美,可以穿巡的美;比如,在堆集着时间碎片的洱海地区,我寻找十三个王陵的时间,耗损尽了我的激情,然而,在死亡和秘密中,我获得了诗歌和用来书写的灵感。
在流逝的一切时间里,我的宿命,已经交给了未知的一切时间,只有写作可以抵制日渐衰竭的审美疲倦,唯有写作才可以揭穿心灵生活中最漫长的秘史。
“回避”的技术与“介入”的诗歌
蓝 蓝
茨维坦·托多罗夫在一篇题为《面对极限——集中营的道德生活》的文章中,提到了索尔仁尼琴曾亲身经历的一幕。在劳改营,一个囚犯非常认真地用自己的手艺砌好了一面墙。而据另一个名叫列维的人讲述,奥斯威辛集中营他见过一个品德极好、曾救过他的泥瓦匠为盖世太保修建防护墙以避空袭。这位泥瓦匠勤恳认真,工作出色。他的理由是“以做好命令他的工作来维护个人的尊严”。集中营里的女人们,也是尽心尽力地干活,她们说:“我们织出一流的手套,并引为自豪。”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就要被送进焚尸炉的人们这样做不是听从纳粹的命令,而是为了职业的尊严。
同样,他还举出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一个卫兵对集中营司令鲁道夫·霍斯的描述,说他如何“着迷于他的工作”,甚至连他的妻子也对他忽视了家庭和她的情感抱怨连天。这位集中营的卫兵忘了提到鲁道夫的工作是一桩大规模的集体谋杀。
茨维坦·托多罗夫指出,做好一件工作是否总构成善,不应仅仅根据它们是什么而且也应根据它们被用来做什么来进行判断。一个人必须将其用途和后果一起放进头脑考虑之中。这是因为,个人的尊严并不建立在社会认可之上,而仅仅在于良心和其善的意义悬而未决的行为之间的一致。
自然,这是人们在极端情形下遭遇到的个人尊严和道德的问题。到了今天,为了自我尊严的完善,在追求专业和手艺完美性的名义下,把对整个人类、对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隔离开来,是不是意味着同样也存在着问题?
从我们当下的各种刊物里,我读到过不少技术精良、几乎无懈可击的诗歌作品。在文本中,隐喻、反讽、通感……等等,做得完美无缺,形式的创新和观念的创新比比皆是。我不能不说,在修辞的意义上,在丰富汉语文字和表达形式的意义上,这些诗歌的的确确做出了贡献。但是,假如我在其中看不到对人的关心,看不到对他人生活的想象力和表达,我不会认为这是一首好的作品。我无法赞同单纯的技术主义的做法,因为作为现代社会的特色,“热衷于技术特权能使我们对人类情感变得迟钝(布鲁姆·贝多汉姆语)”。尤其,诗歌创作是一项探索人与世界、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语言艺术活动,技术主义至上从根本上违背了诗歌并不完全内在于个人、而是最终要超越个人立场的原则。
诗歌创作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作用于诗人的不仅仅有修辞艺术的要求,还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良知,以及对存在的关怀和对他人他物的想象力。追求单纯的技术主义从某一角度说,恰恰是一切扼杀人性、忽视人类情感、对人类生存处境冷酷漠视的极权统治和时代现实客观上的帮凶。
那么,诗歌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其艺术性为代价,简单地介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