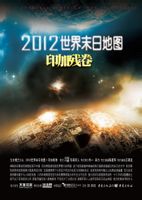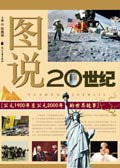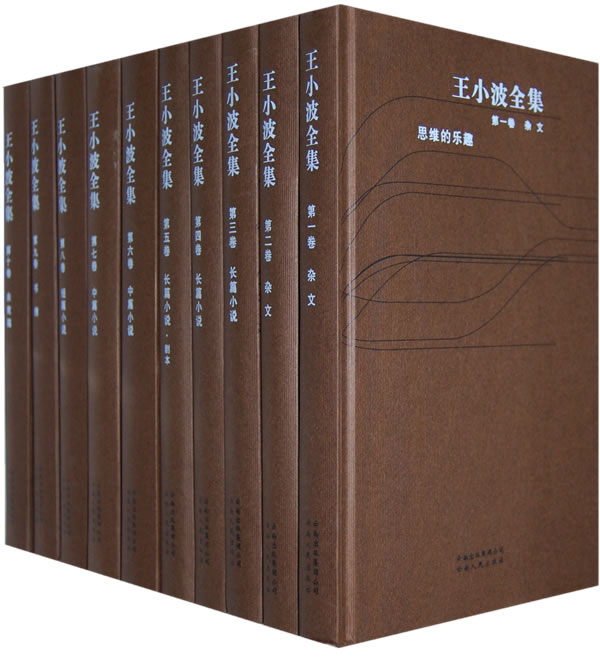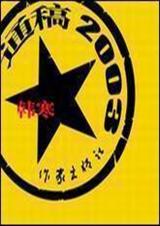2003年第15期-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字词活动的激情不单单归因于一般的语符崇拜,它还暗示出写作的动力真相。即对诗人而言,写作实现了一份深藏不露的追悼权利。大致说来,写作本质上就是怀旧,就是对已有的经验和情感进行语言上、心理上的强化和追认。诗人的语言具备一种记忆的再生潜能,诗人借助了语言的唤醒、复制、臆想功能,创造或复原历史。当然,这样的历史必须为诗人的身份认证提供确切的担保,以消除生命存在的虚无感。结果,我们在诗中看到的就只能是一个业已消逝的遥远世界的遗像了。诗人则仿佛如一个“词语的亡灵”,或曰亡灵的替身,他执意将世界的遗像当作倾诉对象,似乎一种诵经般的歌唱可以召回全部的栩栩如生的经验,而存在者就惊现在那条时间链条中。我把诗歌的这种对彼在世界的灵视力量看作是诗歌神性的表现。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写作的经验中存在着一种似非而是的历史性。而且,诗人的经验要比历史学家们的经验更有意义、更生动,总之更有必要。因为诗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既非客观,也非傲慢。他们所要追述的可能是一些心理事实。这类追述自然远离了行家们的“混账逻辑”,但却具备那种释放被禁的享乐(joyance)的效力。显然,德里达想说的是,文学写作不仅是一项权利,而且还是一项超越了理性逻辑的特权。的确如此,大多数诗人对待身边现实都保持了某种审慎的、扭扭捏捏的,甚至格格不入的态度,而对历史却葆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亲和、同情。可见,诗人都是一些倒着走路的人,他们往往与当代生活擦肩而过,却能够沿着历史的暗河上溯,在逆向运动中仔细辨认出存在的身世或踪迹。
诗歌的追悼根性这一观念的引人,既可以为解释诗歌生成机制提供一套弹性十足的诠释模式,又可以使我们在观察当代诗歌边缘化问题方面获得明晰的思路和宽容的心境。我的意思是说,当代诗歌对现实语境的适度疏离,不应简单地被指斥为诗人的处理当代生活的灵感萎缩或道义责任的放弃,这其中更包含着诗人对诗歌质能观作出重新体认和修正的努力。事实上,90年代以来的汉语诗坛的确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诗歌追悼风格的退还。社会生活一天一个变脸,使诗人在一夜之间便成为红色时代的灰色遗民(游民?移民?)——其身份甚至被认为是非法的。部分诗人被遣送回了历史,同时又阴差阳错地获得了诗歌本体的觉悟、体认。最著名的例证当属90年代初由《诗歌报》组织发起的,以席永君、江堤等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新乡土诗”运动;最极端的例证则是有着殉道倾向的天才诗人海子、顾城的自杀事件。这类事例表明,当代诗坛一直存在着时隐时现的某种“复古”潮流。一些诗人,包括知识分子,为了在日渐异化的后工业社会中保持一份最小的自由,都程度不同地将文化立场进行了后撤。此外,小说界的先锋作家,诸如苏童、余华等人对历史题材的持久热情也颇能说明问题,当然更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勃兴。总之,当代中国的现实裂变,促成了文学界保守主义的形成。(摘自《当代文坛》2003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