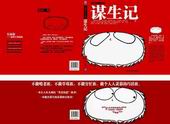境由心造 作者:程莉-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通俗书解闷。
以前开会我最喜欢带字典,事先把一本旧字典拆成三四摞,变成巴掌大的薄本本,经常揣在兜里,一开会就能派上用场。读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随便翻到那页,都有不认识的字,常读常新;随便看到哪里,都能停得下来,说走就走。这些年各式各样的书越来越多,就不怎么看字典了。昨天带的是2006年第三期《读书》,内有聂华苓回忆梁实秋的文章。
有人问,开会看书,会怎么办?别急,长期应付开会,训练了我的注意力分配能力,我非常擅长边听会边看书。听会可以达到传达会议内容的程度,看书可以达到复述文章大意的程度。其实做某些事用不着一心一意,一心二用或者三心二意就足以了,比如开会。
开会要不要带书,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要去开有我发言的会,你们最好不要带书,我好容易才有一次上台的机会,大家好歹给点面子。
凡人开博
前一个时期,名人开博很是热闹。如今,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的凡人草根也渐渐遍地“开博”,使得博客像一切正在流行的文化元素一样,迅速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这种男女老少皆宜的玩法,我早就想试它一试了。但由于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所以直到最近才行动。从去年12月14日至今,“开博”数月,正在兴头上,即使某一日上网不便,也会在几天内更新。没有时间写,便以发旧作为主,好在从前勤奋,存货不少。
原以为“开博”就是有块自留地,经营好自家菜园子就其乐融融了。真正当了博“客”,才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空间无限的文化宝库!平时,大众接受的信息大多来自媒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件和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我们只能看到进入记者编辑视线、又经过他们编撰的极少部分二手货,绝大多数原生态的信息被淹没在了匆匆流逝的平凡日子里。
凡人博客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一扇可以走出媒体禁锢的大众视野之窗。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博比写博能给人带来更大的益处和快乐,这么丰富的阅读内容,令我喜出望外!
我一直怀疑自己患有一种叫做“阅读强迫症”的顽疾,它可能与我在成长年代患有的“阅读饥渴症”相关。也许那时候可看的书太少,长期处于饥渴状态,使我在信息爆炸时代,面对铺天盖地的报刊、书籍、电视和网络应接不暇,产生强烈的吞读愿望。只要眼睛睁着,手闲着,就一定得读点什么才是,开会、如厕、乘车,甚至走路,只有阅读的时候;心里才会踏实,才会平静,否则就要心急,就要浮躁。就像一个小时候总也吃不饱的人,突然面对大量无论垃圾食品还是美味佳肴,都有旺盛的食欲,不把自己撑个腹满肚圆才怪。如今,有了博客这样一个好去处,我的“强迫阅读”就更有的读了。
读一堆文字在肚里有用吗?古人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还真是如此。虽说百闻不如一见,但是世界之大,谁也不可能走遍,不能亲身经历的事情,不能亲自去的地方,都可以通过阅读弥补。更何况阅读所获得的知识与信息,经常是可以用得着的。
当然,就像什么好东西都不能多吃一样,过量阅读也有副作用。视力疲劳、颈椎病就不去说它了,老话说“人生识字糊涂始”。读得多了,脑子乱了,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越来越差,人就变得糊涂了。另外,如果战争、凶杀、腐败、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消息充斥你的眼球,难免让你增加忧虑和烦恼,要不说“眼不见心不烦”呢。
想来想去,治疗阅读强迫症唯一有效的方法,恐怕就是出门旅行了。什么时候我也能像那些总是脚下生风的博友一样,每年行它万里路,咱的这个顽疾可能就有治了!
感悟上海
感悟上海这座城市,是从我小时候开始的。我幼年时曾在安徽省会合肥生活过几年,外祖父供职的那所大学,各系的知名教授几乎都来自上海,据说为了吸引上海籍的教授到这里工作,学校专门为他们修建了西式风格的住宅楼。
我对那些教授和他们风度优雅的夫人发生兴趣,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吴侬软语。上海人无论男女,人人说一种只有他们自己能听懂的语言,那声音听起来又甜又软,像水晶糖一样粘粘的,而且半透明,我很喜欢听这种燕子呢喃似的美妙方言。
上海人的穿着也很有品位。不见得多么好的布料,却因剪裁得体,做工精致,穿在身上就显出了与众不同。记得邻居家有一段料子,几家铺子都说买少了,不够做衣服。拿到上海,裁缝师傅量完尺寸就夸料子买得好:〃多一寸浪费,少一寸不够〃。做成一件春秋装,式样新颖,美观合体。上海人的精打细算,确实名不虚传。
上海人秀气。他们吃饭用小碗、小碟,不像北方人,大人、小孩都端着大海碗。上海的妈妈们管他们的孩子叫〃弟弟、妹妹〃,我一直想不通,这么一叫妈妈不是成了孩子的〃姐姐〃了吗?
在人们印象中,上海是全国最好的城市,我的一位上海籍的朋友曾认真对我说过,〃我家往上好几代可都是真正的上海人啊〃。那时候的上海,好比现在人们心目中的纽约或者巴黎。
合肥离上海不远,到上海去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我的一个愿望。后来回到北京上中学,我的数学老师就是上海人。他当时不到三十岁的年纪,课讲得很棒,性格温文尔雅,衬衣的领子永远洁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会唱评弹,一曲《蝶恋花》唱得疏音婉转,优美动听,曾在学校联欢会上演唱。上海话〃黄、王〃不分,〃胡、吴〃不分,老师姓胡,却总说自己姓〃吴〃,点名时也常要闹点笑话。更有意思的是他色盲,如果他在课堂上指着划了绿粉笔道的公式说:〃划红线的是重点。〃我们就会笑倒一片绿粉笔是我们偷偷放的,他的粉笔盒里只有红粉笔。老师知道我们无恶意,往往一笑了之。那时,我们全班同学都喜欢他,我也因此而热爱数学。
以后参加工作到了西安,单位很小,只有两三百人,除本地人,还有北京人和上海人。北京人多是从农村招来的知青,上海人则是刚刚经过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北京人和上海人都不怎样安心留在这座西北名城工作,他们最大的共同语言就是如何把自己弄回属于自己的城市。
后来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上海人远比北京人执着和雷厉风行。几年之内,上海人走得一干二净,北京人则在二十年后还有人留在那里。在当地人眼中,北京人豪爽大方,没架子,上海人自私小气,北京人比上海人口碑好得多。
有一段时间,上海人似乎在全国混得很没有人缘,被称之为小市民。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特别是北方人,越是当着外地人,越是要说别人听不懂的上海话。后来上海出了〃四人帮〃(其实四人帮中没有一个纯粹的上海人),更是使他们在各地的威望大打折扣。
说来也怪,我从小在京沪铁路上来来往往无数次,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走到过这条铁路的尽头。
在多少次渐渐离近而又掉转身之后,与上海的神交也越来越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深秋,当我终于踏上这片土地置身于上海的时候,尽管上海人的语言和做派依然独特,这种感悟与我多年对上海的印象却是那么不同。就像一位心仪已久而未曾谋面的偶像,我对它所有的想象似乎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模模糊糊。
如今这座城市就在我眼前了。这是一座古老而崭新的金融城市。白天的东方明珠、金贸大厦摩天而立,夜晚的外滩人流熙攘、灯光灿烂。渡过黄浦江,月色下的滨江大道幽静、柔美。与外滩隔江相望,美不胜收。
上海音乐学院是一定要去的。走在汾阳路上,踏着苍老的法国梧桐的片片落叶,从一扇扇开着或者半开着的窗中探出来的音符在空气中漂流,几座典雅的小楼中进进出出着表情高傲的少男少女。
一条三岔路口,一尊1937年树立的普希金像让人感到上海的文化底蕴;南京路的繁华,是上海的标志;浦东的速度,是上海建设的步伐;上海博物馆丰富的馆藏,是世界文化在上海的窗口;上海大剧院的构思,是上海精神的展示。
驻足观赏,浮想联翩。据说大剧院的空间结构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构图,三面都是玻璃幕墙,采用的是建筑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钢架式支持法;将人与大自然融合的天地人观念,与开放精神结合。
我喜欢上海。在向往多年后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我有点理解当年的上海教授和上海大学生依恋这座城市的原因了,因为它独一无二。
高玉兰小传
高玉兰是一个弃儿,身世和出生年月不详;生身父母是谁,恐怕永远是个谜了。
高玉兰被弃时大概还不到半岁,嗷嗷待哺的样子,很招人待见。从面相上看,她不大可能出生于名门,虽然够得上漂亮眼睛大而明亮,耳朵小巧对称,鼻梁笔直端正,不出声的时候,绝对的樱桃小口,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但这种小家碧玉式的漂亮,透着市井人家的通俗,使收养高玉兰的人家觉得,这小家伙应该好伺候粗茶淡饭就能养活。
高玉兰被收养后才叫高玉兰。高玉兰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名字,无论谁唤她,总是呆呆的样子,表情迟讷。倒是叫她的小名咪咪,还多少有些反应。
尽管说不准确切年龄,但高玉兰现在应该有两岁了,个头比刚来时大了不少,体重也增加了将近一倍。她看上去健康、活泼,只是智商可能有点问题:无论教她什么,似乎都很困难,不仅笨笨的,而且不爱学习,一副三心二意的样子。
高玉兰也有点优势,别看个小,身手却敏捷,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从不把桌、几、案上摆得满满当当的东西碰到地上。要是培训得力,搞搞体育什么的,高玉兰不见得不行。
最出乎意料的是,高玉兰居然穷身富命,绝非粗茶淡饭就能养活的。刚到我家时,几乎给什么都吃——忘记交代一句了:高玉兰被我家收养,纯属偶然。高玉兰先是女儿的小友领养的,一天,还没有名字的高玉兰跟着那位小友进了他家,见高玉兰又脏又瘦,小友动了恻隐之心,将她带到医院检查身体、打预防针,并接受医生的建议,做了一个剥夺了高玉兰追求幸福权利的手术。
第一次见高玉兰,是她术后复元的日子。小友出差,没时间照料,遂将高玉兰送到我家。那天很冷,高玉兰被装在一个书包里,当她把头从书包里探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双猫视眈眈的大眼睛,全家便喜欢上她了。只见高玉兰毫不犹豫地跳下地,大摇大摆地从客厅流窜到厨房,又转悠到阳台,一点儿也不认生。后来她伤口愈合,取下肚子上的绷带,这才得见了庐山真面目:一只身上带着黄色斑点的小白猫,像画家用蘸了黄颜色的笔甩出的一幅大写意。
名字是随口起的,俺家户主姓高,女儿有一只宠物玩具叫“高来福”,她就被唤作了“高玉兰”。这里头还有一典故:据说当年天蓬元帅猪八戒西天取经前在高老庄看上的姑娘就叫高什么兰,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