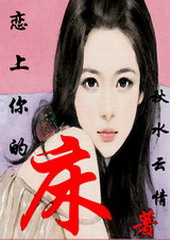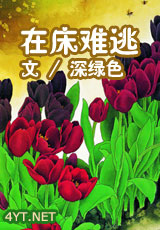大铜床-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丙崽按着信上的地址没有找到他的外婆,他找到的只是一大片凌乱的工地。原来一九七六的地震将这里一大片简易的平房震得东倒西歪,屈卫红的父母和邻居们在抗震棚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政府安排了新的住处,就都陆陆续续的搬走了。搬到新的住处,丙崽的外婆给珍姑写过信的,但不知什么缘故,那封信始终没有寄到珍姑的手上。
工地上的工人耐心的听着丙崽的外地口音,也听清了他的意思,但他们也不知道原来的那些住户搬到哪里去了。没有人能告诉丙崽,他要投奔的外婆家藏在了这个巨大城市的什么地方。
丙崽没能找到他的外婆,不光这天没能找到,以后也没能找到。多年之后,已没有人再叫他丙崽的丙崽回想起这件事,恍然觉得,外婆家也许只是冥冥中一个把他吸引到这个城市来的海市蜃楼,而等他到来时,这个城市和这个时代又恰好为他准备好了一切。
离开工地,丙崽一个人在偌大的北京城开始了他漫无目的的闲逛。除了高大的建筑,宽阔的马路,更让他惊喜的是那满大街像蝗虫一般的自行车人流和一辆辆挤得快要胀破了肚皮的公共汽车。
“这么多的人啊,这么多的人一天得吃掉好多的豆腐啊!”丙崽惊讶的想。巨大的人流让他兴奋不已,那感觉就有点像鱼儿见着了水一样。二十年后,人们把他的成功归结为他的天赋,这样的归纳确实是准确的。丙崽天生喜欢这个城市的一切,涌动的人群总是让他感到莫名的激动和兴奋,他天生是一块在人海中冲浪的好材料。
这天,天快要黑下来时,丙崽逛到了东直门外新源里一带。那时候这一带还是个荒凉的三不管地区,既不属于城里,也不属于郊区,又不属于农村,一大片菜地里孤零零的座落着几座农家小院。丙崽虽然怀里揣有二十张“大团结”,但他不知道城里有专门交钱就可以住宿的旅社,在山里赶夜路,人们都是找个路边的人家借宿一宿,所以丙崽想北京也应该是这样的,但他不敢去敲那些高楼的大门,就走到了这还有点像农村的地方,怯生生的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院门。
屋里聚集着七八个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这些人正秘密印制一本要“以更有力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声音”的地下刊物,印的都是他们没有经过或者没能经过审察机关审察的诗歌、小说和绘画。
他们聚集在这间农家小院里已连续熬了几天几夜了,用从印刷厂“顺”来的颜色不一大小不一的纸张,和好不容易借来的当时属于党委和工会专门管制的油印机,再手刻蜡版,用手推油印机上一张张推出来,一张张的摺页、配页、装订。
在这本后来载入史册的油印小册子中赫然印有这样的句子:“……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刊物印出来后怎么办?大家一商量,决定像他们的父辈,当年的地下党那样,把印出来的书页像传单一样四处张贴,但谈到由谁去贴的时候,就有人说,“我现在要考大学,不行” “我现在要结婚”或者“我现在比较困难”。毕竟是非法刊物,在习惯了因言治罪的年代里,谁也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商量的结果,决定由三个领头的去干这件事。
丙崽恰在这时敲响了院门,极轻的敲门声却仿似惊雷,把屋里的人吓了一大跳。
“谁?”屋里的人问。
“我。”丙崽答。
“你是谁?”
“过路的,想借宿一晚。”
听到是个外地口音的小男孩的声音,屋里的人大大松了口气,打开门一看,也果真是个半大的孩子,屋里的人都为刚才的虚惊一场感到好笑了。
丙崽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愣愣的看了他们一会儿,也跟着傻笑了起来。
“进来吧,”其中一个像是领头的说,“你叫什么?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丙崽想,在北京,可不能再让别人叫我的乳名了,于是就说:“我叫赵颉,就是左边一个吉字右边一个页字的那个颉,就是鸟儿向上飞的意思。我走了四小时山路,坐了十六小时汽车,二十八小时火车,来北京找我外婆。”
“名字还挺有学问的,那你找到你外婆了吗?”
“还没找到,我外婆家的房子已经拆了。”
“原来这样,好吧,那你就在这住一晚吧。不过,今天晚上你可得和我们一起干点活儿,熬浆糊,怎么样?”那个领头的轻快的在丙崽的头上拍了一下。
“嗯。”丙崽高兴的点了点头。
头一天晚上熬好浆糊,第二天骑上车,挎上包,挂上浆糊桶,准备出发。出发前把自行车后面的车牌给涂改了,0改成4,1改成10,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公安局就是用自行车号码来抓人的。而事实上这三名勇士也确实和亲人朋友作了交代,万一出了事如何如何,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劲头。
头天晚上熬完浆糊,这三个人还煮了面条,让丙崽也和他们一块吃。丙崽特别爱吃面条,山里人家都是把面条煮一小点儿,当下饭的菜吃的,很精贵。丙崽能有地方住下,还能大碗吃面条,他就觉得这些人特好。
所以第二天起来,看到他们骑上车要走,他也想跟着他们一块去,就问他们:“你们去哪?”
“西单。”
“西单是不是离天安门很近?”
“对,离天安门不远。”
“我想去看天安门,我能跟你们一块去吗?”
那三个人看着他,没吭声。
“我可以坐在车后头帮你们抱着那些书,你们干活的时候,我还可以帮你们看自行车。”丙崽讨好的说。
“那好吧,你上来吧。”那个大家都叫他猴子的领头的家伙说。
“唉!等我一下,我去拿我的包。”丙崽噔噔噔的跑回屋拿他的那个军挎包去了。
另一个领头的叫老木头,他对猴子说:“算了吧,万一出事,把这孩子也牵连进去。”
“没事,他还是个孩子,能把他怎么着?挺多也就是遣送回籍,反正他也没找着他外婆,真这样到还省了回去的路费了。”猴子满不在乎的说。
自行车驮着丙崽,经过了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经过了可用辽阔比喻的天安门广场,还有楼顶的大钟每到整点就高唱一遍《东方红》的电报大楼,来到人头攒动的西单 “民主墙”。
西单民主墙位于西单大街的东南侧,是西单体育场一堵长约二百米的灰色砖墙,但它面对宽阔的长安街,位置醒目。一九六六年这里最早贴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这里又率先贴出呼吁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声讨“四人帮”的诗词。而从一九七七年夏天开始,这堵墙成为了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忆苦诉冤,争取支持的大字报的集中地。
到一九七八年,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胆大的开始散发传单,并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除了看热闹的观众,被吸引来的还有外国记者和联袂而来的便衣警察。那时除了绿军装,人们几乎只有灰色和蓝色两种颜色的服装,便衣警察藏蓝色的“警蓝”,在人群里相当容易辨认,匮乏的年代,便衣警察也往往无衣可便。
便衣警察也没什么事可干,夹在在人群里东张西望,也许他们已得到了上司的命令,只要不出乱子,一切听之任之。三次被打倒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会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时已经说了,“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
这样的谈话据说是由一名加拿大记者在民主墙前转达的,当时聚集了好几千人,没有扩音设备,加拿大记者的讲话像波浪一样,被一层层人传出来,然后流向北京的大道通衢或者小街胡同,流向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虽然有重新“恢复工作”的数千名老干部的支持,但那时邓小平的地位并未稳固,他并不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两种力量还在较量,胜负未分。此时,群众的“民意”和外国新闻记者,在历史的进程中就都有了意想不到的用武之地了。
丙崽和那三个热血青年抱着他们的“非法刊物”来到民主墙时,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穿着花里胡哨的外国记者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的比划着手势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一群人簇拥着一个人,围成一个圈子,听他演说:“一个人怎能禁止另一个人头脑中的思想呢?”一个带着一付镜架用胶布粘起来的深度近视眼镜的人激愤的说,“一个政府又怎能用强制的手段去禁止公民的思考呢……”
他的话还没讲完,人群又被另一处不断有叫好声传出的圈子吸引了过去。圈子中央,一个人大声宣布:“邓小平说了,毛泽东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当然不能比他,最多四六开……”
“好!”人群中一阵喝彩。
二百多米的民主墙密密麻麻贴满了好几层的大字报,老木头和猴子揭去一块快要脱落的大字报,三人密切配合,一人往墙上刷浆糊,一人贴,另一人用扫帚扫平。
大字报都是手写的,还没见有油印的,一贴上去,就有人凑了过来。人越聚越多,后面的就看不见了,就有人在后面喊:“前面的,别老光顾着自个儿瞧啊,念几句有意思让大伙听听。”
“别挤了,别挤了!”前面的一个大个说,“我给大家念上面的一首诗,诗名叫《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好!”人群中又是叫好又是鼓掌。
老木头和猴子手上拿着一些他们的“杂志”,打算赠送给一些看上去像是他们“同志”的人。一些人陆续围了上来,向他们索要,拉着他们问这问那。“这诗真好,真痛快,作者是谁,我可以和他认识吗?”“你们的杂志还有吗?再给我多来几本。”“这本杂志是你们编的吗?我也写诗,哪天我拿给你们看看,你们住哪?”老木头和猴子他们被众人缠住了。
有一个人格外注意到了老木头这一行人和跟着他们一块来的丙崽,孩子应该呆在幼儿园和学校里,不应该出现在民主墙这里,还有就是丙崽胸前的军挎也让这人觉得有点眼熟。这个人就是十三年前用自来水管敲碎了赵援朝脑袋的王晓军,丙崽背着的那个军挎十三年前天天背在屈卫红的身上,天天在他眼前晃荡,王晓军当然就觉得有点眼熟了。
不管风向如何变换,水流如何湍急,有些人总是可以长久屹立于潮头不倒的,这些人在一次次风暴中幸存下来,决不仅仅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他们像一个老水手那样,练就了对风暴的良好的嗅觉和反应。王晓军的父亲王全就是这样的一个深谙风向和水性的“老水手”。文革开始没两年,红卫兵不吃香了,王全就安排王晓军去部队当了兵,而且很快穿上了四个口袋的干部服。部队在石家庄,离家很近,王晓军经常到北京出差,可以隔三岔五的往家跑,这兵当得轻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