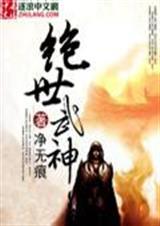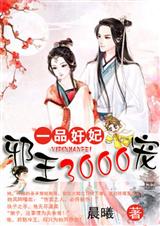收获-2006年第1期-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觉中,她在用他的价值观评价她曾经推崇的一切,那些下午他们共度的时光是否正在影响她未来的人生观?
劳伦斯笑着告知哲子,事实上,著名摄影师开幕酒会上的啤酒比他的作品更吸引他。可无论如何,那些图像仍然震撼了哲子,那都是真实人体两至三倍的巨幅照片,照片上是该摄影师的下体,以及阴茎的特写。这是个至少有六十五岁的老人,放大了好几倍的老人的阴茎,软塌地垂挂,不,是躲藏在两只睾丸之间,像一颗已经废弃但仍然被日晒雨淋藏污纳垢的鸟巢,不再有生命愿意栖息,而发出腐朽的气息,丑陋得令人窒息;然而,紧挨着巨大的萎缩的阴茎,是老人和他同龄老伴做爱的照片,哲子不由地闭了闭眼睛,甚至无法判断自己的内心是厌恶还是感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奇怪的恰恰是这一点,在厌恶的同时有感动,哲子想和劳伦斯讨论,但却觉得难以启齿,语词不够,勇气不够,她的文化让她无法坦然面对一件正在腐朽的性器官与另一个可以说是陌生的异性讨论与此有关的一切,也许这些都不是原因,仅仅是有些话题刚说出口便被话语本身误会,是啊,正是在这时,哲子感受到艺术作品的好处,它所蕴含的意味,是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可以对应。
对此,劳伦斯也未做评价,这个展览观众很多,开幕酒会上的空啤酒瓶被整齐地堆积成一座小山坡,就像一件装置作品,劳伦斯似乎忘记他是来喝啤酒的,他仔细地看完每件作品,然后说道:“最近这些年这位大师的作品要让人们喜欢越来越不容易,他知道他要什么,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他指指大厅里挤满的观众,似乎这是一个话题的引言,有些大而化之,哲子等着他细说缘由,但是他带着哲子离开展厅,朝20街去,那里的画廊几乎占据整条街,街上是三五成群的从画廊里溢出来的年轻观众,手里拿着啤酒瓶,劳伦斯笑了,“哦,这里有的是啤酒。”好像他必须先喝上啤酒,才有兴致把刚才的话题继续下去。
这里的画廊前身是间规模较大的工厂,原来的车间变成不同的展厅,有一间在做音乐演出,挤满了年轻人,另一间是VIDEO展示,其中有几件作品需要观众互动,很像电脑游戏,这个展厅的观众更接近游乐园客人,许多中学生,甚至有不少儿童,不断碰到劳伦斯的熟人,劳伦斯把哲子介绍给他们,说她从中国来,到纽约拍纪录片,其中有几个是瑟基洛派对上的客人,他们看见哲子稍稍发了一会儿愣,这天的哲子穿卡其短裤全棉汗衫,长发披肩,背着摄像机,与派对出现的形象判若两人,也许他们连这种差异都未必发现,全世界漂泊者来来往往的纽约,谁关注谁呢?出于礼貌或好奇,他们对哲子的城市哲子的工作问长问短,然后,在另一间展厅再遇到,他们已经忘记她是谁了,哲子有一种刻骨的寂寞。
她只有牢牢地跟着劳伦斯,就像小时候在“大世界”这样的游乐场牢牢地跟着父亲,这个城市就像个游乐场,如果没有紧密相连的人与你共享生命中的一些片刻,进来或出去,都变得没有意义,那时候画廊的人流量进入高峰,越来越多的人进来,不要说谈话,想要谈话的念头都变得疲惫,哲子终于忍不住问劳伦斯,是不是该走了。
他们走到画廊外,顺着街道继续朝前走,过马路等绿灯时,哲子才突然想起来似地问道:“接下来去哪里呢?”那时已经十点,但是对于哲子,对于在纽约没有家的人,十点仍是个迷惘的钟点,劳伦斯说:“去酒吧喝酒!”“然后呢?”“继续喝,你不断付钱,不断喝酒,酒喝得越多钱付得越快,然后早晨就到了,当然还有音乐,我想,总会有些音乐吧!”劳伦斯笑了,笑得有几分醉意,但这个晚上,他似乎才喝了一瓶啤酒。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见哲子沉默,劳伦斯问道,那时他们正在过马路。
“酒吧远不远呢?”哲子沉吟着,她对于酒并没有生理上的需求。
“不远,再过两三条横马路就到了,想不想去呢?”他再一次问道。
哲子没有回答,直到过第二条横马路时,哲子突然停下来,她对他说:“我想我还是回家的好!”仿佛这个回答是在劳伦斯的意料之中,他朝她摆摆手,说了一句:“回家路上小心。”便在路口与她道别了。
朝回家去的路上,总是伴随着无法排遣的寂寞,她一路上在后悔自己的选择,似乎,和劳伦斯之间有什么没有完成,可是她同时知道她并没有勇气去那个开门到早晨,将一屋子醉人送走的酒吧,她不是害怕酒吧,而是害怕与劳伦斯会走向某一地的深处,或者,那更像进入先前去过的巨大的遗留着旧工厂面目的画廊,一个只有进口却找不到出口的地方,人挤人,但都是陌生人,携带着陌生语言陌生背景,之后离开,去向更陌生的去处,她只能紧紧跟随一个相对熟悉的人,其熟悉程度只限于知道他的名字,职业,在片刻的微笑以及伴随而来的深不可测的沉默。
归根结底,这将是一个无法预知后果的旅行,假如她在路口不是与他道别,而是继续跟随他。
之后,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因为两人的时间表不一致,劳伦斯有空的时候,她没有空,她有时间的时候,劳伦斯有了安排,他们以一星期通一次邮件维持着联系,他的信渐渐地长起来,但也是广种谨慎的增长,似乎劳伦斯在控制某种节奏,假如说交往也是有节奏的,哲子有时会向他描述她看到的好戏,但从来不描述她看过的画展,对劳伦斯描述画展不是班门弄斧吗?
在一次激烈的争执后她与男友互不理睬三天,第四天早晨哲子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突然觉得在纽约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她坐在床上给中国城的旅游公司打电话订回上海的机票,然后退房租,整行李,告别,忙乱了几天,回上海前一天,收到劳伦斯的信,他问:“最近又看了什么新戏?也许应该让你带着,去那些我陌生的剧场,就像我带你去画廊。”哲子轻轻叹了一口气,这也曾是她的期盼。
她给劳伦斯电话,告诉他她明天就要回上海的家了。劳伦斯问:“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事,只是,我突然很想家。”
“大概你有个热闹的大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可我记得你的国家都是独生子女。”
她一愣,他把她的“家”误以为她父母的家,这就是说,他一直认为她未婚,她应该告诉他她已有自己的家,但在纽约最后一天,她怎么都没有勇气告诉他她已婚的现实,或者说,她从来就没有打算告诉劳伦斯她的真实人生。
事实上,她对他的人生又有多少了解?
“没有时间去剧场了,但是,至少应该一起喝杯咖啡。”她说,似乎,她和劳伦斯之间有些什么没有完成,她想了想,想不起是什么。
他们讨论了一会儿关于见面时间,但是很不凑巧,他们的时间表仍然不一致。放下电话时她想起来了,是关于那个著名摄影师的话题没有继续,不仅仅是一个话题,他们之间好些话题都只是开了个头。
她回上海后,劳伦斯写信提起他们的时间表,开玩笑道,我们应该是很理想的室友(roommate,即同租一套公寓),总是在时伺上错开,见不上面。他还告诉她,他的画室租约已到;他租于个集装箱放画和绘画工具,正在寻找新的画室,此刻,他在纽约图书馆消磨应该在画室的时间。
她的眼睛在湿润,她身在上海,却再一次从肌肤上感触纽约漂泊的寒冷,她写信告诉劳伦斯,有时候觉得,我对纽约的爱远远超过我对自己的城市,但,SOWHAT?(又怎么样呢?她用了大写)假如你没有勇气为你的爱付出代价。
这封信没有发出,而是被她delete(删除)了,这些议论就像她的人生给予劳伦斯的印象有些面目不清,她不想再平白地给他增添一些误会,毕竟,萍水相逢。
孔雀
马 枋
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五岁之前没有见过孔雀;事实上,我直到九岁那年仍然没有见过孔雀,但那时我已经知道有孔雀这回事了。
之所以要提到五岁这个时间概念,是因为一个叫花儿的小女孩儿。花儿跟我一般大,也就是说,我五岁那年,她也五岁。我们两家是邻居,住在一排房子的东西两端,她家在东头,我家在西边。
花儿的母亲跟我母亲很要好,当然,这是指在发生那件事之前。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而花儿没有;她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没有,所以她就经常跑到我家里,跟我的姐妹们玩儿,有时,赶上吃饭,就跟我们一起吃。花儿的母亲来找她时,看见她捧着我家的粗瓷碗喝面汤,呼噜呼噜喝得正香,就笑着说,这孩子,在家里不肯好好吃饭,到了这里却变成了小猪。我母亲听了也笑起来,母亲说,干脆就把花儿送给我来养吧,长大了给我当儿媳妇。
我那时虽然还很小,但我已经明白母亲的话大概的意思,那就是要花儿给我当媳妇。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孩儿,而女孩儿们是不需要媳妇的。
我五岁的时候,并不知道媳妇是怎么一回事,花儿大概也不知道,但花儿似乎比我想的事情多一些。有一天,在我家,姐姐和妹妹不在跟前的时候,花儿忽然问我,你知道我是你媳妇吗?我说知道啊,我妈说过的。花儿说,女的只能给男的当媳妇。我说,这谁不懂啊。花儿一下子变得神秘起来,伏在我耳边小声地说,那你知道男的跟女的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
我被问住了。说真的,五岁之前,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了又想,只能对花儿说,男的头发短,而女的梳小辫儿。花儿说才不是呢,你妈妈头发也挺短啊,可她是女的呀。我想一下,也对,就无话可说了。花儿得意了,她很骄傲地对我说,我知道。她说,我知道男的跟女的哪里不一样。
后来,花儿就脱下了裤子。她让我看看她。然后又让我也如此照办。我们互相观看着。我觉得很有趣,是不一样。但我当时并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觉得很好玩儿,有一点点满足感。因为我有的,她没有。
花儿似乎并不介意她比我少点儿什么。她穿好裤子后,又总结道,男的和女的只有前面不一样,后面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花儿说得很对。花儿经常是对的。我对花儿佩服得五体投地。·
后来就到了九岁那一年。那时我和花儿都上小学了。
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但互相很少说话。那时男生和女生之间除了吵架,一般是不讲话的。花儿也很少到我家里来玩儿,偶尔来一次,也是来找我的姐妹,对我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我也不想跟她说话。我们装成谁也不认识谁的样子,紧绷着脸,目不斜视。母亲看见我们这般模样,觉得可笑,就说我们是“小大人儿”。
这种局面在那个夏天被打破。
那年暑假,花儿跟随她的父母去了一次省城。
省城的概念对于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小城的孩子们来说,既遥远又神奇,让我们充满了想象,然而许多事情却又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比如说冰棍儿。花儿从省城回来后,告诉我们,那里的冰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