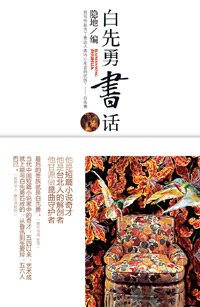夏衍书话-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世纪初,每年都有七八千乃至一万人去日留学,要考取官费是困难的。可是我拚命一搏,居然不到一年就考进了素以严格著称的明治专门学校(现九洲工业大学)。起初是认认真真地读书。可是年复一年地过去,我的工业救国的梦想开始动摇了。二十年代,中国还没有起码的现代化工业,像上海这样一个工业城市,几乎所有的工厂设备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我在“明专”学的是电机工程。那时中国不仅不能制造发电机、变压器,连最普通的机器配件也都被外国厂商所垄断,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成套设备要靠进口,连安装、维修都掌握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手里。在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在工科大学毕了业,当上了工程师,究竟能对自己的祖国作出什么贡献呢?中国现代有两位伟大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他们本来也都是在日本学医的。但是,他们后来终于感觉到治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先要治中国人民的贫穷、愚昧和甘为奴隶的“国民性”。我不自觉地也走上了和他们相似的道路,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时代潮流。当然,我的弃工从文,可能和“明专”的校训“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有点关系,我开始察觉到没有一个独立、自主和民主的国家,单凭技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是不可能的。我的思想开阔了,我终于下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二十年代中叶的日本,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参加了日本进步学生的“读书会”,结识了秋田雨雀、藤森成吉和大山郁夫先生,更重要的是我感受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种顽强拚搏的“顽张”(Ganbaru)精神。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有悠久的友好联系,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阿倍仲麻吕、小野妹子和空海法师,日本人民也不会忘记鉴真法师、朱舜水和黄遵宪。在古代,日本多次派遣过遣隋使、遣唐使,从中国引进了文化、艺术和工艺。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亚洲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日本 明治维新之后,废弃了锁国政策,大力吸收西方文化,锐意改革,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而中国则在鸦片战争之后外敌入侵,内政腐败,成为一个被叫做东亚病夫的半殖民地。从这时起,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人志士为了挽救危亡,振兴中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东渡日本,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彭湃,终身为中日友好事业而献身的廖承志,中国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驰誉世界的大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都是本世纪初和二十年代日本留学生。
两年前,我看了一部为纪念空海法师圆寂一千一百五十周年而摄制的日本电影《空海》。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当空海随遣唐使留学长安,学成回国之后,有人问他对大唐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唐朝像一只老虎,不论怎样硬的东西,他都能把它嚼碎,吞下去,消化掉。”这是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可是我想,到了二十世纪,用这句话来作为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许是更恰当了。作为一个青年时期在日本学习和生活过来的人,我觉得日本民族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仅敢吸收一切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文化,能够把它嚼碎、吞下和消化,而且还适应本民族的需要把它融化加工,变成为有民族特色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古代,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又通过中国,引进了印度的佛教文化,然后把两者融会贯通,形成了一种日本特有的人生哲学。思想意识上如此,文化、艺术、技术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书法、围棋、茶道乃至许多民间习俗,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经过千百年的溶化,提炼,加工,到了现代,都已经超过中国了。在科学技术方面,这样的技术就更多了。汽车和电子工业等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现在,日本的丰田、日产已经赶上乃至超过了美国的福特、克雷斯勒和西德的奔驰。日本的电视机、录像机都已经占领了世界市场。现在,美国正忧心忡忡,深怕日本会抢先生产出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走在它的前面。日本民族对世界上的一切先进事物有一种惊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这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事了。
中国和日本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之间应该和平共处,互助合作。这决不是一方面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和地理条件制约的必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合作则互利,对立则两伤。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仅亲身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过的伤痛,也多少知道一点战争中和战后一段时间日本人民承受过的灾难。因此,珍重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两国人民更友好、更合作的时代,已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庄严使命。
提到文化交流和民族传统的关系,很自然地想起了许多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逐岛战争的时候,我们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议论得最多的问题是日本会不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所提的条件?当时,我们这些人认为日本是不会接受的,一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外国征服过,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二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能真的会迫使他们“一亿玉碎”。可是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太片面了。一九四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一年,对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去思考;直到一九四七年,我在新加坡看一本美国人类学家路斯。本尼狄克(Ruth Benediet)的《菊与剑》,才使我感觉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动向(即使像日本这样一个和我们有上千年的交往的近邻),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因素之外,还得从人类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才能得 出比较正确的答案。本尼狄克写的这本书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应美国国务院的嘱托,为了研究美国的对日政策而执笔的一份供咨询的报告。她没有到过日本,不懂日语,她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被美国扣留的日侨和“二世”,和大量有关日本的著作和文艺作品,所以这本书的注释中有一些不合实际的地方。但是她从人类学,也就是从“日本文化的某些类型”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会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在战争胜利后也不能用对待纳粹德国的办法来对待日本,而必须考虑日本民族的特殊性格和感情上的承受能力。她的意见对罗斯福的决策起了一定作用。战后事态的发展,也和她的预测和建议一致。本尼狄克认为,尽管一个民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习俗和邻居民族相同,但总会有一点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这一点尽管很小,但它对这个民族的本身的独特的发展方向,会起重要的作用。她从文化、民俗的视角来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人生哲学。她认为从人类学来分析,一个人在文化习俗上不可能是一张白纸,人一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国情”。美国人由于不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亏,于是才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对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终战时期采用了既对美国有利(减轻了几十万美军的伤亡),又制定了可能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政策。从这一角度来思考,我们对近邻日本的研究实在是太落后了。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成了任人摆布的“东亚病夫”。可以说,那时候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存亡。可是,除了清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不久前才出全的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之外,我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实在太少,更不用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日本了。两个田中(决定侵华战争的田中义一和中日恢复邦交的田中角荣)之间的半个多世纪,中日两国人民由于互不理解而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直到今天,我认为这种互不理解的情况还依然存在。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日本人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难解的“谜”。战后四十年,尽管中日友好已成为很难逆转的大势,但日本人眼中的这个谜是否已经解开了呢?对这半个多世纪的血泪史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了呢?我接触过不少日本的有识之士,但近年来从日本报刊上看到,似乎也还有一些人对这四十年前那一场浩劫,还有一点“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心理。反过来看,我们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国运的大起大落,对日本人的既谦恭又自大,既性急又从容,一方面可以争分夺秒地拚命工作,一方面又舍得花时间慢吞吞地玩茶道、下围棋的这种矛盾心态,是否有了认真的探索了呢?我看也差得很远。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代的中国,现在的日本当然也已经不是大隈重信时代的日本了。高科技迅猛发展,地球变小了,中日两国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仅关系到亚洲,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危。现在,是应该静下来认认真真地加深理解的时候了。我想引用黄遵宪的几句诗,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
譬若辅车依,譬如犄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
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
一九八七年元月(原载日译本《夏衍自传》,日本东方书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致读者
——日译本《夏衍自传》序二
拙作《懒寻旧梦录》的自序和前三章,承阿部幸夫先生译出,已于今春由东方书店出版。现在,这本书的第六章《记者生涯》的日语版又将和日本读者见面了,阿部先生要我写一篇短序。
《懒寻旧梦录》是我的自传体回忆录。一九八二年动笔的时候,原来的计划是回忆和反思我一生的经历——从一九○○年到八十年代中期,全书共十章,但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年就搁笔了。这是我的前半生,写了三十多万字,篇幅已经不小,可以告一段落。这之后的后三章——《十年作吏》、《艰难的岁月》和《尾声》,尽管早已有了一个提纲,但大部分资料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汇集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停了两年一直没有动笔。
现在译出的第六章,主要写的是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记者生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协助郭沫若办《救亡日报》起,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华商报》止,前后当了十二年的记者和编辑。那是战争时期,生活艰苦,但斗志旺盛。上海沦陷,《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复刊,一九三八年冬广州沦陷,再一次搬到桂林。一九四一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救亡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又和邹韬奋、范长江一起,到香港办了《华商报》。这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四月回到重庆,当了《新华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