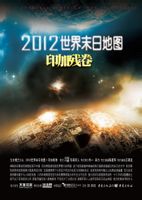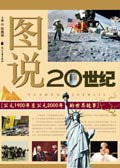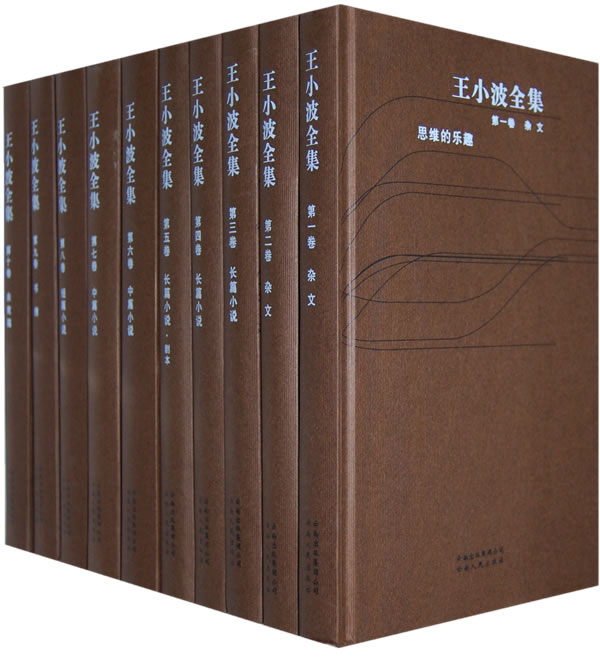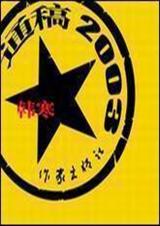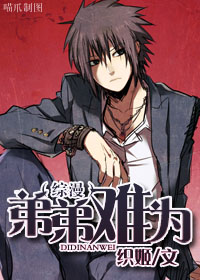2005年第1期-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注视。我没发现它们的欢迎词。对任何财富我也不想问津。为了避免嚎啕大哭,我必须立即逃走。天赋的本能,阿谀老先生,今夜我不能忍耐。他肩并肩悄悄溜过想到:“男孩子的爱情,很不幸照顾他们要特别留神。”“踏步走,再来一次,”本能对我说。像一位经院哲学家,英明地领我穿过被晒热树木的、丁香花和情欲的童贞的禁入的芦苇。“你要学会走路,然后再跑。”——本能说,而新的太阳从天顶下望,就像教地球上的土著在新行星上重新学步。这一切使某些人眼花缭乱。使另一些人—— 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雏鸡在大丽花丛中觅食, 蟋蟀、蜻蜓像钟表一样滴答响。 房瓦在游泳,中午不眨眼地 看着房顶。在马堡 有人高声吹口哨,做弩弓 有人默默准备去圣三一节集会。 沙子发黄,吞噬着云朵。 暴风雨将临使树丛的眉毛抖动。 天空烧焦后结成止血的 金车素而落下。 那天,我像个地方的悲剧演员 背诵莎士比亚悲剧一样, 把你从头到尾背得烂熟, 随身携带着在城里闲逛并排练。 当我跪在你面前,搂抱住 这片雾,这块冰,这个外表 (你多美!)这股热旋风…… 你说什么?清醒些!完了。我将被抛弃。 这里住过马丁·路德。那里住过格林兄弟。 利爪状的屋檐。树木。墓志铭。 所有这一切都记得并向往他们。 一切都记忆犹新。这一切又多么相似。 不,明天我不去那儿。拒绝—— 比离别还彻底。一切都明白。我们两清了。 火车站上的忙碌与我们无关。 我将发生什么事,古老的石板? 大雾把我们的行李袋散放各处, 在两个窗口各存一个月。 忧愁像游客在每本书上划过 并和书本一起被放入沙发。 我怕什么?我对失眠之夜 像对语法书一样熟悉。我已和它结盟。 为什么我惧怕习惯思想的出现 犹如惧怕月夜狂患者的到来? 夜晚坐在月色下的 镶木地板上,同我下象棋, 窗户敞开,空中散发着金合欢的香气, 热情像证人一样头发灰白地坐在角落里。 杨树是棋王。我同不眠之夜玩耍。 夜莺是棋后,我倾心于夜莺。 黑夜在胜利,王和后在退却, 我看到早霞。
1915年
(菲野译)
马 堡
我战栗。我闪烁又熄灭,
我震惊。我求了婚——可晚了,
太晚了。我怕,她拒绝了我。
可怜她的泪,我比圣徒更有福。
我走进广场。我会被算作
再生者,每片椴树叶,
每块砖都活着,不在乎我,
为最后的告别而暴跳。
铺路石发烫,街的额头黧黑。
眼睑下鹅卵石冷漠地
怒视天空,风像船夫
划过椴树林。一切都是象征。
无论如何,避开它们注视,
不管好歹我转移视线。
我不想知道得失。
别嚎啕大哭,我得离开。
房瓦漂浮,正午不眨眼
注视房顶。在马堡
有人吹口哨,做弩弓有人为三一节集市妆扮。沙子吞噬云朵发黄,一场暴风反复撼动灌木丛。天空因触到金车素枝头而凝固,停止流动。像扮演拥抱悲剧的罗密欧,我蹒跚地穿过城市排练你整天带着你,从头到脚把你背得滚瓜烂熟。·当我在你的房间跪下,搂住这雾,这霜,(你多可爱!)这热流……你想什么?“清醒点!”完了!这儿住过马丁·路德。那儿格林兄弟。这一切都记得并够到他们:鹰爪—电檐。墓碑。树木。一切都活着。一切都是象征。不,我明天不去了。拒绝——比分手更彻底。我们完了。两清了。如果我放弃街灯,河岸——古老的铺路石?我为何物?雾从四面八方打开它的包袱,两个窗口悬挂一个月亮。而忧郁将略过那些书在沙发上的一本书中停留。我怕什么?我熟知失眠如同语法。早就习以为常。顺着窗户的四个方框黎明将铺下透明的垫子。此刻夜晚坐着跟我下棋象牙色月光在地板上画格。金合欢飘香,窗户敞开,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
杨树是王。我同失眠对弈。
夜莺是王后,我闻其声。
我去够夜莺。夜得胜了。
棋子纷纷让位给早晨的白脸。
1915—1956年
(北岛译)
由于篇幅关系,我略去顾蕴璞的译本。这首诗,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修改了很多遍,比如菲野译本标明的是1915年,顾蕴璞译本标明的是1916年和1928年,而我参照的企鹅版的译本表明的是1915—1956年。看来有理由相信,我的译本是最后的定稿。由于找不到菲野和顾蕴璞译本的英文翻译,故无从比较。也许更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诗人修改的地方。与1915年的版本相比,1956年的定稿中做了很多改动,特别是大幅度删节,初稿中的第五到第八段完全被去掉,把十八段压缩成十四段。从定稿的角度来看,这四段确实是多余的,自言自语式的表白,使全诗陷于停顿,带有青春期写作中滥情的痕迹。另外即使没有参照,我们还是可以感到意象和节奏上微妙的变化。只举一例:热情像证人一样头发灰白地坐在角落里(菲野译);激情如证人枯坐在角落里(顾蕴璞译);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北岛译)。显然让热情这个灰发证人,从坐在角落里改成站在门口,变被动为主动,证人成为不速之客,造成一种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这首诗带有明显的个人自传色彩,显然和马堡的失恋相关。从结构上来看,这首诗分两
部分:其一,前十段是作者在城里游荡时的感受,加上对求婚被拒那一刻的“闪回”;其二,后四段是不眠之夜的苦闷,以及最终的超越与升华。
开篇直接进入主题:我战栗。我闪烁又熄灭,/我震惊。我求了婚——可晚了,/太晚了。我怕,她拒绝了我。/可怜她的泪,我比圣徒更有福。作者一连用了七个动词短句,展示求婚被拒绝那震惊、后悔及无所适从的状态。而最后一句的基调显然和前三句不同——怜悯,骄傲、如释重负,与下一段中我会被算作/再生者相呼应。对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这种失恋的痛苦,对“契约”的无知和渴望,失败后的轻松感统统交织在一起。
接下来是作者的漫游过程。他在马堡这个古城漫无目的地行走,穿越历史穿越自然,与其说是消耗体力,不如说是一种精神释放。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周围环境上的感情投射,步移景换。
其中第三段最精彩:铺路石发烫,街的额头黧黑。/眼睑下鹅卵石冷漠地/怒视天空,风像船夫/划过椴树林。一切都是象征。静与动、愤怒与和谐、坚硬与柔软都融合在一起。诗歌中既要讲“奇”,又要讲“通”。所谓“奇”,就是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陌生化”;而“通”,按我的理解,则是一种诗意的合理性。比如鹅卵石冷漠地/怒视天空,风像船夫/划过椴树林这两组意象既“奇”又“通”,真所谓神来之笔。
再来看看第七段:像扮演拥抱悲剧的罗密欧,/我蹒跚地穿过城市排练你/整天带着你,从头到脚/把你背得滚瓜烂熟。把自己想象成排练的演员,把情人当成台词牢记在心,且非常具体化——从头到脚。正是这种“陌生化”的效果,避免了陈词滥调,延长并加深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这首诗的高潮在第二部分,那是漫游的终结与醒悟的开始,若无这部分,“马堡”几乎是不能成立的。其中的第一段是过渡,即内与外的连接点:雾从四面八方打开它的包袱,/两个窗口悬挂一个月亮。/而忧郁将略过那些书/在沙发上的一本书中停留。只要和初稿相比,我们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大雾把我们的行李袋散放各处,/在两个窗口各存一个月。/忧愁像游客在每本书上划过/并和书本一起被放入沙发。(菲野译)至于是翻译上的差异还是作者修改的结果,都无从判断,我们只能比较“现状”。依我看,雾从四面八方打开它的包袱,/两个窗口悬挂一个月亮比另一版本更“奇”更“通”,有一种更虚幻更博大的东西。首先想想雾的包袱得有多大呀,而两个窗口又构成具体的限制,打 开,按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即除去遮蔽——两个 窗口悬挂一个月亮。
推动最后三段是一组统一的意象,即与不 眠之夜对弈,其实也是与自己对弈。而作者不 断引进外部的自然意象:月光、金合欢、白杨。 夜莺,由于窗户敞开,它们加入到这场对弈中 来,结盟或成对手。其中最重要的外来者是热 情,那灰发证人,即诗歌本身,它如同不速之客, 为历史也为诗人耗尽身心的一生作证。这画龙 点睛之笔表明作者的决心。
全诗是这样结束的:杨树是王。我同失眠 对弈。/夜莺是王后,我闻其声。/我去够夜莺。 夜得胜了。/棋子纷纷让位给早晨的白脸。在 这里,夜莺是女性的象征,作者并没有背叛爱 情,尽管那爱情的临时代表抛弃了他。在这个 意义上,夜得胜了。但似乎这已无关紧要,因为 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新的生活无所谓输赢,迎 接他的是早晨的白脸。
纵观全局,这绝不限于一首情诗,而是由于 失恋引发的危机,包括精神漫游的历程,对理性 世界的怀疑及对使命感的领悟。在我看来,这 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生涯的高峰。虽然他 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曾半开玩笑地提到自己 “那些马堡的垃圾”。
六
1960年年初,在第一次见到帕斯捷尔纳克后不久,奥尔嘉又来到作家村彼列捷尔金诺。她希望做一次正式采访,被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说:“你要采访,必须等我不太忙的时候再来,也许明年秋天。”每次分手,他都用俄罗斯传统的方式吻奥尔嘉的手,请她下个星期天来。于是接连三四个周末,奥尔嘉都如约而至。在过早降临的暮色中,她抄近道,从电气火车站经过一片墓地,迎着风雪,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
他的家人已在午餐后散去,屋里空荡荡的。帕斯捷尔纳克坚持让她吃东西,让厨师端来鹿肉和伏特加。这是下午四点钟,屋里又暗又暖和,只有风声雪声。他们隔着桌子聊天。帕斯捷尔纳克告诉奥尔嘉,他最近重读了她祖父、俄国著名小说家安德列耶夫的小说,非常喜欢:“他们带有十九世纪那些非凡岁月的印记。那些岁月如今退入我们的记忆中,它们像远处的大山一样隐隐呈现。”他谈到尼采对他们那一代的影响,而他认为,尼采在那个时代传播了某种不良趣味。
餐厅越来越暗,他们换到开着灯的小房间。帕斯捷尔纳克端来橘子。墙上是他父亲的肖像画,那些世纪之交的作家在盯着他们。
奥尔嘉听说在写《日瓦戈医生》时,他摒弃他的早期诗作,认为它们只是试验,已经过时了。对奥尔嘉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在她看来,《生活,我的姐妹》、《主题与变奏》早巳成为经典之作,很多苏联作家和诗人都会背诵。难道他真的摒弃早期诗作了吗?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时,多少带着愤怒的声调:“我对我的同时代人有一种巨大的负债感。我写《日瓦戈医生》就是想试着偿还。这种负债感在小说进度缓慢时让我喘不过气来。在这么多年只写抒情诗搞翻译,对我来说有责任对我们的时代表明立场——那些岁月,遥远却隐隐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