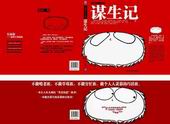�ջ��뵶 ����:(��)����Ͽ��� ��,��־��,��С��,����ʤ ��-��3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ɱ���ķ������������ⲻ������������ְҵ����ѧ�ҵĹ۵㣬��Ҳ��ÿһ�����ڼ����ܸ�ĸ����ʱ�ͽ�ȾѬ�������е���ѧ���������ѧ�ҵķ�����������������е�����ʵ�顣���ӵ���һ����ʱ�䡰���롱���ޣ����������丸ĸ�ı����в����������һ��ѹ�֡���������ͥ�к�����ÿҹ�Ĵ�������ʾ�䲻����������һ���ܹ����������������ˣ���˯����Ϊ�ˡ����롱�������飬���������۵���ʽ�ķ���������ĸ���涨ijЩ�ء����롱�ԵĶ�����������������࣬�ˣ�������������֭��������С��ѧ���˶��������롱�ԵĶ�����ʾ���顣����ó����ۣ��������������桱����ʳ�ﲢ����ζ���õ�ʳ�����һ����ͼϰ�ף������ձ�������δ�ŵģ�������ϣ��������һЩ����������Ҳ��û�еġ�����������ζ�Ŵ�ʳ���ѹ���еõ���ţ�һ�������˲������ڳ�ʱ��������Ķ��������һ����Գ�ζ���õ�ʳ���
�������ǣ�������������������������������ȣ���Щ����˯������ʳ�Ĺ����Dz�ֵһ��ġ���������������Ϊ��ĸΪ�亢�������˾�����������Ϊ���ɷ������Լ���һ�����ɷ�Ϊά��һ�����ƶ������Լ������ɡ������˺���������ijЩ���������ŮŮ����������������֮��Ҫ������ȴ����ġ������������������˵����ĸ��Ȼ�е�С���ɰ���Ů���ڽ�������������·֮����Ըѡ��ǰ�ߣ����һ�ڵ��������ڸ�����ϲ����ְҵ���������˻������ڸ�����ϲ����ְҵһ����ΪʲôҪ̸������������������ǿ����Щ���ͣ�����������������Щ���������������
����������Ͳ����õ����ϡ���
����һ������������������������Ϊ���۶�Ϊ������������һ�У�������һЩ�Ļ���ȴ����Ϊ�ǻ��ཻ�������ǻ��ǽ����Ժ�õ�������Ͷ�ʣ����Ƕ��ѵõ��ļ�ֵ�ij������������Ĺ��ң��������ӹ�ϵҲ�Դ˷�ʽ���Դ��������ڶ�������ʱΪ��������һ�У����ӽ������˵������������������ҵ��ϵҲ��һ�������Լ����Ȼ����ȷ��������������Ҳͬ������ʹ������һ���е���������ʹ��һ���е������������˫������Ϊ�����洦�����ڼ�����û��һ������Լ�������������Ϊ��������
�������ձ���Ϊ���˷����ǿ������Ȼ�ǻ�����������Ҫ����յ��Ķ�������������ҲҪ���ڵȼ���ϵ�е��˱˴�֮����������Ρ���ˣ����������ĵ��¹������ĵ�λ���������ĵ�λ����ͬ���ձ��������رԻ����̴���ʿ��������������˵�̡����������е��Ե��˲�Ӧ��Ϊ��Ϊ��������֮���Ƕ��Լ�Ը����ѹ�֡�һ���ձ��˶���˵����������������dz�֮Ϊ�����������£�������Ϊ����ϣ�����裬����Ϊ�����Ǻ��¡����Dz���Ϊ�Լ��е��ź�����������Ϊ����ʵ���������˶��ٶ��������Dz�����Ϊ���ָ����ʹ�����ھ�����������������Ӧ����˶��õ������𡯡������ձ�������һ������˸����꾡���������Ϊ�������ĵ����壬��Ȼ��Ϊ���Լ�����Ϊ˵����������������̸֮�����ǽ߾�ȫ��ȥ���м��˵�������ͳ��������Լ����ʹ���Dz���е���������������Ϊ�е¡������ָ����ڸ��������Ϊ���غ;�����Ϊ���ҵĹ������Ǻ����ײ����ġ���
������ˣ�Ϊ�������ձ���һ�������������ϰ�ߣ������˱�������ǵġ�����������������һ��������������DZ����ȥ�����ǵ��Ļ�����������һ������Χ�ġ������������͡�ѹ�֡����ࡣ���ձ���һ����Ϊ�˳�Ϊ�õ�ѡ�ֶ�����ѵ�����ձ��˵Ŀ����ǣ����˲������ű������Ƶ��˸����������ʶ������ѵ����ѵ����Ȼ���ϸ�ģ�����������Ӧ��֮�塣�������Ҹ��������ޡ�Ʒ����������������ֻ�о������������������������������˻�Ů�˲��ܻ�ó�ֵ�����͡�Ʒζ����������������һ����ͨ����Ϊ��ֻ����ˣ�����������������������������ʹ��������������ҿ���Լ��������������������������
�������ձ������С������������������Ļ�����������������һ���˵Ĵ���̬�ȡ�����˵��������֮����Ҳ����е��������ܣ������ָо����þͻ���ʧ����Ϊ�����ջ�������ие���Ȥ�������������������ѧͽ���ؾص�������������ѧϰ�����������������������������ҵ�������Ӧ����ĸ��Ҫ���Զ�����������������Σ���ϰ������Ҫ������˻�Ů�˿��ܻ����ӱܴ��֡����������丸�������˵�����㵽������ʲô�������ͷ��Ϊ��Ʒ�������������Ҫ���ٽ���һЩ��������������������ȫ�����У��Ժ�ض�������ҡ�������������Ľ������ʹ������˵�����ģ���Ҳ����̻����ġ����������dz��õĻ���˵�����������Dz�ȥ�����ϳ�����
�������⡱����ʹ�˱�����λε������ĵ���������Ȼ��Ҫ��Ϊ�����ĵ�����
����Section��2��
�����ձ������ǿ���������������������Ⲣ����ζ�����ǵĵ��½��ɾ���Ҫ��ļ�����Ϊ�����������ص�ѹ�֣�Ҳ����ζ����Щѹ�ֲ��ᵼ�·����ij嶯����������������������Ϸ�������˶��п���������������ƹھ����ᱧԹΪ���������Ҫ�������������������������Ϊ�����������ֶ����ò����ѵ�ʱ���Ϊ��ѹ�֡������ǣ�ҽ��˵����ijЩ����£���һ����Ϊ�˺ܸߵĶ�ע��Ϊ�˶�ùھ�������ʱ���������븶���ĸ߶�ע������θ�����������Ƚ��Ų����ء�ͬ�������Ҳ�������ձ������ϡ����ǣ�����������ǿ�������ձ��˶�������������������ȷ�ţ�ʹ�����������˿��������ܵ��ж����ձ�����Ϊ���¡�����������ȣ����Ǹ����е�ע�����������ı��֣����ҽ���Ϊ�Լ��绤�����Dz�����������������Ƶ���ذѶ������ʧ���Ƶ�����������ȥ������Ҳ������˾����ع�Ӱ��������Ϊ��������ij��ԭ������������ν��ƽ����졣���DZ������ñ�һ�������˸����е�ע�⡰���ϳ������⡱����
�����ڡ������������������IJ��֮�ϣ����С�����ĽΡ������һ���ձ������������ձ����ߵ�������û���������˽�����������Դ˿�����ר���о�������ѧ���������Դ˲�ȡ���ӵ�̬�ȣ���ʱ���dz�֮Ϊ������һλ����ѧ��д��������ȫ����Υ����ʶ������ע����������������������Ӱ��������ǡ�һ��ׯ�صĺ��ԡ������ǣ��ձ���������Щ��������ʵ�ֵ�Ŀ�IJ��Dz������⣬���Ҷ�������������о������ںܴ�̶��ϸ����ձ��˵ľ���ͳ��������
������һ�������ĵ��ʱ������������ĸ���Ӧ�ôﵽ�����ľ��硣������ר������֮����Щ������ָ��Ա�ģ���Щ������ָ�ڽ���ͽ�ģ���Щ������ָ�����ֵģ���Щ����������˵�ҵģ���Щ������ָ���ҵģ���Щ������ָ���˾�ǵġ����Ƕ�����ͬ��һ���Ժ��壬����ҽ�ȡ��һ���������ҡ�������һ���ڷ��������һ�������ϲ�����ڽ���ʹ�õĴʡ����������ᄈ�ص��������£������ҡ�����ʱ�����Щ���Ļ��ڽ̵����飬�ھ�����������ʱһ���˵���־���ж�֮�䡰�䲻�ݷ���������ֱ�Ӵ���������������û�дﵽ����֮����������˵����־���ж�֮���ƺ���һ���Ե���ϣ��ձ��˳�֮Ϊ���۲�����ҡ��������ŵ����ҡ����������ߵ����⣬ϵָ�жϸ�����Ϊ���Ƿ��ƶ�ļ����ߣ�������ע�����������ر�����������ų�֮�������߱���ȫʧȥ�ˡ����������������¡�����ʶ��������ͨ���裬��Ϊ�������������ǡ�����һ�㡱������one��pointed������ľ�������ڡ����������ʡ���ʹ�õĴʣ��ݴ�����˵��������Ϊ����ekagra������ѡ�õģ��������Ͳ��֣��ļ�����һ���״̬��ͨ����̽�����Ϊ��һԵ������һ�ġ��ȡ������뱾ע����Ϊ˿�������������Ϊ���������������ͼ�Ρ���
�������ձ�����ͨ����Ҳ�����֡������Ӣ���о���̵Ĵ�Ȩ���闝�������ؾ�ʿ������һ��Ůѧ�����¡���
����������һλ��������ʿ������룬˵�����Ϊһ��������ͽ�����ʼ���ԭ��ʱ�����ش�˵���ĺ�Ը�dz˷ɻ����졣���������ͷɻ��������֮�����ϵʱ�����ش����������֪�������˷ɻ�����֮ǰ������߱�һ�ַdz��Ϳ���������ľ����������ľ�ֻ�о����ڽ����в��ܻ�á�����Ϊ�ڸ����ڽ��л����̿�������õģ������ǰ����̡����闝�������ؾ�ʿ�����ձ���̡�����286ҳ������ԭע����
�����ձ��˲����ѻ�������ɻ���ϵ���������ǻ����������Ϳ���Ŀ����ľ��������������ѧ���ԡ���˵�����μ�������ϵ�����������ǿ������������鼯����һ������������ڽ����κ���ҵʱ���ɴ����������ʵ����档��
����������������չ�����������������ձ��˵�Ŀ���뷽�������Լ���������������һ�����ر���Ȥ�ģ���Ϊ�����ձ����з�����Դ��ӡ�ȣ����Ƕ����г�Ϊ�٤���ձ������Ҵ��ߡ��۾�����Ϳ��Ƹйٵķ�����������ʾ����ӡ���˵ķ�����ѪԵ��ϵ�����Ǽ���ͬ��ǿ���Ŀա�����������ε��ظ�ͬһ�仰����ע�����̶���ij��ѡ���������ϡ�����������ӡ�����õ�����Ҳ��Ȼ���Ա��ϵó��������ǣ������������ɵ���Щ�Ǽ�֮�⣬�ձ��ķ�����ӡ�ȵķ��������й�֮ͬ������
����ӡ�ȵ��٤����һ����������ļ������ɣ����Ŵ��ֻ��л�ý��ѡ�����������ֽ��Ѽ�������û�������þ�֮��������·���ϰ����˵���������Щ���������ð������������Ѱ��ĥ��������ͨ����Щ�ֶ��˿��Գ�����ʥ��Ӯ�����ԣ��ﵽ����ĺ�һ���٤��һ�ַ����������磬������ͽ��������ֻ������ѵķ�������Ҳ���������������ķ���������Խ�������ﵽĿ��Ľ��̾�Խ�졣��
����������ѧ���ձ�������δ�ŵġ���Ȼ�ձ��Ǹ���̴�������ֻ�����˼������Ͳ��ǹ��������������ݡ���Щ˵�̱�ijЩ���ɮ�¸��������ܣ������Ǵ�δӰ�����ڵķ�ϰ�����ڵ�˼�롣���ձ������Dz�����Ϊɱ���κζ��������ͻ�ɱ��ת��Ͷ̥��������꣬���Ҳ����������ձ�������ͳ�����ʽҲ�����κ�ת���ֻ�˼���Ӱ�졣�ֻز������ձ���˼�뷽ʽ����˼��Ҳ����ˣ���������һ�����ں������壬ɮ�����Լ�Ҳ�����ĵò������ڡ�ѧ�����������������֮��������֮�У������ڴ˵ش�ʱ��һ���˿���������Ұ��������������ձ��˴�����û����Ȥȥ�����������һ�����硣���ǵ���������������ߵ����������������������������Ӧ��˼�롣�κ��ˣ��������������ũ�����ɷ𡣼��������ڵ�������λ�ͽ������𡱡�û���κ�������̹���ʹ���������ԣ����һ��������˴�̸������ͨ������ô��������Dz�������κ���ʵ�����������ѵ�Ŀ��ģ���һ���Dz��Բ����ġ������ʲô���ܳɷ�Ļ����˾�û�б�Ҫ���������Դﵽ���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