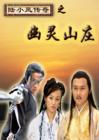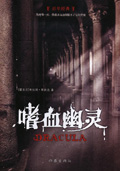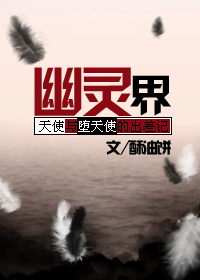��ɽ�����-��2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տ��Ѷ���¶��Ƭ��ɫɽ�أ����ȥƤë���ڵ�Ѫ�ľ��档����˵�Ȳ������ã�������ɫ�ͺÿ��ˣ������Dz�֪������Ƭ��ɽ����Ȼ��ֵҲ���Ӵ���ʧ��
����̤��ɽ���Ͻ���û���Ĺ�������ߣ��ҳ���Ⱥɽ֮�ϲ���֮��һ����ĺڵ㡣��ϲ�����Ա�����Ȼֲ�����ǵ�ɽ����Ⱥɽ��ԶӰ����������ɽҰ��Ȼ�����������ů��������������ںϡ�һ·������Σ��������磬������Ծ�������ߡ�ֱ��ɽ·�����������ԣ���ľ���ߡ��������ߣ�·�����ģ��������ƣ���ӿ��������ʱ�����ɽ���������ͥ������ͯ�������в��е����������ɽ��֮���ˡ�
�����Ƴ���ɽ������������������˦������ס�����ɽ���糤�����ֱ���չ���£������↑ʼ��£����Ҫӵ���뻳��ͨ���������ɽϪ�ڵ���ϸϸ���졣����������÷�ͽ�����ȫ���·�׳���˳���Ⱦ����������Щ��÷����֦������״��������Ҷ������ͤͤ�绪�ǣ�ÿ�ö������ĵ��ܣ���̬���ض��ֺ���ḻ��
�������˵Ĵ���ɽ�ȣ�������Ȼ�Ĺ��֣����������ˮ����������������ʮ�㣬�����л�����ݺͻ��ķ��㡣
���������ĵؾ������¾�����ب�ŵľ��ס�
����ˮ���������ˮ���֣�������ɲ�����档������ַ֮���ֱ�ֲ���������ⰻȻ��������������ϵ���÷����֦��������أ�֦Ҷ��ɡ��ǣ������������������֮�����ݣ�����������
��������Ƭ�ľ��Ĺ����������������ʯ�����������������Ƭ������ʯ������ɵ�������Ҳ�ж��ѵ�ʯ�������ž��µĿ���������Ұ����飬ͷ�Ϲ�����֦���ˣ�����ɽȪϸ��������
������˵�������ڲ��ؽ�ˮ���֡����ã�һ���ִ����ȡ����ǰ��һ�С����������������߹�һ���ž�������ɽ�룬��ת�������Ǿ��纣����¥������������ʧ��
�����������ͯ����ഺ����һ�����������ָ���Ӵ����ٿ�Ѱ����ֻ�ܾ���տյ����Ʒ�����
�������ұϾ����Թ�Ʈ���ˮ�����糯¶�����µĴ��⣬Ҳ��Զ����������һ�̵ĸ�����ж�����Ϊ�˸�л��Ƭ���ɽ�����ҵĺ�
�������յ���翷壬��ɽ��Ұ��Ϊֲ������ɺ������硣��һλ��翴��������Σ���ɽ������ʯ����ݴ�Ѱ�ҹ��ϵ�ʯ�̣�������û������С���ϲ�����ϵ��տ���ɽ��Զ����Ȼ������ɽ��ʱ��ʱ�ֵ�С·�µ���Щ������ɽ��ȥ���������翷嶥�־���ɽ����������±�����һ�£�����ͨ�������ķ���ȥ��Ҳ��һ����������������ï�ܵ��ç֮�С�
�����ȴ���翷����µ���һ��ɽͷ����;ȫ�ǰ��˸ߵ�é�ݺ�����ͷ�Ͻ���ֱк����Χ�ݺ���ӿ��������������ͷ������ñ����ʵ��ɽʱ��������ͷ������û���������ų�����ţ�п㣬�Ŵ�����Ь�������ڻIJݾ������к��ֱײ��ֻ���������֣����ɱ���س������̵ľ���������͵Ϯ�ɹ���
���������ɽ���ո��������Բ���������ߣ�����ɽ��é���纣���γɵ�׳����Ұ��ȣ��������ʲô��
������������ɽҰ�����������������ľ������ͯ��ʱ�ֲ��еĸо����ָ���˻�����һ��ֻ�ں����¡�
������һ�̣���IJ��֮��ֻ��ɽҰ��ʱ��������������ǵ�Ц�������ռ�ĺ�������������ʹЦ�������Զ�����������ɻ�����˭��Ц����
�����µ�����ɽ�����߸ߵ����ֶ���ˮɼ��һ�������Ϸ�ֱ����������ȫ���������⣻���³�����ˮ��֦Ҷï�ܵ������������µ�һ�У������߱����֦��Ҷ���С�
���������Ƭ�����д�Ŀ���̵�ֲ�����磬��������������������ľ����֮��ϴ�����أ�ü��Ҳ�峺���������ࡣ
Ʈ�����ļ���4��
���յļ��վ�Ӧ�������ȹ����߳��յ�������Ұ�⣬��ɽ�䣬�������ֲ�サ�ϵĿ����о���������Ȼɣ�ã���ÿ����ë���ſ���ȫ��������ϴ�������ۻྡȻ�ų����������յ�ɽҰ���ּ����̥���ǣ��ػ�Ӥ����ĺ����뵥����
������һ����������ȥ��翷��ʱ����������֮��Ѥ������ʱ�⡣������ʮһ�µ�һ�������죬��Լ��С�ο���ȥ��ɽ�����и���������翷��µĺ���������ǣ��������ȵ�ɽ��Ȼ��ȥ�������һ�����з�����ִ�ɽ���ѽ����硣
������ɽ�Ծ�����翴塣����Ľ���ɽ�壬��ɽ��Ұ�Ľ��ֹ�������ͨ���С��������ɫ��ʥ������������ۺ��С�ơ������������ӵ��ڴ�ǰ�ݺ���ɽ������䣬������̵���Ⱦ������ķḻ��������������Щ�ߴ�����������������ƽ�Ƶ�����ҶƬ�绪�ǰ�ſ��������۾�һ������Ҳ���ƿ���
������Щ����˥�ܶ���ζ������������ݣ��Ұ��߲���ǽ����ƣ���оɵĴ������Щ���������ֻ���������֦Ҷһ���У���Ҳ����������������
��������Ǵ�ɽ������һ���������ֵ�С����ɽ��������Ⱦ�̵�С·����Ϊ��������������С������Ĺ�����������Ȥ��Ȼ���ּ�յ��м��ù��ϵ���÷����֦����֦��չ�棬һ������Ծ���������̬��
��������ɽ�������磬̫�����ģ��·��Ĵ�ׯ������������һ�������п���������̫�������Ҳ�ǻҰ�һƬ���ܸо����������Ƥ������һ���ȶ��̵����ޡ�
����Ⱥɽ�ѻ�װ����һƬ������̵Ļ��ɫ����һ·��������֪���������β�ɣ������ǹ�ľ�Ͳ����������һЩ���ɫ������ɽ���������Ŵ��̵Ĺ�ʵ��أ�Ҷ�ӿ�ʼ���㣬����֦ͷ�ģ�Ҳ�ѽ��ݡ�
��������������ɽ·����翷嶥ͨ����ɽͷ�������������µ���ͬ��ɽ�룬һ��ͨ���Ͻ�����ˮ���룬��һ����Խ���ȥ��ͨ����Զ���ĺ����롣
��������ʱ�֣����ѷ�ɽȥ��ˮ��������������壬��ξ�ֱ����Զ���������ȥ��
�������̵�ɽ·�͵�ȡ�ģ��ǽ�ɽ���洦�ɼ��Ļ�ʯ����ƽ�̣���һ�������ƴ�����չ��Ⱥɽ��ͺ��ͷ��֮�ϡ�̫���ߵ�ɽ������ˣ���һ���߶ȱ���ʯ���������������ֻ��ϡ���������é��
�������ڶ�ɽԽ���ȥ��ɽ��֮�ϣ������ܽ����һ����
����;��ˮ���붥�ϵ�ɽ�����ּ���ɽ��IJ��汻��ȥ��Ƥ����¶���¸����ĺ�ɫ���㣬��������ֲ��Ҷ��ũҵ������Ŀ��
�����ִﺭ������Ϸ������Կ������ɽ��������ף���ɽ���³���һ���أ�����������������أ��Ա����ڽ���һ������ޒ�ȵ�¥����
��������һ·���̵Ļ�ʯ̨��һֱ�µ�����ǰ��С�ε��������ڵȺ����Ǵ峤����Ͻԭ�ȵĺ���������壬�ֺϲ�Ϊһ��ͳ������壬�ֱ���ˮ����ͺ������������У���800���˼ҹ�3000���ˡ�
������Щ������������Ŀ������ɽ�����ڿ�����������Ŀ����¥�Dz�¥��
�����з���������ԣ�����������ɫ��ɽӰ���˷���Ϻ���㡢��ˡ�ެ�ѵ��������Ǿͽ����ݺ�ͺ���ȡ����ʮ�����ʡ�������������У����Ͳ����ˡ����峤Ц��˵����ʱ��������һ����ˡ�
���������г��룬����ˮ��·��Լ������ͨ�����⡣���߽Ե�ɽ�������������������Щɽ���������ѣ���ԭ��ë����ʢ��ͷ���³���һ���ͺ�ߡ��峤����˵����ũ���ڿ����ֲ裬�����ͺ��ˡ��ֲ������룬��ũ���кô������Լ�Ҳ�����Ͽ���һ�Ҳ�Ҷ�ꡣ
����������ɽ����ӳ���µ�ũ�ᣬ��̾����˵��Ҫ������������ͺ��ˣ��Ժ��и�С���ĵط����峤Ц˵����ӭ��ʱ��ס��
����;����ũ�����ų��صķ�Ͱ������·�����ϵĹ��ּ�Ҳ��ũ�������������峤�����к�����Ȼƽ��������ʮ�ִ��ӡ�
���������塣�������ת��һ����լǰ���������Ĺŵ��̣�ľ�Ƶ��Ŵ�����ȫ���������Ŵ档�ܱ߱���Ӱ�Χ��������������ģ��Ϸ��Ӻܶ࣬�е�ֻʣ�����������֦��Ҷ�쵽����ȥ�ˡ�
�����������Ŵ����ƣ�����һ���Ľ��ִ�ӵ��ī�̵�֦Ҷ����������������ѹ����֦ͷ��һ������ǰ�ݺ���Ȼȼ���Ž�ɫ���ӣ�������������������֮��ȫ���ƴ������쳣�����������һ�δ������������������롣
Ʈ�����ļ���5��
������С���һЩ�յغ�ɽ�Ŵ�����Щ֦����ͦ�����������Ƶĸߴ����ӣ���ֱ������翷�Ⱥɽ�����ѳ��ľ��ꡣ
�������ص���Ӣ�ͷף�����������������ºʹ����
�������˺��壬�����²�����ȥ�f��壬ʵ����̫�����������ɽ����ˡ���ʱ���������߽�ɽ����κν��䣬�����߽�һ����Ѥ�������Ļ�ͼ�
�����f��Ҳ��һ���Ŵ��䣬������һǧ��֣���Ӵ��������ֱ��̫�����������Ǵ�����Խʱͨ�̵ĸۿڣ����ۼ���æ�̼��Ƽ�����������Խ����һ�������ʷ�����ֻ�ǹŴ���һ����ֱ�ĺӵ����羲ˮ����͡�������һ����С�ţ���һ�ξ�������ˮ���ʯ�ס�С�Ŵ���ǹ��ţ�������������ʯ����ˮ�е�Ӱ�γ���һ��Բ���Ż���ʼ���ݣ�����̨��ʯ���г�����ݡ�����ˮ�е�ʯ�״������ʯ������ԭ��Ӧ�Ǵ��ݻ���֮������ƺ��Ŵ��˵ط����غӵ����Ӷ��϶��ɣ������ٳ��˲ݣ�һЩ��������������Ѱ��ܣ��������ţ����Ƶ�ǽ����é��Ժ�����ſڵ���ʯ�ͽ�̨�ϵ��ŵ��뻧�ԣ�����ʯ���ϵ�̵ľ��»��ƣ���������˵���յķ�⡣
����Ϧ�����£�ɽ��ߵĹŴ����ƻ衣����ǧ�׳���֣����һֱ��ǰ�ߣ�����·�ߺ��а����ۣ����ַ���ϸ������һ������Ժ���ڻ谵����֮�䣬Ψ���ſ�������ĺɫ�����÷�������ϸ������ʱС�δӺ������˹�����һ���ͽ�������Ŷѽ������DZ�լѽ��
�����ף���լ��������ĩ���������������ӣ�ʽ�ѣ�����ɽ�ļ�����λ�����Ӻ���ɽ����������ͬ��д��һ�οɸ��������ʷ�������ʷ�������˻س�������
��������ʮ����ף�ʱ������̫����Ѳ�죨�൱�����ı�������ά�����յ�����˾�����չ١���������ʮ��������һǮ���棬����ְ�������������f�ƶ�������ϴ�����ɽ���ں�Ϊ������ƽ���е����ף��е��Ͳ����ھ�����������ʮ��壬Ϊ��Լ�߰�ǧ�ҡ���̫���������ݸ�������ʡ��������Ϊ֮����Ϊ������ɿ��Ҫ�����ܲ�ã����ϳͰ족���������������Ʒ�������һ������Ա��ȴ���ֳ��������ʿ���������š��������ݣ�����ͥɽ����������١���û�����Բ������ڵ��£���ɽ�����Ͳ��ף���������������Ը��Թ�߲����裬���߲���Ȱ��������������ġ�������1890�궬���������ܼ����˵�ʱ������������������ɢ֮Ϊ�桶����ɽ������ͼ�������������裬֣��䡢������˶�ȶ�����ӽ��һʱ��Ϊʢ�¡������Ӱչٻغ��ϻ����ϼҺ������ִ���������μӶ���ս������Ա���̫���f��Ѳ��ʱ����ֽڲ٣��Բ������Ϲٱ��������ж��ţ�����Ϊϧ������ǰ��Ͷ�����ɴ�ϲ���������á�����������������ɫ������ϭ����������������ǧ���˽һǮ�������Ϊ֮��̾����������Ϊ����������пɹ��ӡ������ҵڶ��ꡰ�м�������⣬�����ʮ�࣬������ϧ֮�����